







| 定價250元,特價79折198元 |
|
|





一個笑的黃金時代的消逝 台北•駱以軍•文 我們從很久以前就知道,這個世界已經不可能推翻,不可能改造,也不可能讓它向前的悲慘進程停下來了。我們只有一種可能的抵抗,就是不把它當一回事。可是我發現我們的玩笑已經失去力量了。你為了找樂子,勉強自己去說巴基斯坦話。結果是徒勞無功。你感覺到的只有疲倦和厭煩。──〈哈蒙在笑話結束時的哀歌〉
我們當然會想到《賦別曲》,或《可笑的愛》裡那些「那麼昆德拉」的短篇,〈順風車遊戲〉、〈代表永恆欲望的金蘋果〉,一些憂鬱的,犬儒的,虛無但好色的老男人們(中間會有一兩個他們想引誘上床的年輕美女),在某個譬如酒會、診療室、咖啡屋這類地方,展開滔滔雄辯;充滿哲學的背景,卻很可能說的都是扯屁或「詩意的滑稽表演」;他們為自己的衰老感傷,或是為這衰老無法挽回、那個他們曾經活過的時代一去不回而悲哀;那個時代,某些幽默和笑,是作為暴政、集權、統治者將全部人腦袋強制調成一種音頻,這個對立面而存在的(套句老昆的詞:「痙攣」),類似對立於政治神聖儀典與語言的黃色笑話;性高潮;某種回復到希臘戲劇的酒神憧憬,然其實是現代小說家對「革命的進軍」精神上踢正步這事的豎中指,想找回思辨的清醒位置。 |



|
第一部 主角登場
亞瀾沉思肚臍的問題 六月,早晨的太陽從雲裡探出頭來,亞瀾緩緩走在巴黎的一條街上。他觀察那些年輕女孩,發現她們都在腰身很低的長褲和剪裁很短的T恤之間露出光裸的肚臍。他著迷了;著迷,甚至心慌了:彷彿她們的誘惑力不再集中於她們的大腿,也不在屁股,也不在乳房,而是在這個位於身體中心的小圓洞裡。 這刺激了亞瀾的思考:如果一個男人(或一個時代)視大腿為女性誘惑的中心,這種情色傾向的特質要如何描述和界定?他即興作答:大腿的長度是路徑的隱喻畫面,又長又迷人的路(這就是為什麼大腿一定要長),走向情色的完成;其實,亞瀾心想,就算在性交的途中,大腿的長度也賦予女人一種難以接近的浪漫魅力。 如果一個男人(或一個時代)視屁股為女性誘惑的中心,這種情色傾向的特質要如何描述和界定?他即興作答:粗暴;快活;走向目標的最短路徑;由於這目標是雙重的,所以更加刺激。 如果一個男人(或一個時代)視乳房為女性誘惑的中心,這種情色傾向的特質要如何描述和界定?他即興作答:女人的神聖化;聖母瑪麗亞給耶穌哺乳;男性匍匐於女性崇高的使命之前。 可是一個男人(或一個時代)認為女性的誘惑力集中於身體中央,集中在肚臍,這樣的情色又要如何界定? 哈蒙在盧森堡公園散步 差不多就在亞瀾思索著不同來源的女性誘惑的同時,哈蒙出現在盧森堡公園旁的美術館前,那裡展出夏卡爾的畫作已經一個月了。他想看這些畫,但他早知道自己不會有力氣,心甘情願成為這沒完沒了、緩緩往售票口爬行的長龍的一部分;他觀察那些人,他們的臉因為無聊而痲痹,他想像那些展覽廳,裡頭的畫作被人們的身體和閒聊覆蓋,於是一分鐘後,他掉頭離去,走上一條橫越公園的林蔭道。 那裡的氣氛比較宜人;人看起來比較少,也比較自在:有些人在跑步,不是因為匆忙,而是因為喜歡跑步;有些人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草坪上有某個東方門派的徒眾正在做一些古怪的慢動作;稍遠處,一些法國王后和女性貴族的大型白色雕像圍成一個大圈,更遠處,詩人、畫家、學者的雕像在公園的草地上毫無章法地散落在樹木間;他在一個青銅色的少年面前停下腳步,迷人的少年光溜溜的,穿一件短內褲,要把巴爾札克、白遼士、雨果、大仲馬的面具送給他。哈蒙忍不住露出微笑,他繼續在這座天才的花園裡閑晃,這些天才被散步的人們溫和的淡漠圍繞著,應該會覺得舒適而自在吧;沒有人停下腳步細看它們的臉孔或讀一讀基座上的銘文。哈蒙呼吸這淡漠,呼吸這安撫人心的寧靜。慢慢的,一抹悠悠的微笑──近乎快樂的──浮現在他的臉上。 癌症不會生成 差不多就在哈蒙放棄夏卡爾的畫展,選擇去公園閑晃的同時,達德洛正在上樓梯,去診所找他的醫生。這一天,距離他生日恰恰是三個星期。他討厭生日已經好幾年了,為的是被強加在上頭的那些數字。可是,他又無法嗤之以鼻,因為在他心裡,有人為他慶祝的快樂總是勝過年華老去的羞慚。更何況這一次,看醫生給慶祝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因為今天他就可以知道所有檢查結果,他會知道在他體內發現的可疑症狀是不是癌症引起的。他走進候診間,他以顫抖的聲音在心裡反覆說著,三個星期之後,他將同時慶祝如此遙遠的誕生以及如此迫近的死亡;他將舉辦一場雙重的宴會。 可是一看到醫生微笑的臉,他就明白死神爽約了。醫生像親人般握了他的手。淚水湧上眼眶,達德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診所位於天文台大街,距離盧森堡公園約兩百公尺。由於達德洛住在公園另一頭的小街上,他開始穿過公園走回去。在綠地散步讓他的好心情變得幾乎有點放肆,尤其是繞過歷代法國王后圍成的大圈圈的時候──這些全數由白色大理石刻成的雕像,全身的雕像,擺出莊嚴的姿勢,在他看來不知該說是愉快還是可笑,彷彿這些宮廷貴婦想用這樣的方式為他剛得知的好消息歡呼。他忍不住舉起手,向它們致意了兩、三次,然後放聲大笑。 重病的祕密魔力 在那些法國王后附近的某個地方,哈蒙遇到了達德洛──去年,在一個沒有人會對它的名字感興趣的機構裡,他還是哈蒙的同事呢。他們面對面停下來,用一般人的方式打過招呼之後,達德洛用異常興奮的聲音開始說話: 「朋友,您認識我們的弗宏克吧?兩天前,她的情人死了。」 達德洛停頓了一下,哈蒙的記憶裡出現一張美女的臉,這個著名的美女他只在照片上看過。 「他臨終的時候非常痛苦,」達德洛說了下去:「我們的弗宏克和他一起經歷了這一切。噢,她真是受苦了!」 哈蒙著迷了,他望著這張愉快的臉對他述說一則哀淒的故事。 「您想想看,早上,她的情人在她的懷裡死去,而同一天晚上,她跟我還有幾個朋友一起吃飯,您不會相信的,她幾乎是開心的!我好佩服她!這種力量!這種對生命的愛!她的眼睛都哭紅了,可是她一直在笑!而我們這些朋友都知道,她有多愛他!她受了多少苦!這女人真是太堅強了!」 一如剛才在醫生那裡,達德洛的眼裡閃爍著淚光。因為,講到我們的弗宏克的精神力量,他就想到他自己。他不是也經歷了整整一個月面對死亡的生活嗎?他的性格的力量不也經受了嚴酷的考驗嗎?儘管癌症已經成為單純的回憶,終究還是像小燈泡的微光,與他同在,神祕地,令他讚歎不已。不過他成功控制住自己的情感,轉換成比較平淡的語氣說:「對了,如果我沒記錯,您有朋友可以包辦酒會,幫忙弄吃的跟一些什麼的。」 「是啊。」哈蒙說。 達德洛說:「我要幫自己辦一場小小的生日宴會。」 他興奮地說完那位著名的弗宏克的事,又以輕快的語氣說出最後這句話。此刻哈蒙終於可以露出微笑了,他說:「看得出來,您的日子過得還挺愉快的。」 奇怪的是,這句話達德洛並不喜歡,彷彿過於輕快的語氣毀了他好心情特有的奇異美感──記憶揮之不去,讓這美感如魔法般帶著死亡的浮誇印記。「是啊,」他說:「還可以。」然後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雖然⋯⋯」 他又停頓了一下才說:「您知道,我剛去見了我的醫生。」 對話者臉上的困窘令他開心;他延長了靜默,哈蒙不得不開口問道:「所以?您的身體有什麼問題嗎?」 「是有一些問題。」 達德洛再次沉默,而哈蒙也不得不再次問道:「醫生怎麼說?」 就在此刻,達德洛有如攬鏡自照,在哈蒙眼中望見自己的臉:那是一個上了年紀卻依然俊美的男人的臉,帶著某種悲傷的印記,令他看起來更有魅力;他心想,這個悲傷的美男子再過不久就要慶祝他的生日了,而他去看醫生之前的念頭又在腦海裡浮現了,這是個令人陶醉的念頭──一場雙重的宴會,同時慶祝誕生和死亡。他繼續在哈蒙的眼裡觀察自己,然後,用一種非常冷靜、非常溫柔的聲音說:「癌症⋯⋯」 哈蒙先是結結巴巴地說了些什麼,然後笨拙地,像親人般,用手碰了碰達德洛的手臂說:「還是醫得好的⋯⋯」 「唉,太晚了。請忘記我剛才告訴您的事吧,別告訴任何人;多想想我的雞尾酒會吧。日子總得過下去啊!」達德洛說。離去之前,他抬起手致意,這低調近乎靦腆的手勢有一種意想不到的魔力,打動了哈蒙。 無法解釋的謊言,無法解釋的笑 兩位老同事的相遇以這美麗的手勢作為結束。可是我無法迴避這問題:為什麼達德洛要說謊? 這問題,達德洛隨即也問了自己,他也不知道答案。不,他不會因為說謊而感到可恥。令他困惑的是,他無法理解自己說謊的理由。在正常的情況下,說謊是為了欺騙某人並且從中得到某種好處。可是編造癌症的故事可以贏得什麼?說也奇怪,想到這個謊言的無意義,他忍不住笑了。而這笑也一樣,是無法理解的。為什麼他會笑?他覺得自己的行為滑稽嗎?不是。而且滑稽的意義也不是他的強項。就這樣,莫名其妙地,這個想像的癌症讓他覺得開心。他繼續走他的路,繼續笑。他笑,他因為自己的好心情而開心。 哈蒙去夏勒家找他 哈蒙遇到達德洛一小時後,已經在夏勒家了。「我帶了一場酒會給你當禮物。」他說。 「太棒了!今年我們會需要這個。」夏勒一邊說,一邊邀他的朋友在矮桌對面坐下。 「這是給你的禮物。也是給卡利班的。說到這,他在哪裡?」 「還會在哪裡?在家裡,在他老婆那裡。」 「希望酒會的時候,他會留下來幫你。」 「當然會。劇場界還是沒有人要理他。」 哈蒙瞥見桌上擺著一本厚厚的書。他靠了過去,沒有掩飾他的驚訝:「尼基塔.赫魯雪夫的《回憶錄》。幹嘛啊?」 「是我們的主人給我的。」 「可是我們的主人在這裡頭能找到什麼好玩的?」 「他幫我畫了幾段重點。我讀了覺得還滿好笑的。」 「好笑?」 「那個二十四隻山鶉的故事。」 「什麼?」 「二十四隻山鶉的故事啊,你沒聽過嗎?世界的鉅變可是從這裡開始的!」 「世界的鉅變?有那麼嚴重嗎?」 「是有這麼嚴重。不過還是來說酒會的事吧,是什麼樣的酒會?要辦在誰家?」 哈蒙解釋了一下,夏勒又問道:「這個達德洛是誰?跟我所有的顧客一樣,也是個蠢蛋嗎?」 「當然是。」 「他的蠢,屬於哪一類?」 「他的蠢屬於哪一類⋯⋯」哈蒙若有所思地重複了同樣的話,然後說:「你認識夸克里克嗎?」 哈蒙講解「光芒耀眼」和「渺小無謂」 「我的老朋友夸克里克,」哈蒙說了下去:「我從來沒認識過這麼厲害的獵豔高手。有一次,我在同一場聚會裡看到他們兩人出現──就是他和達德洛。他們互不相識,之所以會出現在同一個擠滿人的客廳裡純屬巧合,而達德洛可能根本沒留意到我朋友的存在。那裡有幾位非常美麗的女人,達德洛遇到這種事就瘋了,他會為了讓女人注意他而做出不可思議的事。那天晚上,他舌燦蓮花,機智的火花四射。」 「傷人嗎?」 「一點也不。他連講笑話都很道德,很樂觀,又得體,不過他的句子實在太優雅又過度雕琢,很難理解,所以他說的話會引起別人注意,但不會引發立即的迴響。得等上三、四秒,他自己先哈哈大笑,然後再過個幾秒,其他人明白了,也禮貌性地跟著笑起來。這時候,就在所有人開始笑的這一刻──請你感受一下這個微妙的轉折!──他變得正經起來;他一臉不感興趣甚至厭倦的表情,望著這些人,心裡因為大家的笑聲而暗自得意了,虛榮了。夸克里克的行為則是完全相反。倒不是說他安靜不出聲。他總是在人群裡,不停地嘟噥著什麼,他的聲音微弱,不像在說話,反而像一陣咻咻的氣音,不過他說的話不會引起任何注意。」 夏勒笑了。 「你別笑。說話卻不引起注意,這並不容易!要一直在人前講話,又要從頭到尾不被聽見,這需要精湛的技藝!」 「我不懂這需要什麼精湛的技藝。」 「安靜會引起注意。安靜也可能讓人印象深刻,讓你變得像一團謎,或是可疑;而這正是夸克里克想要避免的。我剛才說的那次聚會就是這樣。那天晚上有位非常美麗的女士讓達德洛意亂情迷。時不時,夸克里克會過去跟她說上一點稀鬆平常、無趣、無聊的看法,但是這種見解讓人聽了舒服,因為不需要花心思去回應,也不需要用心去聽。不知何時,我發現夸克里克不見了。我滿心疑惑,觀察著那位女士。達德洛剛說出一段俏皮話,緊接著是五秒鐘的靜默,然後他哈哈大笑,過了三秒,其他人也學著笑了,就在此刻,這個女人消失在笑聲的屏障後面,往門口離去。達德洛被自己的俏皮話引發的迴響逗樂了,繼續耍他的嘴皮子。過了一會兒,他發現那位美女不見了。由於他對於夸克里克的存在一無所知,所以也不明白那位美女為何消失。他完全搞不懂,直到今天他還是完全搞不懂『渺小無謂』的價值。你問我達德洛的蠢屬於哪一類,這就是我的回應。」 「光芒耀眼之無用,嗯,這個我懂。」 「不只是無用。是有害。一個光芒耀眼的傢伙試著要誘惑一個女人的時候,這女人會覺得自己進入一種競賽的狀態。她會覺得自己被迫也要光芒耀眼。不能不做抵抗就獻身。渺小無謂反而解放了她,讓她放下戒心。不需要任何機智的表現,不會再想東想西,結果反而比較容易到手。這主題,我們暫且在這裡打住吧。至於達德洛,你面對的不是一個渺小無謂的傢伙,而是一個自戀的納西瑟斯。請留意這個名詞確切的意義:納西瑟斯並不是一個傲慢的人。傲慢的人會看不起別人,輕視別人。納西瑟斯則是高估別人,因為他在每個人的眼中觀察自己的形象,而且想要美化它。所以他對待他的這些鏡子都很親切。對你們兩人來說,他很親切,這是最重要的。當然了,對我來說,他是個裝模作樣的傢伙。不過,在他和我之間,有些事情也已經改變了。我知道他生了重病。從那一刻開始,我眼裡的他就變得不一樣了。」 「生病?他生了什麼病?」 「癌症。這竟然會讓我這麼難過,我也很驚訝。或許他正在度過他的最後幾個月。」 停頓一下之後,哈蒙繼續:「他告訴我的方式讓我很感動,非常簡潔,甚至害羞⋯⋯沒有任何刻意的浮誇,沒有任何自戀。突然間,或許是第一次,我對這個蠢蛋感到一種真正的同情⋯⋯一種真正的同情⋯⋯」 思考肚臍的亞瀾,討厭排隊的哈蒙,謊稱罹癌的達德洛,為山鶉著迷的夏勒,還有等待出場的卡利班;看昆德拉筆下的每個人如何在自己的世界中任由某種意義驅使或佔領,為了活過無意義的每一刻。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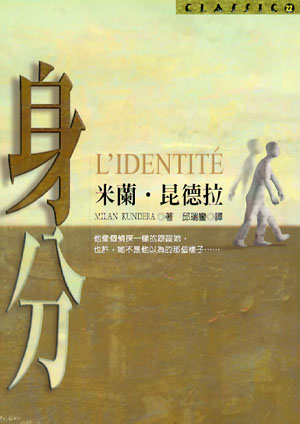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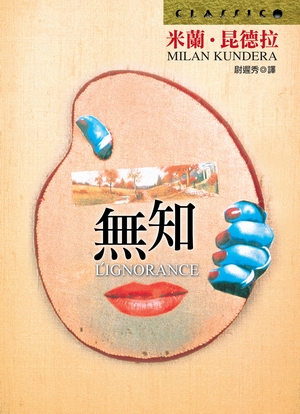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