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定價300元,特價79折237元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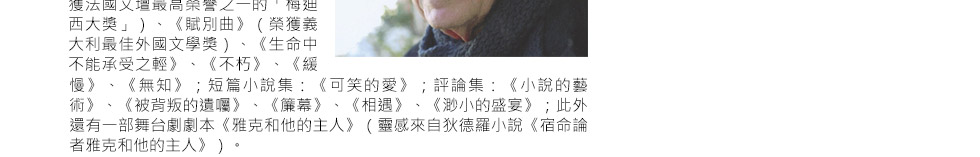





|
輕與重
1 永劫回歸是個神祕的概念,因為這概念,尼采讓不少哲學家感到困惑:試想有一天,一切事物都將以我們已然經歷的樣貌重複搬演,甚至這重複本身也將無限重複下去!究竟,這瘋癲的幻念想說些什麼? 永劫回歸的幻念以否定的方式肯定了一件事:一旦消逝便不再回頭的生命,就如影子一般,沒有重量,預先死亡了,無論生命是否殘酷,是否美麗,是否燦爛,這殘酷、這美麗、這燦爛都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可別太把它當回事,這不過就像發生在十四世紀兩個非洲王國之間的一場戰爭,就算有三十萬個黑人在無可名狀的殺戮之中喪生,這戰爭還是一點也沒改變世界的面貌。 如果十四世紀這場發生在兩個非洲王國之間的戰爭,在永劫回歸之中重複無數次,戰爭本身會有什麼改變嗎? 會的。這戰爭會變成一大塊東西,矗立在那裡,一直在那裡,戰爭的愚蠢也將堅持不懈。 如果法國大革命必須永無休止地重複,法國的史書就不會因為羅伯斯庇爾而感到如此自豪了。可是史書說的是一件一去不返的事,血腥的年代於是變成一些字詞、一些理論、一些研討,變得比鴻毛還輕,不會讓人感到害怕。一個在歷史上僅僅出現一次的羅伯斯庇爾,跟一個不斷返回、永無休止地砍下法國人頭顱的羅伯斯庇爾,兩者之間有著無窮無盡的差別。 這麼說吧,我們在永劫回歸的概念裡所見的事物,不是我們平常認識的那個模樣:永劫回歸的事物出現在我們眼前,沒有轉瞬即逝的情狀給它減輕罪刑。確實,這轉瞬即逝的情狀讓我們無法宣告任何判決。我們能給稍縱即逝的事物定罪麼?日暮時分的橙紅雲彩讓萬事萬物輝映著鄉愁的魔力;甚至斷頭臺亦然。 才沒多久以前,我被一種感覺嚇了一跳,難以置信:我翻著一本關於希特勒的書,其中幾張希特勒的照片觸動了我;這些照片讓我想起童年的時光;我經歷過這場戰爭;家族裡有好些人死在納粹的集中營;希特勒的相片卻讓我想起生命中逝去的時光,一段一去不返的時光,但是,從希特勒的相片看過去,他們的死成了什麼? 這個與希特勒的和解暴露出深層的道德墮落,這墮落是一個以回歸之不存在為本質的世界所固有的,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也因此,一切都被厚顏無恥地允許了。 2 如果生命的每一秒鐘都得重複無數次,我們就會像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那樣,被釘在永恆之上。這概念很殘酷。在永劫回歸的世界裡,每一個動作都負荷著讓人不能承受的重責大任。這正是為什麼尼采會說,永劫回歸的概念是最沉重的負擔(das schwerste Gewicht)。 儘管永劫回歸是最沉重的負擔,在這片背景布幕上,我們的生命依然可以在它輝煌燦爛的輕盈之中展現出來。 可「重」真是殘酷?而「輕」真是美麗? 最沉重的負擔壓垮我們,讓我們屈服,把我們壓倒在地。可是在世世代代的愛情詩篇裡,女人渴望的卻是承受男性肉體的重擔。於是,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最激越的生命實現的形象。負擔越沉重,我們的生命就越貼近地面,生命就越寫實也越真實。 相反的,完全沒有負擔會讓人的存在變得比空氣還輕,會讓人的存在飛起,遠離地面,遠離人世的存在,變得只是似真非真,一切動作都變得自由自在,卻又無足輕重。 那麼,我們該選哪一個呢?重,還是輕? 這是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Parménide)在耶穌紀元前六世紀提出的問題。依照他的說法,宇宙分作若干相反的對偶:光明─黑暗;薄─厚;熱─冷;存在─非存在。他將對反的一極視為正(光明、熱、薄、存在),另一極則是負。如此正負兩極的區分在我們看來或許幼稚而簡單,只有這個問題例外:重和輕,哪一個才是正的? 巴門尼德答道:輕是正的,重是負的。他說的對不對?這正是問題所在。可以確定的只有一件事,輕重的對反是一切對反之中最神祕也最模稜難辨的。 3 我想著托馬斯已經有好多年了。然而,卻是在前面這些反思的光亮照拂下,我才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他。我看見他,站在他公寓裡的一扇窗前,兩眼隔著天井定在對面樓房的牆壁上,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大約三個星期前,他在波希米亞的一個小城認識了特麗莎。他們待在一起幾乎不到一個小時。特麗莎陪他到車站,陪他一起等車,直到他上了火車。約莫十天後,特麗莎到布拉格來看他。他們當天就做愛了。夜裡,特麗莎發燒,她帶著感冒在托馬斯的家裡度過了一個星期。 托馬斯對這近乎陌生的女孩產生了一種無法解釋的愛。彷彿有人把一個孩子放進塗覆了樹脂的籃子裡,順著河水漂流,而他在床榻水岸收留了她。 她在托馬斯的家裡待了一個星期,身體一復原,她就回到她居住的城鎮,那城,距離布拉格兩百公里。而此刻,也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時刻,我看到托馬斯生命的關鍵:他站在窗前,兩眼隔著天井定在對面樓房的牆壁上,他思忖著: 該不該要她到布拉格住下來?這份責任讓他害怕。倘若現在邀她來他家,她會過來和他重聚,並且將一生都獻給他。 或者,他該放棄?這樣的話,特麗莎就會繼續在省城偏僻的酒吧當女侍,他也永遠不會再見到她。 他想要她來重聚嗎?要,還是不要? 他望著天井,兩眼定在對面的牆壁上,想找個答案。 他的思緒一再一再地回到這女人的形象上,她躺在他的沙發床上,她並沒有讓他想起過往生命中的任何人。她不是情人,也不是妻子。她是個孩子,從那塗覆了樹脂的籃子裡出來的孩子,而他將她撈起,放在他的床榻水岸。她睡著了。他跪在她身邊。她的氣息發熱,變得急促,他聽見微弱的呻吟。他把自己的臉貼近她的臉,在她的睡夢中輕聲說了幾句安慰的話。片刻之後,他覺得她的氣息平靜幾許,她的臉不自覺地抬起,向他迎了過來。他感覺她的雙唇因為發燒而散出淡淡的苦味,他吸著這氣味,彷彿想讓自己浸潤在她身體的私密之中。他想像她在他家度過漫漫歲月,此刻行將死去。突然間,他清楚地感覺到,如果她死了,他也活不下去。他將躺臥在她身邊,和她一同死去。他被這畫面感動了,他挨著她的臉,把頭埋在枕頭裡,如此過了許久。 現在,他站在窗前,回想起這個時刻。這不是愛情,是什麼呢?什麼東西會這樣跑出來讓人認識它的存在? 然而,這是愛情嗎?他相信自己確實想死在她的身旁,而這種感情也的確太過分了:那時,他總共才見過她兩次啊!或許該說是某種歇斯底里的反應吧,一個在內心深處確知自己不適合愛情的男人,竟然開始用愛情劇來欺騙自己?而這男人的潛意識又那麼軟弱,為自己的愛情劇挑了這麼一個來自省城的可憐女侍,若非如此,這女侍根本無緣走進他的生活! 望著天井對面那片骯髒的牆,他知道自己也搞不清這究竟是歇斯底里還是愛情。 他責怪自己,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真正的男人會立刻採取行動,可他卻猶豫不決,因此剝奪了自己生命中最美麗的時刻(跪在那年輕女人的床頭,確信自己在她死後也活不下去)的一切意義。 他不斷自責,但是後來他卻告訴自己,其實,他搞不清自己想要的東西,這種事是很正常的: 人永遠都無法得知自己該去企求什麼,因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既不能拿生命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來世改正什麼。 跟特麗莎在一起好呢?還是繼續一個人過日子好呢? 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檢證哪一個決定是對的,因為任何比較都不存在。一切都是說來就來,轉眼就經歷了第一次,沒有準備的餘地。就像一個演員走上舞台,卻從來不曾排練。如果生命的第一次排練已然是生命本身,那麼生命能有什麼價值?這正是為何生命總是像一張草圖。可甚至「草圖」這字眼也不夠確切,因為草圖總是某個東西的初樣,是一幅畫的預備工作,然而我們生命的這張草圖卻不是任何東西的草圖,不是任何一幅畫的初樣。 托馬斯反覆說著這句德國諺語:Einmal ist keinmal,一次算不得數,一次就是從來沒有。只能活一次,就像是完全不曾活過。 4 但是有一天,在兩場手術之間的空檔,護士跟他說有人打電話找他。他聽到話筒裡傳來特麗莎的聲音,她從車站打電話給他,他很高興。不巧的是,他那天晚上有約,他邀特麗莎第二天才來他家。從掛上電話的那一刻起,他就開始責怪自己沒有要她立刻過來,他還有時間去取消原來的約啊!他思忖著,在他們碰面之前的漫漫三十六個小時,特麗莎在布拉格要做什麼?他真想跳上車子,立刻進城上街去找她。 第二天晚上她來了,肩上背著一個袋子,背帶長長的,托馬斯覺得她比上次見面時優雅些。她手上拿著一本厚厚的書;那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看起來相當愉快,甚至還有點聒噪,她努力要在托馬斯面前表現出,她之所以會經過這裡,完全是因為偶然,因為某個特殊狀況:她來布拉格是為了工作的緣故,大概是(她說得十分含糊)要來找一份新工作。 後來,他們裸著身子,精疲力盡,並肩躺在沙發床上。夜已深了。托馬斯問她住哪兒,他想開車送她回去。她尷尬地答說要去找個旅館,她的行李箱寄放在車站。 前一天,他才在擔心,如果邀請她來布拉格的家,她會把一生都帶來獻給他。現在,聽她說行李箱在車站,他心想,她已經把她的一生放進這只行李箱,在還沒把一生獻給他之前,她先把行李箱寄放在車站。 他和特麗莎坐上停在公寓門口的車,開到車站,領了行李(行李箱很大,而且沉重無比),然後把行李和特麗莎一起帶回家。 事情怎麼會決定得那麼快?可他當初卻猶豫了將近半個月,連一張明信片也沒寫給她。 他自己也覺得驚訝。他這麼做,違反了他的原則。十年前,他和前妻離婚的時候,他在歡樂的氣氛裡,經歷了離婚這件事,就像別人慶祝結婚一樣。他從此明白,自己生來就不是要在一個女人身邊過日子的,什麼樣的女人都不行,他只有在獨身的狀態下,才能當真正的自己。於是他精心安排生活的方式,好讓女人永遠無法帶著行李箱住進他家。所以他只有一張沙發床。儘管沙發床夠大,他還是會明白告訴女伴們,跟人同睡一張床他會睡不著,於是午夜過後他就開車送她們回家。而且,特麗莎第一次因為感冒而留在他家的時候,他也沒有跟她一起睡。他在一張大扶手椅上度過了第一夜,接下來的幾夜,他都去了醫院,他的看診室裡有一張他值夜班時用的長椅。 可是,這一次,他在她身旁睡著了。早上醒來的時候,他看見特麗莎還在睡,但是卻握著他的手。他們的手一整夜都這麼握著嗎?這實在讓他難以相信。 她在睡夢中沉沉地呼吸,她握著他的手(緊緊地握著,他無法把手從緊箍之中抽出來),而那只沉重無比的行李箱就放在床邊。 他怕弄醒她,不敢把手從緊箍之中抽出來,他小心翼翼地翻身側臥著,好把她看得更清楚。 再一次,他覺得特麗莎是個孩子,被人放進塗覆了樹脂的籃子順流而下。我們怎能任由這籃子載著一個孩子在湍急的河水裡漂流!如果法老王的女兒沒有把小摩西從水裡撈起來,就不會有《舊約全書》,我們的一切文明也不會存在了!多少古老神話的開頭,都有人救起棄嬰。如果波里布沒有收留小伊底帕斯,索福克里斯也寫不出他最美麗的悲劇了! 托馬斯當時並不知道,隱喻是一種危險的東西。我們不能拿隱喻鬧著玩。愛情有可能就誕生於一則隱喻。 5 他跟前妻一起生活的時間才兩年,就有了個兒子。在離婚判決裡,法官把小孩判給母親,並且要托馬斯將薪水的三分之一交付給他們母子,同時也保證托馬斯每個月可以去看兒子兩次。 但是每到他該去看兒子的時候,母親總是推遲約定的時間。如果他給他們送了貴重的禮物,他要見兒子顯然就容易得多。他明白,為了他對兒子的愛,他得向兒子的母親付出代價,而且是在事前。他想像將來要把跟母親截然不同的種種想法灌輸給兒子,不過是想想而已,他已經累了。有個星期天,母親又在最後一刻阻撓他帶兒子出去,他於是決定這輩子不要再去看他。 而且,為什麼他就要喜愛這個孩子而不是其他的孩子?除了一個不小心的夜晚之外,這孩子跟他沒有任何連繫。他可以分文不差地付錢,但是可別以什麼父子親情的名義,要他為了父親的權利而戰! 顯然,沒有人會接受這種論調。他自己的父母也責怪他,並且宣稱,如果托馬斯不理他的兒子,他們(也就是托馬斯的父母)也不會再理他們的兒子。他們還繼續跟媳婦維持某種炫耀式的真摯情誼,對周圍的親友吹噓他們的模範姿態和正義感。 沒多久,他就這麼擺脫了妻子、兒子、母親和父親,留下的只有他對女人的恐懼。他渴望女人,但是又害怕女人。在恐懼和慾望之間,他得找到某種妥協;那就是他所謂的「肉慾情誼」。他明白地告訴情人們:只有不帶溫情的關係,任何一方都不擅自剝奪另一方生命與自由的權利,如此才能給兩人帶來快樂。 為了確定肉慾情誼永遠不會讓位給愛情的霸道,他跟每個關係穩定的情人都是隔很久才見一次面。他認為這方法非常完美,還在朋友面前大肆讚揚:「一定要遵守『三』的法則。我們可以隔很短的時間就去跟同一個女人約會,但是真要這麼做的話,就千萬別超過三次。或者我們也可以跟她交往漫漫數年,只要在每次約會之間至少隔了三個星期。」 這方式讓托馬斯可以跟穩定的情人們維持關係,同時也可以擁有許多露水情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他的想法。在他所有的女朋友裡,薩賓娜最瞭解他。她是個畫家。她說:「我很愛你,因為你跟媚俗的東西完全相反。在媚俗的王國裡,你會是個怪物。在任何一部美國或俄國電影的劇情裡,你都只能是一個惹人厭的角色。」 所以他要人幫忙給特麗莎在布拉格找工作的時候,他託的就是薩賓娜。在肉慾情誼不成文的規則要求下,薩賓娜答應他盡力幫忙,結果,沒過多久她就在一家周刊的暗房給特麗莎找到一份工作。這工作不需要特別的資歷,但是卻把特麗莎從女侍的地位提升到了新聞從業人員。薩賓娜親自把她介紹給編輯部的人。托馬斯心想,他從來不曾有過比薩賓娜更好的女朋友。 6 肉慾情誼的不成文公約規定,愛情被排除在托馬斯的生命之外。一旦他違背這條規定,其他的情人就會立刻覺得矮人一截,就會起來造反。 所以他給特麗莎租了一個單間公寓,特麗莎得把那只沉重的行李箱帶過去。他想要照顧她,保護她,開開心心地看著她,但是他一點也不想改變生活的方式。他也不想讓人知道她睡在他家。同眠共枕是犯下愛情罪的具體事實。 跟其他女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從來不睡。要是他去那些女人家找她們,事情很簡單,他隨時都可以走。要是她們來他家的話,事情就稍微麻煩一點,他得跟她們解釋,過了午夜他會送她們回家,因為他失眠,身邊有人就會睡不著覺。這與事實相去不遠,但是最重要的理由卻比這更糟,他可不敢對女伴們吐露:在做完愛的那一瞬間,他感受到一股想要獨處的欲望,無法遏止。深更半夜在一個陌生的生命旁邊甦醒,這讓他覺得很不舒服;早上兩人一道起床,這讓他感到厭惡;他不想讓人聽到他在浴室裡刷牙的聲音,兩人一起吃早餐的親密感覺誘惑不了他。 這就是為什麼他一覺醒來發現特麗莎緊握著他的手,會那麼驚訝!他望著特麗莎,他無法理解自己到底怎麼了。回想剛剛過去的幾個小時,他相信自己方才呼吸著某種莫名的幸福芳香。 7 夜半時分,她在睡夢中發出痛苦的呻吟。托馬斯把她叫醒,可她一見托馬斯的臉就恨恨地說:「你走!你走!」然後才跟他說了她作的夢:他們兩人和薩賓娜一起待在某個地方。在一個寬闊巨大的房間裡。房間的正中央有一張床,看起來就像劇場的舞台。托馬斯命令她待在房間的一角,而他就在特麗莎面前跟薩賓娜做愛。她望著他們,這景象讓她痛苦不堪。她想用肉體的痛苦來平息靈魂的痛楚,於是用針扎著自己的指甲肉。「好痛啊!」她一邊說,一邊把手都攥成了一團,彷彿手上真的受了傷。 托馬斯摟著她(她身體的顫抖不曾止息),慢慢地,她在托馬斯的懷裡漸漸睡去。 第二天,托馬斯想著這個夢,也想起了一件事。他打開書桌的抽屜,拿出一疊薩賓娜寫給他的信。他翻了一下,看到這段話:「我想跟你在我的畫室做愛,像在劇場的舞台上那樣。人們滿滿地圍繞在四周,但是卻不能靠近。他們不能靠近,卻又非看不可……」 更糟的是,這封信上頭有日期,是最近才寫的一封信,那時,特麗莎已經在托馬斯家住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非常生氣地說:「你偷翻了我的信!」 她沒打算要否認,只是說:「怎麼樣!那你把我趕出去罷!」 可他沒有趕她出去。他看見她在那兒,身體貼在薩賓娜畫室的牆上,用針扎著指甲肉。他捧起她的手指,輕輕撫摩,他把她的手指捧在唇邊親吻,彷彿指尖還留著血跡。 然而,從這一刻開始,一切事情彷彿都密謀著與他作對。幾乎沒有一天特麗莎不是又發現了一些關於他地下情史的新祕密。 起初他一概否認,直到後來證據實在太明顯了,他才試著要說明,他的多妻生活和他對特麗莎的愛情之間,沒有任何矛盾。他的說詞前後不一:一下否認自己不忠,一下又為自己的不忠辯解。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一個女人約時間。電話才說完,他聽到隔壁房間傳來一陣奇怪的聲音,像是牙齒在打顫。 特麗莎剛好來到他家,可他卻完全不知道。她手裡拿著一瓶鎮靜藥水,正要往嘴裡灌,她的手顫抖不已,玻璃瓶在牙齒上磕碰著。 他撲了過去,像要把溺水的她救起來。裝著纈草藥水的瓶子掉下來,把地毯弄出一大塊污漬。她奮力掙扎著,想要掙脫他,而他則是抱住她好一陣子,像一件束縛衣緊緊囚住一個瘋子,直到她冷靜下來。 他知道自己處在一個無從辯解的處境當中,因為這處境建築在一個全然不平等的基礎上: 早在她發現他和薩賓娜通信之前,他們倆跟幾個朋友一起去了一家小酒館,慶祝特麗莎有了新的工作。她離開暗房,成為那家雜誌社的攝影記者。由於托馬斯不喜歡跳舞,他醫院的一個年輕同事就負責陪特麗莎跳舞,他們在舞池裡滑著美妙舞比的舞步,特麗莎看起來比任何時候都美。托馬斯愣愣地望著她,如此準確又如此溫馴,毫秒不差地迎合著她的舞伴。這支舞似乎宣告著,她獻身於他,她懷抱熾烈的慾望去做她在他眼中讀到的一切,可這一切不一定得連結到托馬斯這個人的身上,而是隨時可以回應任何一個她遇到的男人的召喚。要把特麗莎和這年輕同事想像成一對情侶,實在太容易了!正因為這樣的想像如此容易,他受傷了!特麗莎的身體跟任何一個男性的身體纏綿在一起,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這念頭讓他心情低落。深夜,他們回到家裡,他向她承認了自己的嫉妒。 這荒謬的妒意,誕生於一個全然屬於理論的可能性之上,證明了他把她的忠誠視為一個必要條件。那麼,他又怎能責怪她嫉妒,嫉妒他確確實實存在的諸多情婦? 原打算將愛情排除在生命之外的托馬斯,在六個偶然之下,遇見純真質樸的特麗莎,並決心開始他們的愛情。然而,特麗莎對於感情的絕對與執著,令托馬斯難以承受。而向來崇尚情感自由的他,在諸多情婦與特麗莎之間,又會如何做出選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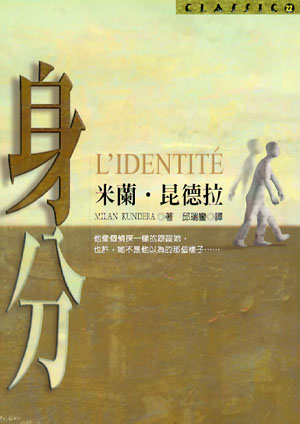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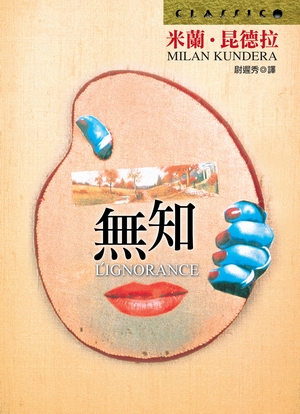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