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山的疊彩,水的樂音
白 靈 ──張默的旅遊詩
張默是這島上的紅塵中極少數能把「詩」當作動詞,而不只是名詞的人。對他而言,「詩」是巨大的引擎,可以裝在任何東西的身後,啟動它、轉動它,將它帶離習慣的位置,因而發現了詩的無數可能。早年他趴在詩的稿紙、詩集、和無數「紮營」式的詩刊、詩選上,帶自己去到那到不了的遠方旅行,是對時代之靜止和束縛的無言抵抗;晚近,旅行,則是張默回家的一種方式,更確切地說,那是他在漂泊中尋找家的一種形式。他的行囊就是他的傷口,他童年的家、他少年的夢,也是他中年的藥、和老來的綑帶,那頻繁的腳程是他將詩和生命動詞化的一帖良方,卻也成了他對時代之亂和痛的一項付諸行動力的抵抗形式。 美的包紮與拆解 後幾代的人都很難明白,張默那一世代由大陸來台的詩人都不約而同陷入相似的行徑中,他們率皆是「拎著家去旅行的一代」,他們的行囊就是家,「旅行」是時髦詞,其底層等同於漂泊、流浪、無常感。因此回頭再看張默所作所為,甚至他五十餘年詩壇火車頭似不停地投注於詩刊、詩選,以及難度極高的書目的編纂,均可看作是他把「心中的方寸之地」填補、包紮、拆解、再填補、再包紮、再拆解的反覆形式,像是心理學中的強迫性行為似的,不斷地以詩以美以各種叛逆、創新行徑去包紮自身,然後又在完成的末端,再度打開拆解原已存在的完成物,去重新感知審視傷口的那個痛和快感,而那與裹包填實一個行囊,然後再予拆光分散並無不同。
說「旅行,是張默回家的一種方式」,跟那世代的詩人是「拎著家去旅行的一代」,這中間並無矛盾,只是各自處理心中漂泊感的形式略有不同而已。因此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會出門總是背著重物和所有家當在身上;或者長年在兩岸三地的邊緣行走講學;或者出國數十年不回;或者老來才選擇遠走他鄉;或者街頭擺攤數十年如坐禪;或者詩中鑽著無數「逃」和「漂」的意象;以及都能更深刻體認到何謂以沫相濡……,他們的行徑相對於後幾代詩人,是流動的、不定的、充滿著不安的,是不斷向遠方和西方延伸的,他們與東西晉、南北宋因改朝換代而被迫大遷徙的文人心境是極度相似的,因為有個永遠回不去的「家」的「過去」,在時代的遠方擱淺,一擱數十年,末了乃成了永遠靠不近的夢,其中感受之苦只有他們一代人彼此可以理解,「動盪」遂成了他們的宿命和掌紋。加以內外環境的變遷、時空氣氛的轉換,和不理解的人無形無理的指摘又無時無刻不煎迫其心境,卻無可辯白,也不欲辯解,因此內心深陷的苦終其生也始終難以消解。 那種感受可以一九六七年張默寫澎湖的〈我站立在大風裡〉的兩句詩比擬之: 我站立在風裡 滿身的血液如流矢 風是人人感受得到的外在力道,尤其是時代強加在每個人身上的颶風,那是人人都會被吹颳得跑的,但「滿身的血液如流矢」卻無人看得到摸得著,尤其「如流矢」的血是熱血、脹紅臉的血、寒冷顫抖的血、氣壯如山的血,還是憤恨咬牙的血?是準備慷慨激昂還是激動欲泣?綜張默和他同世代人的一生,上述諸種「如流矢的血」可說兼而有之,那該如何說得?
應怎樣說清? 一九六七年的這同一首詩中張默以幾近預言的方式預告了他一生的行蹤和欲付諸行動的強烈生命驅力,亦即如何「如流矢」的方向: 我欲以全生命的逼力去親貼去飛逸 去泅泳 舐舐暴躁的海特釀的鹹味 我心中綿密的森林與某些 潮濕的夜晚與某些 星星的爭吵 「全生命的逼力」是怎樣的力道?是如流矢的血的逼力?還是時代的幫浦抽動血的逼力?竟讓張默想「去親貼」、「去飛逸」、「去泅泳」?三個排比句強力表達了一種從現實逃脫的欲望,卻又要去親貼舔舐「暴躁」「綿密」「潮濕」「爭吵」的自然景觀(可能也包含了欲望底層的暗喻),那依然是熱鬧地佈滿生命原力的另一所在,兼有動(海)、靜(森林)、視覺、味覺、觸覺、聽覺,是全方位感受的渴求。雖然那時他的行蹤仍未超脫台灣的範圍,最多在如澎湖金門邊緣的小島上行走,最多是與詩友們在高雄左營「光著屁股∕平躺在四海一家空曠的台階上∕而第二天一大早,新聞報居然隻字未提」(〈再會,左營〉,一九七二年),「光著屁股」像是示威,但未見其他人影,而當時的張默仍任軍職,顯然只是單純叛逆,框框還在,但其行徑已「飛逸」常人行為甚遠。 即使到了一九八一年〈西門町三帖〉的〈天橋〉一詩,其實際的行動力仍深受拘束,反映的是全島嶼的人的共同困境:「那是黑鴉鴉的∕一群螻蟻∕在蠕動嗎∕誰擋著誰的軀體∕誰踩著誰的去路∕發自無數個∕群體的∕無聲的吶喊∕企鵝般地∕綣縮在∕枕木與鐵軌的高處∕且一邊諦聽∕而又∕微微的呼吸」,此詩表面上在寫西門町當年人群雜遝過天橋的場面,但底子裡所說「螻蟻」、「群體無聲的吶喊」、「企鵝般地綣縮」不也是群體當下現象的縮影?而且「諦聽」著什麼呢?像有什麼自鐵軌的遠端要傳來?則「天橋」的「天」字其實是一大諷刺,其高度離「天」極遠,只綣縮在那被整齊排列得中規中矩的枕木與鐵軌的高處,活著,諦聽「遠方」自軌道另端傳來,有什麼事將發生,卻又無可阻擋,此處表現了個人在群體中的高度自覺,想要即早「諦聽」出什麼訊息的強烈渴望。 對遠方的渴望,是張默那一代人一生底層的色澤和痛,遠方的老家由真實落入夢境後,後來便被更遠方的西方所取代,當它們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時(當時僅留學生較易出國,張默遲至一九七六年才去了日、韓兩國,還不是西方),詩的和美的內容或形式乃成了取代物,以之「去親貼」、「去飛逸」、「去泅泳」,不論是去包紮自身或拆解自身,都成了張默在那時空中(來台的前三十年)僅存的出路。
遠方是會流逝的鮮脆 但也因而具足了各種因緣際會,他們也就能堂而皇之的站在荒涼的時代前端,開創出一個全新的詩的時代,填補了一九四九年後海峽兩岸詩史的最可怕的空檔,因為他們嚐過的苦和上帝選民似的幸運,是空前絕後的,至少在這一百年之間。於是張默成了創世紀詩社的三巨頭之一(另二人是洛夫和唯弦),他也是《創世紀》詩雜誌奇蹟似地在詩壇屹立五十餘年仍能如鋼柱般挺著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原因。而此詩集中寫於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二日左營桃子園的第一首詩〈荒徑吟〉早就道出了這樣的訊息,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還是寫景的: 披頭散髮,像不?的浪子 鬍髭已經爬滿兩腮了 它 還要向無垠的闊野,航行 去吧!別再異想天開了 我的腳是重磅的鋤 浪人呀!你還不快修一修臉面 整一整,衣冠──〈荒徑吟〉 此詩創作日期離一九五四年十月「創世紀詩社」於左營的創立時間不足一個月,題目又叫「荒徑吟」,其引發聯想就不足為奇。詩中首段是對現實景象的考察和估量,二段是面對此景擬採取的策略和對策、乃至警告;表層寫荒徑待闢,但面積遼闊,唯有行動才能對應;底層則可能寫人生無窮、前程難料,唯有付諸實踐,則自有錦囊妙方。前二行為一擬人的明喻,顯與「荒徑」的面貌有關,第三行的「它」還原為「荒徑」,但只有浪子才有可能「還要向無垠的闊野,航行」,顯然荒徑亦即前此自我荒廢的、等待收拾整頓的人生,回首望之不短,未來持續將看不到底,不知會延伸到哪裡去,如此浪人、荒徑都成了人生路途的可能卻未可知的去向。二段「去吧!別再異想天開了」表面是對荒徑說,好像也對自己說。「我的腳是重磅的鋤」,此句是關鍵句,「我」的出現是對荒徑、人生、乃至浪子之心(暗喻內在的我)的下定決心似的介入和清理,因此末二句成了對荒徑和浪人所下的最後通牒,說張某人要來了,你們還不自我整肅一番,難道非要我好好收拾你們不可嗎? 如此看來,「荒徑」是「浪子之心」、是「過去之我」、是「等待整頓之我」、是「不可心存僥倖之我」,和「即將奮起之我」。這是往回看,如果往前方看、往後來的五十年看,「荒徑」是「少人走之路」、是「預告之路」、是「未來之路」、是「存在各種可能之路」,也是「創世紀開疆闢土之路」,乃至張默中壯年後「行旅天涯之路」。這首詩等於預告了創世紀詩刊後來五十年的可能性,也預期了這本旅行詩集的誕生。
「重磅的鋤」就是他生命的動詞,實踐力、劍及履及的保証! 也因此,張默即使後來終於能站在荒涼的青藏高原,他也要深深地吸吮的那種氣息,其實和在〈荒徑吟〉中他所欲呼吸的氣息相距不遠,這是與他同齡同世代的大陸詩人所享受不到、體會不著的,那種撥開千層重壓去感受新生式的噓息: 把握每一刻流逝的鮮脆 它們既冷冽又熱熾的折疊著 一種無限延伸的魅力之所在 張默所寫的是既存在又隨時將不存在的感受,「鮮脆」、「魅力」是正面的存在,「流逝」是負面的,「冷冽又熱熾」是反復不定,「流逝」是令人清醒的冷冽,「鮮脆」是叫人沉緬的熱熾,人生即以此「折疊」而成,如此向歲月無限延伸下去,也就成就了遠方「魅力之所在」,雖然是會流逝的鮮脆。他在〈嗨草原,請席捲我〉一詩中說:「我永遠渴想複製那些綿延不絕的地平線,且一直引頸眺望:那些更洪荒、更拙樸、更澄碧,一片煙波浩渺,永生難以抵達的遠方。」「把握每一刻流逝的鮮脆」即因在前方逗引的恆是綿延不絕的「永生難以抵達的遠方」。遠方,成了無常之物、成了隨時會幻化蒸發之美,而那又是他永生想尋訪的家,隨時包紮又隨時將之拆解的行囊,那是難以明說的一種時代的傷口,不只是張默的。即使他寫於一九九三年這首看似要與「遠方」再見了的詩作都只是暫時對傷口的包紮: 〈再見,遠方〉──舊金山紅樹林偶得
第一株 修長而且蒼勁
第二株 筆直而且濃蔭齊天
第三株 弓著嶙峋如山谷般的身子向遠方,淡淡的發問
第四株 閉目凝神,以及什麼來著
第五株 吐納,吸吮對視而且歌唱
第六株 向歲月不斷的哈腰
第七株 一味深情地沐浴沐浴
第八株 每天站著,採一種習慣的樣子
第九株 第十株……
仰泳千山萬壑之間
談笑自在如風聲
此詩妙在後幾句的「仰泳」和「談笑自在∕如∕風聲」,把參天古木的巨大實體自由化為仰泳之人、虛化為飄渺不定的風聲,則插立大自然中就已不必他求,寫的是期待自身有一朝也能如參天紅木林之屹立,就那裡也不必去了,自然可與遠方說再見,當下賞景之人與之同一了,獲得暫時的「家」的深刻感受,有了短暫的解脫和昇華感。但此詩背後卻隱然透露了張默自己要與遠方說再見的困窘,乃至不可能,那仍然是會流逝的鮮脆。 遠方隱藏的奧府 遠方隱含的「每一刻流逝的鮮脆」究竟是怎麼樣的內容物,可以終生逗引一個詩人不悔地拎著行囊前往,它總有個人性的根由或奧祕隱藏著。若試著到美學中去尋找緣由,則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或可略予解疑,劉氏說: 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 天氣四時之循環,天災地搖之駭人,「『動』物」如此明顯,萬物會因自然之變化而感動、驚動、或顫動,乃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到了現代人反而對自然之變遲鈍、駑鈍而無所感起來,豈非值得警醒?且顯而易見的是,一如葉子入冬時樹樹萎落離枝的方式不一、變色的情形不一,有人一定動搖震顫幅度大且快,有人則必然小且緩。如此對張默而言,「遠方之動」,心豈不搖焉?「遠方」之「『動』物」又豈不深矣? 劉勰在此篇的後段又說: 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
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這一段最能說明山水自然對人的重要,「山林皋壤(水澤旁邊平而溼的地方),實文思之奧府」是說自然比人懷有更大的寶藏,人之中不可解的,自然是解答者。《莊子》〈知北遊〉中也說:「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這其中的寶藏一生豈能窮盡,又向能不時時求此「欣欣然而樂與」的江山的包紮?那麼張默胸中的傷口豈能不大大求於此「江山之助乎」? 此文末了結語是: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日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末兩句最值深思,是說人與自然的距離,就是生活與創作的距離,一朝距離拉近,甚至合而為一,則一贈即可得一答,若聲響之叩,一敲即得一響。張默多年「情往似贈」於不斷變動的遠方,遠方對他豈能不「興來如答」,對之有所擁抱和回應? 何況「人之中不可解的,自然是解答者」,遠方顯然充塞了無盡的山林皋壤,也就隱藏了「家」的影子,由前舉〈再見,遠方〉一詩即可略知。在〈峇里島偶拾〉中他說:「我最想做的,還是卸下光禿禿的脊樑∕東一塊,西一塊∕把它扔在朗朗的沙灘上∕什麼,也不想」,那是一種回歸、息去行止的渴望;然則在〈石雕巨柱134之嘆〉中他卻說:「我總是無法筆直打通前進的去路,我會隨時被鄰座一連串巨大柔軟的陰影,不小心的輾碎或淹沒」,這本來寫的是埃及阿蒙神殿一景的幾句,其實說的是他對周遭事物的敏銳和「大驚小怪」的神經質,這也註定了他無法如人為的134根巨柱般安於被時間凝固住,不是不言不語、孤芳自賞,要不即喋喋不休,要不哈欠連連、一事未成:「你瞧,它們都習慣自己是石雕森林的一分子,青苔總是沿著時間的額角,一遍又一遍,兜圈子」,但這不是他的作風,〈再見,遠方〉的「仰泳千山萬壑之間∕談笑自在∕如∕風聲」,比較像他的渴盼。然則「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與「每一刻流逝的鮮脆」的關係不可不深究,比如下舉三例: 山的疊彩 水的樂音 從八方四面不約而同的趕來 你能承受得起嗎 當眾多眼神正撩撥某一特異的景象 那些刻刻變調的風水 又向左舷,不勝倉皇的逃走了──〈乍見灕江〉
摘錄 恍似跌入曠古無人森然的絕境 巨石似一排排洶湧的波濤 側耳,坦胸,伸腿,舉臂 向我的神經末稍急急地圍攏 驀然一轉身,那顆圓溜溜的旭日 唰的一聲,叫我不得不信 輕輕落在那撇拒絕褪色以及招風的眼睫上──〈晨遊始信峰〉(〈黃山四詠〉之一) 在山間,日子像放置在案頭上的桌曆 隨你怎麼撥弄 它就是一動也不動 溪水把鐘錶有節奏的跫音吵醒了──〈溪頭拾碎〉摘錄 〈乍見灕江〉中說「你能承受得起嗎」,隱藏了令人招架不住的「物色之動」;而〈晨遊始信峰〉中說「輕輕落在那撇拒絕褪色以及招風的眼睫上」說的是不易心動的眼睫都不能招架旭日輕功似的「動」。而這些「動」都那樣快速地變化,稍一不留心,「刻刻變調的風水」和「唰的一聲」可能轉瞬就看不見也聽不著,那種「每一刻流逝的鮮脆」是令人心驚膽跳、目不暇給的。
而〈溪頭拾碎〉則是有如〈再見,遠方〉一詩一般,再度有讓遠方凝止不動的感覺,雖然溪水在一旁瞎起哄湊熱鬧,這也是張默何以會六訪溪頭的原因,那裡可能也成了在台灣離他最近的遠方了,一定藏著某些參不透的奧府仍有待持續挖掘吧。 遠方的重組與再造 此文一起頭即說張默是這島上的紅塵中少數能把「詩」當作動詞,而不只是名詞的人,除了他對現代詩壇矢志不移、眾所皆知的行動和奉獻外,他在詩篇中營造的「動態式目光」,其實是非常「立體派」、「未來派」的,那是杜象(1887~1968) 式「走下樓梯的女人」般的連續閱讀方式,充滿了節奏與運動感,但快慢伸縮自如並無未來派的機械感,比如張默一九九五年的作品:〈搖頭擺尾,七層塔〉呏w─大雁塔巡禮 在塔的頂端 伸手抓住幾塊懶洋洋的白雲 把它擰乾 天空,就不會那樣的蕭蕭了 接著,隱隱約約的鳥聲 以密不透風的籠子 偷偷運到第六層 牠們音樂的步姿,將和塔緣的風鈴交響 再向下,是第五層 有一赤身露體的托缽僧 閉目靜坐一隅,啊!喃喃的天籟 嘩然,一群從塞外飛來的寒鴉 精神抖擻,並排立在四層的迴旋梯上 一蹦一跳,一跳一蹦 紛紛下墜到 三層 二層,以及 人聲鼎沸的 第一層 俄頃整座七層塔,經不住一陣驟來的風雨 搖搖晃晃,揹著地平線愴然與黑暗一塊 掉頭而去 這首詩如果改以杜象式的畫面呈現,精彩程度一定更甚於杜象,甚至必須用影片或動漫表現,才足以捕捉其細節,尤其末了還來個超現實情節,杜象根本無從表現。塔有七層,題目已說,詩起頭因此不說,先說天氣和詩人立足點,並為末尾的風雨和黑暗預埋伏筆。第七層和第六層就寫了八行,是蘊勢,「鳥聲」、「籠子」、「偷偷運」等字眼一方面寫了塔的古樸、寧靜、和幽深,一方面也帶出自然和自己對塔和玄奘的敬畏,到第五層仍有此氣氛,但第四層以下是大轉折,詩以快節奏處理,瞬間便到達人間紅塵,表現了塔立於此有交通天上與人間之感。末四行有反諷味道,本有風雨驟來遮去塔影之意,也間接諷刺了宗教在大陸熱鬧的假象,巳與當年佛意有別,以超現實畫面處理,增添了譏諷的氣氛。此詩可說是張默將眾所熟悉的遠方重組、並予再造的力作。
他在二○○一年的作品則以他的老家景點為題材,動態目光則採與登大雁塔相反的方向:〈登金陵閱江樓〉一段嶙峋,把咱們的視覺無端的推升 推升與獅子山一樣高聳 烈烈的傲骨,推升 每一棵不寐 好個逍遙遊的松柏 每一片斑剝 被壓得透不過氣來的磚瓦 推升 無所謂薄如蟬翼的干疋燈火,以及 浩瀚如夢的蒼穹,推升 推升,從六朝喋喋不休 驚叫到現在的 寒鴉 此詩簡潔有氣勢,起句即震人,末尾出人意表。與上首詩由上而下不同,改由正常的由下而上方式向上推升,景由遠(山)而近(瓦)再推遠(燈火),由視覺而聽覺(鴉叫)。四至七句為跨句,原句是「每一棵不寐好個逍遙遊的松柏∕每一片斑剝被壓得透不過氣來的磚瓦」,末五行最是精彩,「無所謂薄如蟬翼的干疋燈火」應是黃昏遠觀的感受,燈火宛如一層薄翅,宛如隨手即可被無所謂地燒毀的尋常萬民百姓,將實景推升至與歷史和當下鴉叫合而為一,而寒鴉歷代以來何曾稍歇,世世傳承而來,把當下情景與六朝以降的登高情境、感懷寫得精當無比,令人拍案驚喜。
而歷史是無法重履的遠方,其消逝終究是無可挽回的事實,所有的想要把它客觀重現或重演的努力都無法與真實合一。所以唯有遠離歷史的現場讓它在心裡以藝術手腕短暫介入,使之與自己偶然重逢,或才是最能與之貼近的方法。比如在下舉詩作中的努力,張默即以不凡的時空透視力介入再造他的遠方: 穿越空空蕩蕩的大門,緩步入內 驀然瞧見千年前 一隊金盔銀甲的兵士,正在霍霍磨刀 眉宇間,難掩各自的獨孤與無奈 那些等待家書七零八落的歲月 究竟是怎樣一分一秒挨過的 我,徘徊復徘徊,不忍驟然離去 連連自側門的洞口,向外張望 而鋪天蓋地的沙暴,恰似川劇變臉般傳來 同行老麥急急以相機焚燒牆角酣睡已久的積薪 我不得不飛快竄出,深深吁一口氣 ──摘自〈再見,玉門關〉
啊,好一隻歷盡滄桑的燕子 你巍顫顫地站在長江的下游 想呼叫我這個遲遲歸來的過客 在上游用力拉你一把 還是乖乖跟著你一個鷂子翻身 永遠沉入冷冷無聲的水底──摘自〈昂首,燕子磯〉 站立在一八○五年拿破崙指揮法軍作戰的平台,極目四顧,雪原盡處是德俄奧疲憊不堪的軍士,是一團團悶燒的烽火,是僵直的馬群不安的喘息,是戰鼓一陣弱一陣不搭調的敲打,是漫長的忍耐與守候,是一匹匹靜寂召喚著另一匹匹靜寂。
偶爾不遠處三五隻敏捷的野兔,突然在雪地上飛竄、倒立、啄食,甚或推雲捉雨,企圖把藍藍如洗的天空扯下來,當棉被蓋。 由是,我也顧不了雪的暴起暴落的逃亡,逕自張開獨孤的雙臂,向一面陰森,直立如刀的巨大峭壁,衝去──〈雪暴起暴落的逃亡〉後三段 〈再見,玉門關〉像是誤闖歷史現場的現代旅人,必須「以相機焚燒牆角酣睡已久的積薪」才得脫身﹔〈昂首,燕子磯〉是把燕子磯活體化為一隻燕,互憐身世,有欲與之相約沉淪的悲嘆感;〈雪暴起暴落的逃亡〉再造且並置了歷史、自然,與個人當下的多重時空,顯現了戰場的廣闊無垠及淒涼畫面。這些詩段具體呈現了張默能將現代與過去結合、當下與遠方同一、自身與歷史相互滲透的手腕,是旅行者在其漫長的行腳中穿越不同時空時對遠方的重塑與創新。此項發展顯示了張默的行囊早已有了嶄新的包紮方法、拆解方向,和新形式的重組企圖。
結語 張默那一代人一生所體會到的由低谷到高峰所折疊出的詩的「魅力之所在」,如他所言,是一系列「冷冽又熱熾」、殘酷又冰冷的歷史現實所鍛造出來的,但他們一生所擁有的流逝的「鮮脆」,絕對是少有前例的,包括曾經旅行的長度、高度、和寬度,對歷代詩人而言絕對是空前的。他們朝思夢想的「遠方」,其實是一殘忍的現實所逼迫出的,尤其是大陸老家的變幻和失落,因此張默不斷地包紮和拆解的行囊其實是「一箱歷史的傷口」,他環繞著地球跑了幾十個國家,但離那箱傷口始終不遠,他不斷地變換、更新、麗美他包紮和拆解的方式,都只為了跟那遠方說再見,但時代和現實的亂、痛、和分割,只使得他對遠方的感受越來越深沉。因此其行旅過的痕跡,特別是這本詩集的斑斑履痕,正好印証了他們那一代人被「時代重磅的鋤」所砍伐過的痕跡,以是,它不只是張默的足印所堆疊出來的一本特殊的詩集,它的上頭也深深踏滿了歷史無情地履過的大腳印。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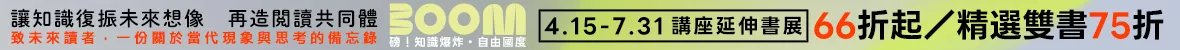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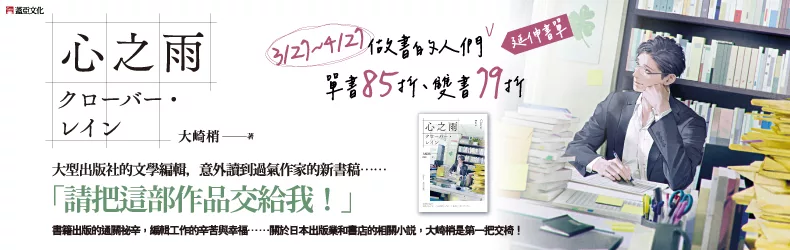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