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小說是一部藝術作品,多數是由於它與生活之間無法
估量的差別,而較少是因為它與生活有著必然的相似。」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文革第一個冬天:從狂熱荒誕到迷茫迷失
—為胡發雲《迷冬》序言[1]
朱嘉明(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客座教授)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氣溫零下27.4度,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今北京的最低溫度。至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冬天北京的氣溫,雖然沒有直接的氣象資料,在我的記憶中是相當寒冷的。此時此刻,以「紅二代」為核心的紅衛兵運動伴隨著毛澤東在十一月裡的最後幾次接見,迅速地由盛轉衰。但是,文化大革命卻是方興未艾。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全面奪權」為標誌的「一月風暴」席捲中國;二月五日,上海召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
[2]雖然這個「新」政權形式僅僅存在18天,它卻根本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的政治格局。胡發雲的《迷冬》,所寫的就是這個冬天,只不過,它不是北京的冬天,也不是上海的冬天,是一個叫作「湖城」的冬天,一個省會城市的冬天。
文化大革命爆發於一九六六年六月,此時的共產黨執政十七年,距前清傾覆和五四運動半個世紀左右。在此期間,雖然全國性的政治運動—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四清
[3],持續不斷,與此同時,最高統治階層內部的嚴酷鬥爭,也一天沒有停止。但是,這樣的政治運動和黨內鬥爭,對精英階層衝擊甚巨,卻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特別是大眾的生活方式,所謂「舊中國」特徵依然頑強地存在,俯拾皆是。原因十分簡單:政權更迭,百姓未變。一九六六年的中國人口是7.5億,城市化率約18%。
[4]中國人口的大部分,出生和生活於一九四九年之前。人們的衣食住行,言談舉止和思維模式,還在歷史的慣性之中,而且是越接近社會底層,越是如此。政府可以重編教科書,卻不可能把教師通通換掉。「共產黨來了,幾批人一殺,幾批人一關,運動一個接一個,都是又好聽又好懂的一些話,便將他們弄糊塗了。但是骨子裡,還是舊社會那一套多,對於權威,敬畏甚於誠服。民間依然存在著傳統的情感體系和利益選擇方式。民間倫理常常重於正統意識形態。「這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見的。這樣一種張力,一直或隱或顯地存在著。這些,都是統治者不願意看到的,他們更願意看到每年的國慶日、五一勞動節,人民在自己的安排下,花花綠綠浩浩蕩蕩走過那個鮮花掩映的檢閱台,喊著響亮的口號唱著豪邁的歌,一派歌舞昇平歡樂盛世景象」。
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不足半年時間,在第一個冬天到來時,中國社會的斷裂性地「解構」,原本社會基礎和紐帶的毀滅性摧毀。這種現象,實為中國歷史所少有。至少,自清軍入關,歷經三百餘年,發生太平天國、庚子之亂、辛亥革命和對日戰爭、國共內戰,都未曾發生。
此次中國社會被徹底「解構」,是以將人與家庭分類和分裂為突破口的。而分類和分裂,則是基於「血統論」的鼓吹、強加和蔓延,進而成為強制性政治觀念。共產主義基於階級鬥爭理論要實現「自由人共同體」。共產黨執政以來,鎮壓和剝奪地主和資本家,老百姓接受了。經過五十年代的土改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所謂「剝削階級」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可是,偏偏在這時候,中國又進入講階級出身的時代。文化大革命初始,人和家庭,包括青少年和兒童,被劃分為不同「類別」:即「紅五類」、「黑五類」,還有處於中間的「灰五類」。「黑五類」就如同「當年猶太人的六角胸符」。這樣的「血緣色譜」,賦予「紅五類」對「黑五類」擁有天然的羞辱、甚至生殺權力。於是,「那些曾經朝夕相處的同窗們,昨天還在一個籃框下『打半場』或在一個床頭前洗屁股,今天,一些人成為紅色,一些人成為黑色。紅色的,理直氣壯豪情滿懷地批判、羞辱或毆打黑色。黑色的,痛哭流涕或強裝卑下地自我批判接受羞辱和毆打。而那些灰色者,必須真誠地贊同紅色們的革命行為,並與黑色者劃清界限」。即使在五十年前,人類已經進入太空、電腦硬體和軟體重大突破,互聯網最初理論已經出現,甲殼蟲樂隊(The Beatles)代表的搖滾樂音樂和思想,後現代主義美術風靡世界,各種新的哲學概念改變著人們思維方式。所以,從「血統論」或者「出身論」出生的那個時刻,就是一種反現代文明的愚昧、陳腐和荒謬的非理性思潮,也有悖執著當所公開宣稱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卻可以將「血統論」和諸如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衛紅色江山,世界革命,革命接班人的「理念」結合起來,構造成不容質疑的「真理」,人為造成社會成員與生俱有的「不平等」,一部分人可以天然地壓迫另一部分人。因為「自來紅萬歲」和「紅色恐怖萬歲」是不可分割的。於是,以「理性」外衣的非理性思潮,與非理性的年輕人結合,造就了超越法律和實施暴力的空前能量,山呼海嘯般地撕裂原本堅固的傳統社會結構,以求「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
[5]。遇羅克
[6]撰寫的〈出身論〉,展現了「血統論」荒謬本質,解釋了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邏輯」,即發動文化大革命和「血統論」之間的邏輯關係,而慘遭槍決。如今回過頭看,沒有「血統論」,文化大革命實在難以發端,「血統論」確是文革的「第一推動力」。後來的歷史不斷告訴人們,「血統論」從來沒有真正消亡,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以這樣和那樣的方式影響著中國的演變。
[1]我與胡發雲是同代人。文革時,他在武漢,高中生;我在北京,初中生。三年前,我們在維也納做過長時間的廣泛交談,其中的一個主題就是「文革」。那時我發現,發雲以其文學家的藝術思維和氣質,對於在文革中的的整體認識和分析,特別是在諸多的歷史細節上,竟與偏重邏輯、學術和歷史思維的我,是那樣的接近,甚至重合。之後,發雲贈我《迷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O一三年一月),我連夜讀完,喚醒了那個年代的許多記憶,頗受觸動。最近,發雲的《迷冬》將由臺灣的南方家園出版社出版臺灣版本,邀請我這個非文學中人寫一個序言時,我接受下來。因為,在一個輕浮的時代,像胡發雲這樣,以小說的形式還原「文革」的,特別稀少和珍貴。還因為,今年畢竟是文革發動五十週年。不要說我們的父輩,即使我們這代人,也在老去和凋零。深化對文革的認識,實在是一份難以推辭歷史責任。
[3]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四清,均是政治運動的簡稱。
[4]李善同、劉雲中(1999),〈中國城市化的歷程、現狀和問題〉,《資料通訊》,一九九九年第九期。
[6]遇羅克(1942-1970):男,中國北京人。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學。之後當過學徒工和代課教師。一九六六年冬以「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為筆名,寫了六期《中學文革報》的頭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出身論〉,全國反響巨大。遇羅克於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被捕,一九七O年三月五日和另十九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上,被宣判死刑並被執行槍決。
自序
這世上沒有與你無關的事
—致臺灣讀者
胡發雲
我記事很早,清晰且得到證實的,大約是三四歲的事,在我們家那個臨江的陽台上,用粉筆畫長江上來來往往的「洋船」,粗矮的煙囪裡冒著黑煙向後飄去,江面上有一些倒人字形的江鷗,遠方還有一片片小小的風帆。恍惚迷蒙、似真似幻的,應該是一歲左右的—比如五十年代,一位姓孫的伯伯,父親的老同事,來家時說起一九四九年末,在重慶一個舊貨市場上,我將人家的一隻大花瓶拉倒摔碎了,我竟有隱約的印象,腦子裡浮現出當時的場景。後來我想,也許是我早年在長輩們還不太避諱我的時候,談一些有關我的往事,我在想像中將它們復活了。
詭異的是,後來,我父母再也沒有提及過我和重慶有什麼關係。
我的很多記憶,都與畫面、情景、氣息、味道,特別是與旋律相關。比如桃子的香味,可以讓我記起童年住過的那條街道;汽油味,會讓我想起我們樓下馬路雨後積水上面那薄薄一層五彩斑斕的油花;一塊熟悉的香皂,會想起兒時的房間,和房間裡的一些故事。
我第一次知道「臺灣」,是我五六歲的時候。鄰居家有個男孩,比我大一兩歲,叫小寶,已經上小學一年級了。一天他放學回來,告訴我說,他們今天學了一首歌,叫〈我愛我的臺灣島〉,說著就給我唱起來:「我愛我的臺灣喲,臺灣是我家鄉。過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我們要回到祖國的懷抱,兄弟們哪姐妹們,不能再等待……」。小寶說,他唱的時候哭了。我對旋律很敏感,一下就記住了,唱的歌詞似懂非懂,但是「臺灣」這個詞卻記住了。不久,幾個鄰居的孩子在一起說話,說起小寶,說他的爸爸跑到臺灣去了。我這才想起來,真的從來沒有見過小寶的爸爸。他們說這件事的神色和語氣都很詭異,彷彿臺灣是一個很恐怖的地方,跑去的人也是很恐怖的人。待我再長大一點,知道了臺灣是中國最大的壞蛋蔣光頭住的地方,那個地方有很多從中國跑去的壞人,後來認字了,就看見街上有「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大標語。知道了臺灣是一個壞人橫行,好人受難的地方。再聽那首〈我愛我的臺灣島〉,果然就聽出了很多的苦愁。只是我一直沒有弄清楚,小寶唱這首歌哭了,是想他的爸爸呢,還是為那裡受苦的人們傷感?想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已經搬到了一個新建的宿舍區,從此再沒有見到小寶。
我像新中國所有的少年兒童一樣,在「一個世界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社會」裡學習、成長與生活。同情著臺灣人民和「世界上三分之二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受苦人」,並立志要將他們從苦難中「解放出來」。我從小就是一個好學生,品行好,學習好,身體好。剛滿九歲,就加入了「中國少年先鋒隊」,當過中隊長、班長、學習委員、文藝委員。我以為,我從此就是一個「共產主義接班人」了。
進了初中,每個學生都要填寫「家庭出身」。我回家問父親,應該怎麼填,父親有些窘迫也有些為難地告訴我,要填「舊軍醫」。我問什麼是「舊軍醫」,他說,就是國民黨部隊的醫生。這件事,於我來說,不啻於是一道撕裂長空的萬鈞霹靂。原來我的家庭,也和臺灣那些壞蛋一樣,也和小寶的爸爸一樣。但是,我眼前的父親,卻是一個那樣溫和、儒雅、待人彬彬有禮,工作兢兢業業的人,從我們記事起,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有什麼被人詬病的地方,更不消說做什麼不好的事情。街坊鄰里都那樣敬重他,一口一個「胡醫生」,哪家有個三病兩痛,也會來找他,即便是天寒地凍的夜裡來敲門求治,父親也會馬上爬起來,帶上聽診器、壓舌板等等醫療器具跟隨而去。「好人」?「壞人」?十幾年的人生中,我第一次遇上了這樣難以理解的問題。
這個天大的難題,我還沒有找到答案,「家庭出身」的巨石,已經無情地壓在了一個敏感的少年身上。在其後漫長的歲月中,如影隨形,讓我體驗了一種別樣的人生,也讓我思考了比同齡人更多的問題。
後來,讀了更多的書,很多是禁書。瞭解了更多的事,很多是老師、父母、報紙廣播不告訴我的事。看到了更多的世界。特別是父親去世之後,我讀到他留下的各次運動中的有關材料,我終於看到了一個完整的父親。
後來,我有時也兀然想過,一九四九年,重慶那個風雨飄搖的冬季,父親如果做了另一種選擇,我就在懵懵懂懂之中成為了一個臺灣人,或者像我們家族那些赴臺親友的後代一樣,小學中學之後,去到第三國—英國、泰國、美國、澳大利亞繼續深造並留在那裡,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甚至華文華語華夏文明和神州歷史,都會變成與己無關的遠方與過去。
我們胡家,明末自江西移居武漢,至今已近四百年。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我這個長子長孫在離祖屋不遠的普愛醫院出生。那是一家建於一八六四年的教會醫院,也是湖北省最早的西醫院。那時,父親歷經顛沛流離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加三年內戰,剛剛回到暌違已久的故鄉,祖孫三代父輩兄妹五家數十人,終於有了一九三八年武漢保衛戰結束之後的第一次大團聚。
我出生的那一天,國民政府向美、蘇、英、法四國發出外交照會,希望各國參與中國的內戰調停,促成國共和談,未果。不能打,也不能和,十三天之後,老蔣黯然下野。於是,便有了時任漢口軍醫署第二休養總隊醫務主任的父親在履歷中記錄的「偽總隊奉偽軍醫所的命令向重慶遷移」。
此次遷移,幾乎重複了一九三八年那一條相同的路線,只不過那次的傷病員是從抗日戰場上抬下來的,這一次是中國人的自相殘殺。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剛剛滿月,便在襁褓裡與父母一起踏上了西撤的漫漫長途。歷經五個月,七月到達重慶。
十一月底鄧小平劉伯承的二野大軍進入重慶。在這之前,父親是有機會去臺的,他當時已是休養大隊負責人。但是他放棄了,守護著全隊設備藥品,還有那些傷病員,等待一次歷史的大更迭。父親也可以進入共產黨的軍隊醫院的,但是他也放棄了。大陸官至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父親吳忠性,曾與我父親同在蘇州「中央陸地測量學校」任職,一個是教官,一個是校醫,年齡、資歷、官階都很相近,連兩次西撤的時間、路線都差不多。在中共軍隊佔領重慶之後,他選擇了帶領測繪人員和設備加入了共產黨軍隊。
父親是一個不懂政治的人,認為治病救人,懸壺濟世,是醫生的天職。他後來才知道,有一些人,哪怕是保家衛國浴血殺敵的手足同胞,也是不可以被救治的。救治他們,就等於是他們的幫兇,是人民的敵人。這些在文革中成為組織和群眾對他說得最多的批判用語,後來也成為父親對自己罪行的批判用語。
一段漫長的軍旅生涯終於結束了,十多年的腥風血雨也停息了。他當年拿著二野軍代處發給的批文與路費,將妻攜子乘舟東下時,大概沒有預料到,其後數十年中,還有著那麼漫長的階級鬥爭的疾風暴雨在等待著他。
我的書桌上,放著一張照片,是父母和幼年的我。這張照片一直都在家裡的:母親穿著旗袍高跟鞋,抱著我。父親長褲襯衣,側後站立。父母臉上都是安寧幸福的微笑,一點也沒有一支敵對大軍兵臨城下的驚慌與恐懼。倒是不到一歲的我,眼裡充滿疑惑和思慮,和那種年齡很不相符。
很久以後,我才發現這張照片是在重慶拍的,(我的另一張同時期的單人照背後,有父親用小楷寫的「發雲半歲」幾個字,但是攝影日期地點卻被墨去,對著燈光可顯出「重慶」的字樣。看來,父親不希望我們知道他和重慶的關係。)仔細看,父親穿的是夏季的軍便裝,肩頭還隱約看得見肩章扣帶。這是父親唯一一張和他軍旅生活有關聯的照片。所有與此相關的物件都毀掉了—日記、信件、照片、手槍、中正劍,各種可能會帶來麻煩的衣物和用品,還有他及他的親人們關於這一切的記憶。
《迷冬》的各色人等中,不少與臺灣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有的是=逃臺」人員家屬,有的服務過那個萬惡的「逃臺政府」,還有一位京劇名家,與蔣介石合過影……在大陸數十年各種運動中,這一類人隨時都是刀俎魚肉。到了文革,就更是火烤油煎九死一生。
兩個政權的血戰與對峙,造成了百萬計的家庭撕裂,更造成數以千萬計的民眾塗炭。一灣淺淺的海峽,隔開了兩個互為妖魔的世界也割斷了萬千家庭的血肉聯繫。
一九七O年代後期,兩岸的鐵幕終於鑿開了一絲縫隙,一九八七年,臺灣放行赴大陸探親,一批批各種臺灣人來到大陸,那是一部令人心碎的悲情連續劇。不論是曾與共軍廝殺過的國軍老兵,還是國民黨「壓迫下」的勞苦大眾,不論是半生孤單的老父,還是已經兒女成群的兒子……大陸人終於看到了活生生的臺灣人,看到了他們的富裕,看到了他們的自由。不久,又有更多的臺灣人來到大陸建廠開店做貿易,一時間成為各地政府的座上賓。可以說,以經濟活動為主導的兩岸關係,讓臺海兩岸第一次祛魅了。
後來知道,那個看似與大陸制度迥異互相對立的政權,也有過與大陸的相似社會歷程—「二二八」事件、《自由中國》案、「保釣運動」、「美麗島事件」……知道了我們的湖北老鄉殷海光,知道了雷震,知道了陳映真、許信良、施明德、林義雄,知道了我的漢口老鄉詩人彭邦禎和他那首譜成曲的〈月之故鄉〉……也知道了在對付民主自由的訴求上,這兩個政黨,曾有著那麼多的相似之處,連許多用語、口號、歌曲、宣傳畫甚至罪名和懲治手法……都兩兩互為鏡像,左右對稱。只是相比起來,海峽那邊還是要溫和節制得多,有著更大的彈性。這也是後來臺灣走上一條新路的條件之一。
知道了這些,令我驚異的是,我發現我的同情與支持,依然在反對派一邊,也就是說,哪怕我當年隨父母去了臺灣,我大概也是一個社會的批評者。
同時我也發現了,那個看起來與我們已經毫無瓜葛且孤懸海外的小島,對於大陸來說,同樣也具有重大的意義。他們在前進路上的每一步,都成為我們的樣本與參照。
我明白了,這世界上沒有與你無關的事。如果沒有一九八七年臺灣的戒嚴開禁,我們會認為這樣的日子將天長地久遙遙無期。如果沒有後來的大選,我們會認為這個民族—包括臺海兩岸,永遠不配享用這薄薄的一張選票。
同樣,臺灣也不能把大陸的一系列社會政治災難—特別是文革,看成是隔岸觀火與己無關的一齣鬧劇。它代表著一種黑暗與暴力的價值觀,考驗著我們的心靈與精神。當這世界上還有一個人不自由,便是這世界的不自由。當這世界上還有一個人在受難,便是這個世界的受難。一粒小小的病毒,它的存在,意味著整個世界可能被感染。同樣,文革的瘋狂,也是這個世界的瘋狂。當一個獨裁者的個人意志可以操控八億大國的時候,它的破壞力是無邊界的。
今年是大陸文革五十週年。文革的幽靈從來沒有離去。時至今日,我們又聞到那股令人窒息的氣味,它愈來愈濃郁地向我們逼近了。
在距今十九年前的一九九七年,我在一家名為《今日名流》的刊物舉辦的座談會上,做過這樣的發言:
「文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並沒有結束,它在政治上、組織上、意識形態上,及其他種種依存關係上,依然制約著我們對文革的正常表述或思考。
至今為止,我們對『文革』的研究依然是在一種強勢語言的解釋下進行,有很多規定好了的表述不能突破。
首先有必要對文革的過程和事件進行一種清理。文革像一頭極其巨大的象,我們每個人都只摸到它的某個局部。要把事件本身弄清楚,這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全國各地、各種派別、各種觀點、各種階級地位、各種不同結局的人都能夠參與。重要的一點,文革是億萬人投入的政治事件,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同時它又提供了巨大的資源,如果我們付出了這樣的代價又不利用這種資源,那就比付出代價本身還要可悲了。
還有一批隱匿者,就是今天依然在台上的一部分官員,他們在文革中的經歷,依然是不可言說的。所以,文革最終的結果,是一大批的隱匿者不知躲到哪裡去了。重新尋找這些文革的隱匿者,讓他們重新承擔自己應當承擔的那些責任,讓他們發出自己對歷史該發出的思考,這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要說一下前面提到的那首臺灣民歌。不久前,在成都與臺灣作家楊渡先生聚談,說起這首歌,並唱給他聽。楊渡先生說,這是臺灣的一首愛情歌曲,說著就唱了起來:「我愛我的妹妹啊……」
一首在大陸唱了半個多世紀的歌,原來是個偽託。代臺灣人民訴苦情,寄衷腸。這首歌至今還在大陸流傳,成為學校的音樂教材和歌唱家們的經典曲目。
美國氣象學家洛倫茲說過,亞馬遜雨林一隻蝴蝶搧動翅膀,也許兩週後就會引起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臺海兩岸也好,東西半球也好,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每一家都互為鄰里。隔壁失火,安能自保?我只想說,我的大陸,我的臺灣,我的每一個熱愛自由與幸福的個人,祝福你們!
二O一六年四月八日 武漢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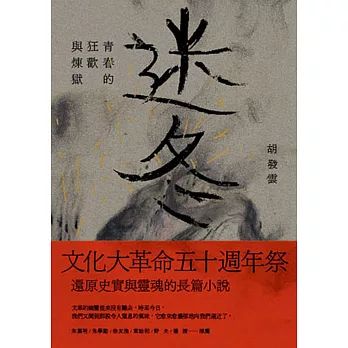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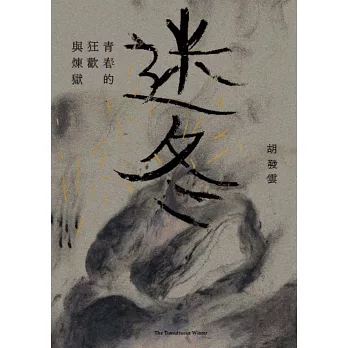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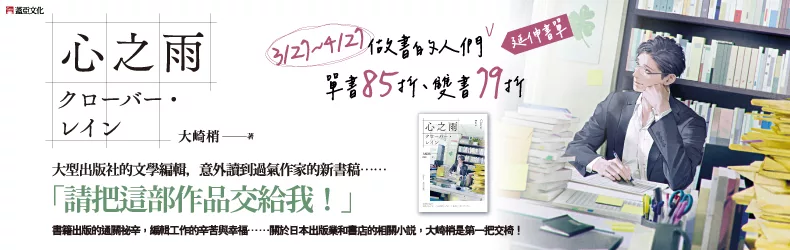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