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台灣天光? 謝清志
我一生被定位為工程科技人員,深知所學有限、知識無止境,所以很少會因參與一件工程、辛苦努力完成,而覺得自己了不起;因為,每件工作,無論大小,都不是我自己一個人能力可單獨完成的。
生活、學業,或事業上,如果有進步與成就,常常是因既存的外在誘因,加上些許的運氣所致;不進步,或失意時,大多又是因自己的努力不夠,也怨不得他人。
這本《謝清志的生命振動》一書,你即將發現,我謝清志跟許多人一樣,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生命個體(菜市仔命);我的生命因起落而生振動,就像一個被擲在地上的籃球,落地反彈,彈高又落地,上下振動,直到力道消失才靜止。
我參與過不少國內外工程科技計畫,每當計畫成功執行完成,身為團隊成員之一的我,得到的褒獎常是一頓慶功宴,有時外加一張感謝狀。感謝狀拿回家掛在牆上,驕我妻及兒女,怡然自得。
然而,二○○一年後,我有幸參與的「南科高鐵減振工程」,結局卻和以往大大不同,所造成的振動特別劇烈,振幅之大,力道之猛,幾乎令我差點倒地不起。
就因靠著大家的扶持,還有老天的幫忙,我終能轉危為安。真是要感謝天,感謝地,感謝大家!
這次的結尾很不一樣,我心已不再憤恨不平,相反地,感覺較以往獲得更多,也更有意義。因為,除了工程科技知識的增進外,我還有了新的學習:(一)親情與友誼間的生命對話及告白;(二)牢內牢外的生活感受;(三)檢調人員、公訴人、被告、證人、律師及法官等司法制度上的角色定位與運作。
這一趟,我身歷其境,一舉數得,不能說值回票價,卻真的不虛此行。
當一個人失去自由,被隔離於社群之外,不能與親人、朋友聯絡,與外界音訊全無時,其情境與死亡相近,有的只是「短暫」與「永別」之分。朋友們,會因此惋惜、同情、憤怒;親人們,則是不捨、失望、絕望、懊悔;但他們無邊的等待,只會讓關心與營救更加無力,有時更是換來自責。同樣地的境遇,也會發生在被隔離的人身上,虧欠、無助、無奈,還有想向親人訴說的衝動,使得他因此說出平常說不出口的話語。這難得的經驗,我願意與大家分享。
我的生命因這五十九天的牢獄生活而增添不少「禪意」。進牢前,渾然不知坐牢這回事;在牢裡,無論如何掙扎、聲嘶力竭,外面親人則完全聽不到。
剛開始,鬥志昂揚,但度日如年,信心也逐漸動搖;本來從未發生的事情,竟然經不起檢方多次訊問,我也懷疑起是否真的發生過!漸漸地,我開始相信那是曾發生過的,繼之,我竟會在訊問者的刻意操作下,深信不疑地認為我確實做了那些不法的事。要說這就是「催眠」、「洗腦」,都十分貼切。
二千多年前,曾參這位中國春秋時期的學者,連殺雞都不敢看,但他的母親在聽別人說了三次「曾參殺人」的傳聞後,竟也緊張得懷疑起「曾參確實殺了人」!在牢裡,我終於體會這二千多年前的心理學問題,因為在那裡「曾參殺人」的戲碼每天都在上演。
我們天天聽「法律人」說,犯罪事實要有證據,而要能證明犯罪的證據,必須要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才可 (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同時,要指控被告有罪,舉證責任在檢方,而不是被告。所以,在檢方舉出證據,在法官宣判以前,被告理應被視為無罪,這就是所謂的「無罪推定原則」及「證據裁判主義」。
不幸的是,台灣檢察官所寫出來的起訴書,幾乎都是以「合理的懷疑」(並不是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來包裝編撰一個犯罪的故事,而被他們用以來佐證這個編撰故事的片面資料,錯誤百出,也就屢見不鮮!
然而,這個含有編撰犯罪故事的起訴書,就是承辦法官在正式開庭前,先收到、先閱讀的東西。可想而知,打從第一次開庭時,許多法官在心理上就已覺得被告有罪,蒞庭審判時反倒要聽聽你這「罪犯」如何證明自己無罪!我十分懷疑,究竟有多少法官在審理過程時,會提醒自己堅守「無罪推定原則」及「證據裁判主義」?
這二年來,我的團隊與律師們就是夜以繼日地努力找證據,為的就是要證明我的無罪;本來,檢察官應負舉證來證明被告有罪的,現在卻變成我這個被告必須舉證來證明我無罪,多麼荒謬!
這就是民主後台灣今日的司法現況。有人說,台灣已經「天光」了,但這樣的檢調系統,卻又令台灣烏雲密布!
而我個人,以五十九天的牢獄,我與其他九位被告,也以近二年來的煎熬,見證了這樣深刻黑暗的現況。
最後,我必須感謝在這段期間給我愛與溫暖、信任與鼓勵的親朋好友,我銘記五內;本書若因內容需要而必須提及您因而帶給您不便,也請見諒!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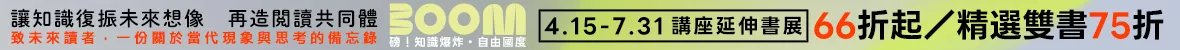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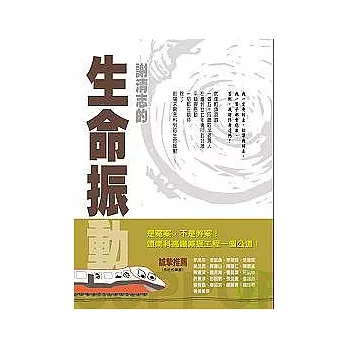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