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永不放棄的追問:寫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成書六十年
無論我們能從以往歷史中學得多少,都不能使我們預知未來--鄂蘭
一、反思二十世紀「人的處境」之經典
《極權主義的起源》是政治哲學家鄂蘭的名著,成書於1949年,初版時名為《我們當前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s)。1951年該書出版時,立即引起政治哲學界的巨大反響,對她的評論產生了對極權主義研究持續不衰的理論熱潮。六十年之後的今天,當我們檢視有關極權主義的種種分析時,則可以發現:無論是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對封閉社會的哲學概括,還是弗里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對黨國體制的社會學研究,以及雷蒙.阿隆對意識形態統治的反思,所有這一切均不如鄂蘭著作的視野深刻和宏大。從歷史的深度和廣度而言,《極權主義的起源》的重要性是無與倫比的,因為它更能代表對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人類困境的反思。
每個時代都存在「反思人的處境」的思想經典,它們是對那個時代社會弊病的深刻揭示,亦是對人應該生活在甚麼樣社會的想像。十九世紀西方反思性著作無疑以馬克思的《資本論》代表。眾所周知,十九世紀最重要的特徵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朝,生產力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超增長。但是所有社會學者都被如下悖論所震撼:為甚麼當社會財富成倍增長(這些財富本來是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但卻有近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赤貧之中,甚至發生了傳統社會都罕有的窮人流離失所?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力圖從理論上回答這個問題。二十世紀則出現了另一個問題,法西斯主義肆虐表明,個人面臨國家和社會愈來愈可怕的壓迫,不僅令思想的尊嚴喪失,連古老的良知和道德都備受踐踏。
二十世紀最令人費解的是,那些本意是促使人類獲得解放的思想突然反過來奴役人類,使人的尊嚴蕩然無存。意識形態本來只是觀念系統,它是人根據某些現代觀念建構出來的產物,然而在二十世紀它居然比一切真實都更強大,對現代人產生了巨大的壓迫。在該書的初版序中,鄂蘭這樣寫道:「反猶主義(不僅僅是仇視猶太人)、帝國主義(不僅僅是征服)、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專政)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比一個更野蠻,這說明人類的尊嚴需要一種新的保障」。但是,當沒有認識到問題出在何處時,又如何為時代作出診斷?更何況提供保障?鄂蘭清晰地意識到,對人最大的壓迫來自於極權主義,而這些制度的背後是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在這些龐然大物面前,我們卻有空前的無力感。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起源於二十世紀二零年代,墨索里尼及其他法西斯領袖常鼓吹「我們革命的總體計劃」,認為他們具有「總體暴力的意志」(feroce volonta totalitaria),極權主義由此得以命名。但在鄂蘭著作之前,人們普遍將其局限在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至多再加上蘇聯斯大林主義統治。鄂蘭意識到,極權主義對人的壓迫,並不因為第三帝國的滅亡而結束,也不會因個別人物的去世而改變,因為其本質根植於現代性本身的展開之中。
據鄂蘭自述,1945年希特勒德國失敗之際,她開始寫作本書;而在斯大林去世前三年,該書初搞完成。她把寫書的這幾年稱為幾十年來的動盪、混亂、恐怖之後的第一個相對平靜時期。實際上,鄂蘭的感覺是對的,正是《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後,極權主義體制的全貌才完全顯現出來,該書的反思價值才真正得以凸顯。
對現代性的反思存在著兩類思想家,一類是把人類的不公平的困境轉化為憤怒反抗的烈火,並在批判中孕育出理想社會的烏托邦。另一類是被對現實深深的無力感所苦,將這種無力感轉化為深層的思考。馬克思屬於前一種,而鄂蘭是後一種。在某種意義上講,後一種思想家更值得我們注意,因為正是這種對現代性展開中顯示出來弊病的無力感,更能代表當今人類的處境。
二、宏大的歷史視野
《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重要性在於從現代性的發展,特別是全球化過程來探討極權主義出現的原因。鄂蘭力圖指出:現代性存在著黑暗面,黑暗時代的來臨有時是不以人們的良好願望而轉移的。極權主義體制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14年前是第一次全球化凱歌進行的太平盛世,當時人類根本無法想像二十世紀會經歷死亡數千萬人口的大浩劫,以及納粹德國和蘇聯的鐵幕統治。鄂蘭相信,必須到十九世紀第一次全球化發生的內在邏輯中去尋找大災難的根源,也就是必須追溯「極權主義因素」(element of totalitarianism)的形成與發展。
十九世紀的全球化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的,第一次大戰的原因是民族國家主權的無約束性,在思想上則可以視為帝俄和東歐的泛斯拉夫主義與德、奧的泛日爾曼主義的衝突;再加上納粹德國建立在反猶主義之上的意識形態恐怖統治,於是「反猶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及泛日爾曼主義」成為鄂蘭重點追溯的對象,《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論證正是圍繞著這些主題展開的。它由「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統治)」三個邏輯環節組成。
第一環節反猶主義意識形態的起源寫得極為精彩。鄂蘭指出,反猶主義和西方中世紀以來的排猶傳統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1870年以後在西方出現的全新思潮。法國大革命後西方基督教共同體已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猶太人本已作為「國民」融入不同的民族國家之中;那麼,為甚麼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西方又普遍出現了反猶主義呢?鄂蘭認為,反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泛」化是同步的,其背後是西方民族國家的性質發生變化。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二部分〈帝國主義〉中,鄂蘭展開了對西方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變構的深入分析。十九世紀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西方對現代化後進地區的衝擊。鄂蘭認為,正是資本的不斷向全球擴張,摧毀了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結構。當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征服殖民地、輸出資本,同時又無法解決本國的失業問題時,控制廣大殖民地的列強已經變質,已不再是現代社會剛形成之際那種保障公民權利的民族國家,而是帝國主義了。其民族主義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推動下迅速演變成種族主義,進一步促使泛日爾曼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的泛瀾,反猶主義只是其極端形態罷了!
接下來,鄂蘭詳細描繪了資本的擴張,如何把擁有私有財產的個人轉化為追求私欲、漠視公共生活的群眾。暴民政治和所謂意識形態精英的結合,產生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極權主義體制。它通過假立法(pseudolegal)和革命在德國和蘇聯大行其道。假、大、空的意識形態在英雄主義口號下摧毀人的良知,形成洋蔥般中空的意識形態統治。她的結論觸目驚心,因為如果她是對的,現代性遵循全球化道路的發展,存在著自我毀滅的邏輯。
三、反思和疑惑
鄂蘭的著作引起了歷史學家持久的爭論和政治哲學家的廣泛批評。最大的問題是她的論證邏輯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質。因為被鄂蘭視為導致極權主義因素形成之原因恰恰是現代性本身以及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在整個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包括種族民族主義都是建立民族國家的積極力量,即使泛斯拉夫主義和泛日爾曼主義亦是如此。沒有泛斯拉夫主義,就無法理解俄國1850年以後放棄農奴制的改革和1905年後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化。同樣,脫離泛日爾曼主義,也無法認識德國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奧匈帝國的現代化。
更重要的是,離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契約共同體,我們無法想像人類現代世界的秩序。為甚麼民族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後會指向民族國家之間毀滅性的戰爭,而不是形成遵循國際法的民族大家庭?僅僅從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其種族主義轉向是缺乏說服力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戰鬥權利論」訴諸強者的權利,在相當程度上為弱肉強食辯護,有人認為它應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負思想責任。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社會達爾文主義崇尚市場機制為上帝的法則,這本是十九世紀全球市場形成的基本動力。正是借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公理」,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初接受了人權觀念,並開始為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而奮鬥。歷史的吊詭在於:中國接受意識形態統治、進入極權主義體制,恰恰是在新文化運動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後。
《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理論最脆弱的部分,是帝國主義說。現代意義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一詞,是1870年後才出現在西方政治詞彙中,其原意是用軍事力量控制殖民地,並將其納入自身的經濟體系;暗含著西方現代文明的「教化使命」(civilization mission)。在中國,是梁啟超最早在1901年將「民族主義」一詞引進中國,以鼓動國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當時,「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也會混用。從當時「民族帝國主義」一詞盛行來看,「帝國主義」只是現代民族主義形成時西方現代文明擴張的別名。馬克思著作中,從未用過「帝國主義」一詞。使「帝國主義」一詞真正脫離現代自由主義語境,是列寧1916年出版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一書。從此以後,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與馬列主義一起傳播。列寧之所以可以將帝國主義說引進馬克思主義,是受到1902年出版的霍布森(J. A. Hobson)《帝國主義研究》的影響。但霍布森本人仍是在經濟自由主義框架中討論帝國主義的。這樣一來,鄂蘭就面臨理論上的兩難:要不,堅持帝國主義說使她和她的反對對象站在一起;要不,她作為馬列主義的不留情的批判者,就只能回到霍布森的原點,從而不能證明帝國主義來自於民族國家的畸變。
鄂蘭描繪資本的擴張性確實一針見血,但真的是因為資本的擴張就能把擁有私有財產的個人轉化為追求私欲、漠視公共生活的群眾嗎?資本擴張真的是暴民政治和意識形態精英結合的原動力嗎?如果真是這樣,今天又應怎樣看待資本的輸出?我們知道,把個人「私產」不斷變成再投資的「資產」是全球化的本質,如果它曾導致民族國家變為帝國主義,使公民變為暴民,那麼,我們又應該怎樣理解及評價今日的全球化?反之,立足於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的經驗,人們自然會問:在歷史上是否真的出現過帝國主義?用第一次全球化過程中資本輸出來討論帝國主義之出現,並用此解釋反猶主義和極權主義興起,這是否只是經濟決定論的一種幻象?
四、極權主義的三種形態
其實,要鄂蘭來回答這些問題是不公平的。因為她主要是就納粹德國的歷史經驗來探討極權主義的起源,只是提出了問題而不可能回答問題。《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一種鄂蘭完全不理解的道德意識形態統治方式正在形成。在中國,不僅革命的意義和蘇聯不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運動和造反風暴也不是基於種族民族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模式所能理解的。
必須強調的是,鄂蘭一直對蘇聯共產主義實踐的本質存在誤解,對中國則更缺乏認識。如果一定要把黨國體制歸為「極權主義」,那麼蘇聯和中國的歷史經驗遠遠不是《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所能概括的。在德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源於種族民族主義,極權主義統治來自於民族國家的畸型變構,這一點並無疑義。但蘇聯和中共的意識形態統治卻不是這樣,它與民族主義的關係並不密切。其實,與其說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還不如說是世界主義更為妥切。意識形態態統治在東方的出現和民族國家的資本輸出也沒有太大的關係,相反,倒是俄國和中國在建立民族國家的失敗,使得社會現代轉型中發生了整合危機,從而才導致了黨國體制的確立。雖然,從現象上講,蘇聯和中國的意識形態態統治和德國有極大不同,但有它們在一個深層要素卻高度一致,這就是在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個人權利這一核心價值的缺位。
帝俄在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化的過程中,需要借助於斯拉夫民族認同,故從1850年代起就鼓吹泛斯拉夫主義。然而,正是泛斯拉夫主義使俄國不可避免地深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在此過程中發生社會整合的解體。為了實現社會再整合並退出一戰,蘇聯是用世界主義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為其提供正當性。我們看到,極權主義在俄國的形成機制與德國是不同的,畸型民族主義在俄國無所作為。蘇聯的歷史表明,個人之所以會受到國家和社會的壓迫,乃源於向西方學習的失敗和帝俄社會整合傳統的復活。俄國東正教傳統中,本來就缺乏西方新教中自然法和自然權利觀念。馬克思主義作為對西方現代性之批判,以「一切權利都是階級的權利」為名義否定個人權利是普世價值,代之於平等和人的解放。但是,當人權缺位時,平等和人的解放又如何可能?歷史總是這樣,思想的缺陷只有在它充分轉化為實踐時才會暴露。故當列寧主義和米爾傳統結合轉化為俄國革命時,俄國長達70年的學習現代價值建立民族國家亦隨之中斷,個人權利的缺位使得意識形態恐怖統治得以出現。黨一定會凌駕在法律之上。
在中國發生的一切,則更令人觸目驚心。雖然中國在1911年沒有經過太大的社會動亂就由帝國轉化為共和國,但和俄國類似,中國亦發生了現代轉型過程中社會整合的解體。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正是對嚴重的社會整合危機的思想回應。新文化運動作為第一次啟蒙,在運動早期把個人權利觀念引進家族內部,通過全盤反傳統、重新評估一切價值,使中國人思想得到真正的解放。但是,新文化運動還必須面對向西方學習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所帶來社會整合危機的現實。因此,正是在新文化運動後期,中國知識分子對引進的西方現代價值進行了重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觀念,並建立了新的道德意識形態。新文化運動後,國共兩黨都選擇了用革命道德意識形態去實現社會整合,以克服日益嚴重的社會脫序,這就是1920年代及以後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中國亦用黨國體制實現了社會整合,建立了一個由超級官僚機構統治的新社會。
與俄國不同,中國本來就有用道德意識形態整合社會的傳統。故在中國,用新道德意識形態整合社會不僅是舊瓶裝新酒,「革命」甚至有傳統朝代循環的影子;而且,到文革時,壓迫個人的群眾運動居然是以做無產階級聖人名義展開的。因此,鄂蘭根據納粹德國的分析,得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統治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它伴隨著人道德倫喪這兩個論斷,都與中國情況不符。
在西方和蘇聯極權主義體制中,法制因意識形態凌駕在其之上而被破壞,極權主義往往可以等同於意識形態統治。但在中國社會特殊的整合模式中,人尊嚴的喪失並不一定與意識形態統治相關聯。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告別革命,馬列意識形態解構了,但黨國體制並沒有隨之解體,對個人的壓迫並沒有消失,人們仍然生活在恐懼之中,仍可能不經審判被監禁,仍可能以言論而被治罪,和以前不同的只不過不再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是訴諸於危害國家安全、洩密或被指控為貪污。我們想強調的是,無論中國的共產革命和蘇聯有多大不同,無論是在毛澤東時代或當今,中國盛行的當代價值系統中,人權始終是缺位的,這與蘇聯以及當年的德國一模一樣。
個人權利觀念在1895年後被引進中國,在中國傳統社會現代轉型建立民族國家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在新文化運動早期,人權觀念進入家族內部,中國人思想得到極大的解放。但是,新文化運動是一次被中斷的啟蒙,正是在新文化運動後期,個人權利被等同於階級的權利,人權觀念被重構,形成中國式的個人觀念。這一切都反映在五四後各式各樣的當代意識形態之中,其目標和價值雖不相同,但在對現代性的理解中個人權利的缺位卻如出一轍。
五、永不放棄的追問
換言之,只有將俄國和中國的歷史經驗加到極權主義起源的研究中,我們才能看到個人如何受國家和社會壓迫的完整圖畫,才能理解極權主義的本質。法國大革命後,隨著現代性三大基礎,即「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民族認同」成熟,十九世紀前半葉實為這三大價值轉化為實踐的時期,它表現為民族國家的建立與全球市場經濟的形成。當時,民族認同與個人權利並行不悖,民族主義的勃興是和自由人權追求緊密相聯。正因為人權價值的存在,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仍然是健康的。十九世紀所有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均以立憲為標誌,故民族國家建立亦意味著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
那時,被鄂蘭視為民族國家開始畸變的1870年代發生了甚麼呢?我們發現,這正是全球性不受控制的發生經濟危機的時期。雖然早在1820年代商業循環已在英國發生,但全球性金融危機最早發生在1873年。當時,西方出現了金融恐慌,德國從1874年至1883年幾乎沒有經濟增長,整個社會大難臨頭,幾乎回到野蠻狀態。全靠1880年代的各國軍備競賽挽救了大蕭條。事實上,正是經濟危機使人們懷疑市場社會的正當性,從而導致作為現代性基礎的個人權利發生動搖。
確實,當在經濟危機來臨時,廣大工人找不到工作做,人的生存權受到威脅,個人權利這種基本價值的可欲性受到破壞。這時,個人權利作為政治和經濟制度正當性的基礎受到懷疑,把國家主權視為國民人權合成也失去了意義。也就是說,現代市場經濟的不穩定,會導致人們重構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一些人在否定把人權作為現代性最基本的價值前提下,重新探討現代社會組織藍圖。1870年代正是個人權利從現代性價值中退隱的開始,馬克思主義用平等代替個人權利,而與個人權利分道揚鑣的種族民族主義因此也越演越烈。
對此,鄂蘭有詳細論述,只不過她完全忽略了馬克思主義興起的原因以及對現代性的批判。鄂蘭的最大問題是將個人權利的失落視為極權主義興起(或促使極權主義興起的因素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極權主義出現的原因。這一切導致她為拯救現代性所開出的藥方是回到古希臘羅馬共和主義中去。我想,這和鄂蘭一直在邊緣闡述問題有關,即她沒有重視馬克思主義作為對現代價值的全盤否定並在19世紀的現代性失敗中轉化為實踐的意義。鄂蘭不能對馬列主義在現代性中加以定位(但她又不能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不能不說是鄂蘭的不幸,這也是一個思想家受到她批判對象限制的最好例子。
事實上,納粹主義在德國的產生,是直接源於1929年的大蕭條,這不僅是個人權利和民主憲政備受質疑的時代,還是馬列主義勃興、社會主義在道義上完全壓倒自由主義的時期。法西斯主義在這時出現是耐人尋味的。眾所周知,法西斯主義舉起左手打倒自由主義,舉起右手反對馬列主義。其本質正在於用取消人權的民族主義來對抗共產主義。
而共產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則開啟了另一個方向的探索,在提倡平等用世界主義取代民族主義這些維度上,它和法西斯主義有完全不同本質和價值取向。對於俄國和中國,為了解決現代轉型中社會整合解體問題,必須在建立現代國家的同時對源於西方的現代價值的進行再塑造,開始了多元現代性之探索。特別是在中國,社會整合危機,使得融合外來文化的歷史傳統與社會現代轉型結合起來,其意義是不可抹殺的。但是,二十世紀大規模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又終於證明了個人權利的缺位是無法建立良好的現代社會的。即使是把平等作為核心價值,用道德理想主義來動員群眾,亦會對個人產生巨大的壓迫,出現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民族浩劫。
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現代性必須建立在「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民族認同」三大價值之上,如果在這三大價值中抽掉個人權利,無論出現何種形態的現代社會,極權主義的性質必定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顯現。納粹德國和與其對立的蘇聯和中國,極端差異中的相似正在於此。由此可見,現代性三大基礎缺一不可,一旦否定人權,民族主義和工具理性結合會導致可怕的結果。而在人權缺位前提下追求理想社會,亦只能是道德烏托邦。
二十世紀的歷史經驗給當今人類留下了豐盛的遺產和教訓。今天,我們面臨全球化和市場社會帶來的種種問題,人愈來愈依賴社會,個人的創造性正在被消費社會窒息。當我們力圖去探索一個更符合人性的社會時,必須充分重視二十世紀的經驗和梳理歷史的教訓。在這一意義上,鄂蘭的著作永遠值得後繼者反覆閱讀,因為正是自她開始,政治哲學對人的處境進行永不放棄的追問。今後的極權主義研究必須站在鄂蘭肩上。
金觀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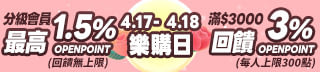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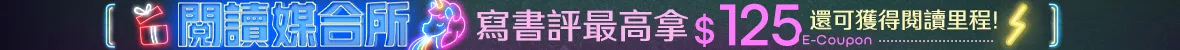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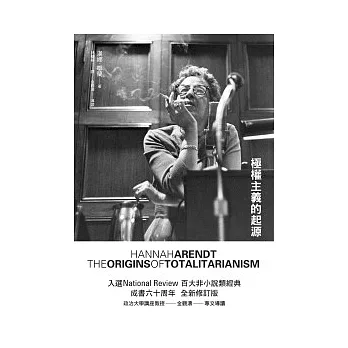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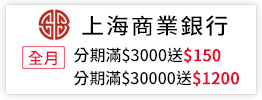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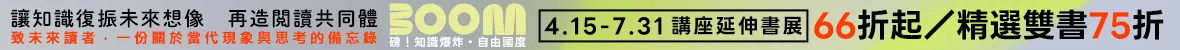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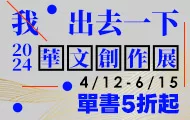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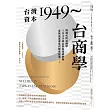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