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迷宮
命名,是人類重大又嚴肅的慰藉。
(伊利亞.卡內提,《蒼蠅的苦痛》)
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力量驅使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放著安穩日子不過,非要窮盡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物。若說這事孩童的遊戲,只是一種假扮──為文談論寫作的人常這樣向你保證──又該怎麼解釋這些人何以一心一意只想、只願、只要寫作,還認為寫作是一項合理的職業,就像把騎腳踏車上阿爾卑斯山當成職業一樣合理?
(梅維絲.加蘭,《短篇小說集》序)
你身在洞裡,在洞底,幾乎全然孤寂,發現只有寫作能拯救你。對一本書要寫什麼主題全無概念、全無想法,便是要再度回到書前面對書。一片廣大的空無。一本可能的書。面對無物。面對某種類似生活的東西,赤裸的寫作,一種必須克服的可怕的東西。
(瑪格莉特.莒哈絲,《寫作》)
1960年代初期,我唸英國文學時,所有學生必讀的一本重要評論作品是《模稜七式》(1930)。驚人的是,威廉.燕卜蓀寫作這本博學的作品時年僅二十三歲。同樣驚人的是,他正苦心孤詣撰寫這本書之際,卻被劍橋大學開除了,原因是在他房裡發現避孕用品。
這個例子很適切地說明了我們都受限於年代,不是像琥珀裡的蒼蠅那麼僵硬透明,而比較像糖蜜中的老鼠;換作今天,他若被開除一定是因為房裡「沒有」避孕用品。聽起來,二十三歲的威廉.燕卜蓀不只精力充沛,也是個明智體貼的年輕人,且並未因遭受挫折而放棄。因為當有關單位邀我來劍橋大學主持2000年的燕卜蓀講座── 一系列共六場的演講,聽眾不只是學者與學生,也包括一般大眾──我很高興地答應了。
或者應該說,我剛接到邀請時是很高興的──當這種差事遠在兩年之後,感覺起來都很輕鬆愉快,但隨著講座日期逐漸接近,我就一天比一天更高興不起來了。
基本上,講座的廣泛主題是「寫作」,或者「身為作家」,而既然我從事寫作又是個作家,想來應該有話可說。我原本也是這麼以為。當時我的構想有著宏大的架構,要檢視長久以來作家建構的各種自我形象──也可以說是描述這行的工作內容。我打算以不那麼技術性的方式來進行,而除非絕對必要,也不會引用鮮為人知的字句;此外我還會順道加進個人寶貴經驗與洞見,如此一來不僅多了些「人情味」(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說裡那些作假的記者常這麼說),更能以精闢獨到的方式闡明這整個領域。
然而,隨著時間過去,我起出那堂皇但模糊的構想也煙消雲散,只剩下有些氣餒的茫然。這感覺就像一個年輕作家身在一座大圖書館,環顧四周成千上萬本藏書,懷疑自己是否能添上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我越思索,情況就越糟糕。寫作本身就夠要命了,但寫作談寫作的文字絕對更糟,簡直是徒勞無益,甚至連寫小說的慣常借口都不能用── 亦即,你不能說「筆下的文字只是虛構捏造,不能以真實確鑿的標準來檢驗」云云。也許聽眾和事後的讀者(你自負地斷定講稿一定會出書、有讀者)會想聽聽文學理論,或者抽象的計畫,或者聲明,或者宣言,於是你打開「理論暨宣言」的抽屜,卻發現裡面空空如也。至少我的情況是這樣。這下該怎麼辦?
接下來我搜索枯腸拚命塗寫的那段經過,在此就不提了,總之當時我發現自己又一如往常進度落後,而且更大的困難是我人在馬德哩,先前以為在書店的英文書架上鐵定找得到的一些書都找不到(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這點有些令人難堪)。儘管有這重重困難,六篇講稿還是拼湊出來,如期發表。希望各位不會注意到,有些地方是匆促的草草打包取代了深刻思想及數十年嚴謹的治學結果。
本書便是由那六場演講脫胎而來,談的是寫作,但不是如何寫作,也不談我自己的作品,或任一時、任一地、任何特定一人的作品。這本書,是一個在文字礦坑裡做了比方說四十年苦工的人──巧的是,我差不多就做了這麼久──有朝一日午夜夢迴,突然納悶起自己這些年都在幹什麼,於是隔天起床後或許就會想寫這麼一本書。
她這些年都在幹什麼,又是為什麼、為了誰?寫作到底是什麼,不管它做為一種人類活動、一種志業、一種職業、一種捉刀代筆的飯碗、甚或一種藝術,又為何有那麼多人受到驅策要從事寫作?它跟繪畫、作曲、歌唱、舞蹈或演戲有什麼不同?其他曾從事寫作的人又是怎麼看待這項活動,以及自己與它的關係?他們的看法能否帶來任何慰藉?所謂作家之為作家,並當然也由作家闡釋的這個概念,這些年來有無任何改變?所謂作家又究竟是什麼意思?作家是否如雪萊堂皇宣稱的那樣,是未受承認的世界的立法者,還是卡萊爾筆下那種老頑固的「巨人」,還是當時傳記作者最愛描繪的那種哭哭啼啼、神經兮兮、一事無成的軟腳蝦?
或許我當初是打算對涉世不深的青年發出警告。也許我在本書內談及這些題目,不只是因為自己寫作生涯之初曾對這些問題感到焦慮,也因為今日許多人依然──從他們提問的內容可以看出──為之焦慮。也許人到了我這種年紀,經歷過好幾番「洗衣脫水」的循環之後,開始認為自己在肥皂水裡打滾的經驗可能值得別人參考。也許我是想說:回頭看看身後。這條路上不是只有你一人。別讓自己被偷襲。小心路上的蛇。小心所謂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它不見得總是你的朋友。殺死濟慈的並不是哪篇負面評論。摔下了馬背,再騎上去就是。這類給天真朝聖者的建議無疑充滿善意,但無疑也毫無用處:危險與時俱增,你永遠無法兩度踏進同一條河,紙頁上的空白廣大得讓人畏怯,每個人在這座迷宮裡都是蒙著眼睛亂走。
讓我從標準的「聲明條款」說起。我是個作家,是個讀者,差不多就如此而已。我不是學者,不是文學理論家,任何混進此書的相關理論概念是經由常見的作家手法而來,類似寒鴉的習性:我們偷來那些閃亮的片段,將之編進自己窩巢的紊雜架構裡。
詩人詹姆斯.瑞尼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說裡,敘事者看著妹妹一邊拼字一邊餵雞,每撒一把飼料就拼出一個字。敘事者說,「我常納悶,她是在給天上的誰寫信。」伊安.麥依溫的短篇小說《一隻圈養猿猴的思索》中,作為敘事者的那隻靈長類也看著作家寫作,思考的不是可能的讀者,而是可能的動機,不過牠做出的結論不太樂觀。「難道藝術之所以產生,就只是因為人希望看起來很忙而已?」牠忖道。「難道只是因為人害怕寂寞、害怕無聊,只要有打字機重複的劈啪聲就能打破沉默、不再無聊?」
「我在想,不知這些念頭都是從哪來的?」三十四歲的瑞娜這麼問。她從六歲就開始寫作並把作品全丟進垃圾桶,不過現在她認為自己幾乎快要準備好,快要可以開始了。
作家最常被問到三個問題,發問的人包括讀者以及他們自己:「你是為誰而寫?為什麼要寫?這念頭從何而來?」
我寫這一段時,開始列出關於動機問題的答案清單。有些答案或許顯得不太嚴肅,但這些答案全是真實的,推動作家的因素完全可能同時是其中好幾項,甚至是全部。這些答案擷取自作家本身的言論──其中包括不可信的來源如報章訪問及自傳,但也有實際對話的紀錄,不管對話是發生在書店一角(之後就是可怕的簽名活動),還是廉價漢堡店、小菜酒吧等等作家出沒的地方,還是為其他名聲更響的作家舉辦的歡迎會中不受注意的角落;此外還有小說中虛構出來的作家所說的話──當然都是作家寫出來的──儘管這些人物有時會被偽裝成畫家、作曲家或其他藝術家。以下就是這份「何以要寫作」的清單:
為了記錄現實世界。為了在過去被完全遺忘之前將它留住。為了挖掘已經被遺忘的過去。為了滿足報復的欲望。因為我知道要是不一直寫我就會死。因為寫作就是冒險,唯有藉由冒險我們才能知道自己活著。為了在混亂中建立秩序。為了寓教於樂(這種說法在二十世紀初之後就不多見了,就算有形式也不同)。為了讓自己高興。為了表達自我。為了美好地表達自我。為了創造出完美的藝術品。為了懲惡揚善,或者──套用站在薩德侯爵那一邊的反諷說法──正好相反。為了反映自然。為了反映讀者。為了描繪社會及其惡。為了表達大眾未獲表達的生活。為了替至今未有名字的事物命名。為了護衛人性精神、正直與榮譽。為了對死亡做鬼臉。為了賺錢,讓我小孩有鞋穿。為了賺錢,讓我能看不起那些曾經看不起我的人。為了給那些混蛋好看。因為創作是人性。因為創作是神般的舉動。因為我討厭有份差事。為了說出一個新字。為了做出一項新事物。為了創造國家意識,或者國家良心。為了替我學生時代的差勁成績辯護。為了替我對自己及生命的觀點辯護,因為我若不真的寫些東西就不能成為「作家」。為了讓我這人顯得比實際上有趣。為了贏得美女的心。為了贏得任何一個女人的心。為了贏得俊男的心。為了改正我悲慘童年中那些不完美之處。為了跟我父母作對。為了編織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為了娛樂並取悅讀者。為了娛樂並取悅自己。為了消磨時間,儘管就算不寫作時間也照樣會過去。對文字癡迷。強迫性多語症。因為我被一股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驅使。因為我著了魔。因為天使叫我寫。因為我墜入繆思女神的懷抱。因為繆思使我懷孕,我必須生下一本書(很有趣的扮裝心態,十七世紀的男作家最喜歡這麼說)。因為我孕育書本代替小孩(出字好幾個二十世紀女性之口)。為了服事藝術。為了服事集體潛意識。為了服事歷史。為了對凡人辯護上帝的行事,為了發洩反社會的舉動。要是在現實生活中這麼做會受到懲罰。為了精通一項技藝,好衍生出文本(這是近期的說法)。為了顛覆已有建制。為了顯示存有的一切皆正確。為了實驗新的感知模式。為了創造出一處休閒的起居室,讓讀者進去享受(這是從捷克報紙上的文字翻譯而來)。因為這故事控制住我,不肯放我走(「古舟子」式的理由)。為了了解讀者、了解自己。為了應付我的抑鬱。為了我的孩子。為了死後留名。為了護衛弱勢團體或受壓迫的階級。為了替那些無法替自己說話的人說話。為了揭露駭人聽聞的罪惡或暴行。為了記錄我生存於其中的時代。為了見證我倖存的那些可怖事件。為了替死者發言。為了讚揚繁複無比的生命。為了讚頌宇宙。為了帶來希望與救贖的可能。為了回報一些別人曾給予我的事物。
顯然,要尋找一批共通動機是徒勞無功的:在這裡找不到所謂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若沒有它,寫作便不成其寫作」的核心。梅維絲.加蘭在她《短篇小說集》的序中列了一份比較短、比較精緻的作家動機清單,從說自己除了寫作一無是處的山繆爾.貝克特開始,最後是波蘭詩人阿勒山德.瓦特,他曾告訴加蘭,寫作就像那個駱駝與貝都因人的故事:最後是駱駝佔了上風。「所以寫作生涯就是這麼回事:」加蘭評論道,「一頭頑固的駱駝。」
既然找不出動機,我便另闢途徑:不問其他作家為什麼寫作,改問寫作是什麼感覺。我特別鎖定小說家,問他們埋首於一部小說時是什麼感覺。
他們全都沒問我說「埋首於」是什麼意思。有人說那感覺就像走進迷宮,不知道裡面藏著什麼怪獸;有人說像在隧道中摸索前進;有人說像置身山洞──她可以看見開口處的光亮,但自己處在黑暗之中。有人說像置身水中,在湖底或海底。有人說像置身於漆黑的房間,獨自摸索,必須在黑暗中重新擺設家具,全都整理好之後燈光便會亮起。有人說感覺像是在清晨或黃昏涉水渡過深河;有人說像置身於一間空房,房內雖空但卻充滿了位說出的字詞、充滿了一種低語;有人說像跟一個看不見的生物或東西扭打;有人說像坐在舞臺劇或電影開場之前的空盪戲院,等著人物出現。
但丁的《神曲》既是一部詩作,也是該詩寫作過程的紀錄。開篇描述他發現自己身在一片黑暗糾結的樹林,時值夜晚,他迷了路,然後太陽漸漸升起。維吉尼亞.伍爾芙說,寫長篇小說就像提著燈籠走進黑暗的房間,光線照出的只是原來就在房裡的東西。瑪格麗特.羅倫斯和其他人說過,那感覺就像亞各在夜裡與天使扭打──在這舉動之中,傷害、命名與祝福全都同時發生。
阻礙,蒙昧,空洞,迷途,暗影,漆黑,常常還加上一番掙扎或一條路徑、一段旅程──看不見前面的路,但感覺到有路可以前進,感覺到前進的行動本身終究會讓你看得清──在許多人對寫作過程的描述中,這些是共通的元素。這讓我想到四十年前,一名醫學院學生對我形容人體內部的話:「裡面黑漆漆的。」
於是,寫作或許有關黑暗,有關一種想要進入黑暗的欲望甚至強迫感,並且,幸運的話,可以照亮那黑暗,從中帶些什麼回到亮處。這本書談的便是那種黑暗,還有那股欲望。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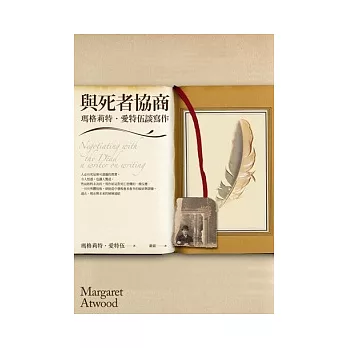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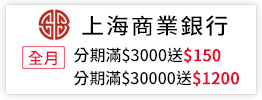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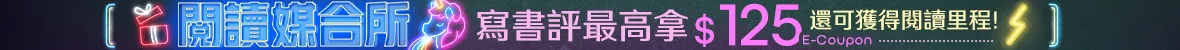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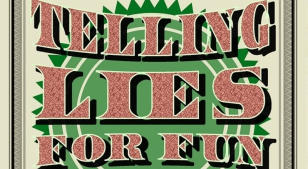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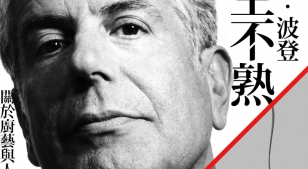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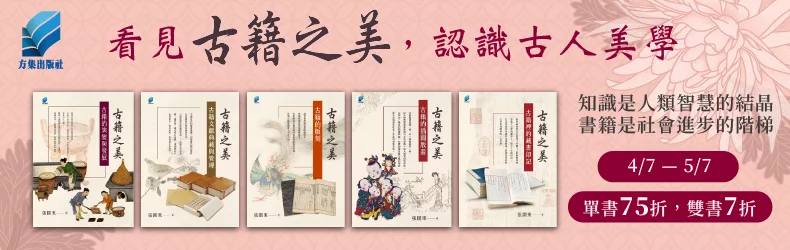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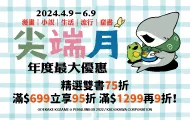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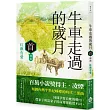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