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節錄)
與時間有關.與眼睛有關 唐諾
如果把時間看成一條河流,波赫士說,那時間就有兩種可能的流動方向,或正確的說,我們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時間流向感受──一種是我們人人以為的,時間從很遙遠的過去而來,不知不覺穿越過我們,持續向無限遠的未來流去消失,這是一種很透明均勻很無言的時間;另一種,則是英國的詹姆斯.布雷德利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事情正好相反,時間是從未來流向現在,而未來成為過去的那一刻就是我們的現在時刻。這是一種很刺激、很有知有覺的時間,我們會感覺時間是迎面撲向甚至撞上我們的,以一件一件事、一個一個人的具體模樣和質量,我們眼睜睜的看著它來,而且,所謂的現在又只是一個數學點,現在是無法存放東西的,現在一掠而過。這裡,波赫士複誦了希洛瓦的美麗詩句:「光陰就在某些東西已離我遠去的時刻消逝。」
這也是我讀《九月裡的三十年》這部小說的清楚時間感受──時間是一次一次迎面打過來的,一開始也許不那麼快察覺,但愈來愈確定的微痛感覺,眼睛然後臉上然後身體,發現原來如此。
我以為波赫士狡獪的隱藏了一個關鍵之詞(不直接說出來也許是好的),那就是死亡,這是時間第二種流向的前提。死亡彷彿豎立在那裡,未來不再膨膨鬆鬆的伸向無窮遠,而是到此為止一堵無法穿越的厚牆,第一種流向的時間撞擊上它,轉為第二種流向加速撲回我們,也因此,這樣的不同時間圖像和感受,又似乎是年紀,就像我們的年齡計算,通常由出生開始一年一年自動累積,我活了多少歲,但有一天,當死亡那麼明確而且逼近,我們也許就倒過來估算了,我還有幾年可以活著
追蹤傷害,化為知識和詩歌
《九月裡的三十年》是我很喜歡的一部小說,我有不少個喜歡它的理由,聰明,冷靜,專注,事事認真而且追問到底,卻不害怕動用情感和信任,因此,動人只是它自自然然的結果。如果考慮到最近這些年華文小說書寫夢遊也似的實際狀況,我喜歡的理由還會多出好幾個。
故事跟著胡琴這個人走,從她十七歲考上北大受一年軍訓到她三十三歲左右好友凡阿玲病逝為止,另一種可以考慮的想法是,寫到書寫者(以及你我所有人)當下的現實時刻為止。我不確定作者是否有意識如此,但這很清楚顯示出來,所有事情(真實的、虛構的)係發生在書寫者和我們共有的這個世界裡這個時間裡,小說本身無意虛擬出另一個世界、創造出另一種時間(這半點不難,事實上是更自由更好寫)。我的了解是,如果小說追問的是實實在在的問題,並期待某個有效可實踐的答案,那它很可能必須接受這個世界一些最基本的限制,視之為條件或者前提,並忍受其無法完滿。小說書寫者當然有權使用這個世界不可能存在的材料(比方人人都是惡魔或有某種不死之藥),耗用我們絕不擁有的時間,甚至援引某個不可思議的強大力量,但仰賴這些所獲取所建構起來的「成果」,往往無法攜回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成立,在穿越過兩個不同世界的邊境,堅實的部分會被擋下來,我們真正收到的,通常只剩某個軟性的心理慰藉,某些恍恍惚惚的所謂啟示而已。
有行業的故事
半開玩笑的說,《九月裡的三十年》還真為當代小說的死亡書寫扳回一點顏面。
我們說,人不會死得更死,死亡一旦完成,就再無法分解,無法真正追問接下來呢如娜拉死掉了她怎麼辦,頂多只能是但丁《神曲》那樣盍名言而志但無從證實的猜想,如今我們更傾向於不去想;而死亡發生之前呢?昆德拉告訴我們,因為太理所當然了,「如果它愈理所當然,就愈不容易看穿。」所以一場革命而死比一次戀愛而死容易看穿,又比一種疾病而死容易看穿,最終年老而死就只是該死了而已,這甚至不會激起我們足夠的悲傷和有意義的好奇,如今我們會說這是幸福的以此來覆蓋它遺忘它。理所當然的另一面是死亡的無可抵拒無可商量,基本上我們已完全接受了死亡是結局這件事,只有像書中胡琴那樣意識到還有機會、還有他種可能,我們才會相應的去認識去追索去想盡辦法,因此一樣的,我們比較可能去想一場革命的死亡,勝過一次戀愛的死亡,又勝過一種疾病的死亡,而人們年老死去,我們能怎麼辦呢?
但小說書寫,不是號稱面對著人的存在處境嗎?不是負責認識、追問、處理人的總體問題嗎?不是說所有的事都是小說的事?那為什麼我們現實世界數量大、折磨最多人(包括生者死者,當然是這樣)的死亡,卻是小說中最不被書寫的死亡?這怎麼可以?
關鍵的麻煩是,我們個人有限、破碎且曖昧不明的實際經驗不足以支撐這樣的書寫(死亡不是可經驗的事,至於我們身體裡面那一點點可憐的經驗,不僅累積得太慢太沒效率,而且我們通常並不知道怎麼解讀它確認它,當下總混夾著一堆猜疑、驚惶、僥倖、沮喪、絕望等等的干擾情緒,事後我們又最樂意第一時間忘記,不是這樣嗎?),我們得借助知識,而知識,正是小說一直在遠離的東西,這是當代小說的紅位移現象。
《九月裡的三十年》是一部「有行業」的小說,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他十七歲到三十三歲的故事,說出他眼中的世界模樣,問題是看到什麼,也許更重要的是怎麼看─難得的是胡琴的眼睛,這是有專業知識支撐並引導的一雙好眼睛,精確,沉著,有記憶有層次,能進入到素樸肉眼不容易看到的死角和縫隙,對看到的東西能夠再描述再解釋,如此才有機會將短瞬即逝的視覺印象給收納下來。就像莊子所講那個有行業的故事(「庖丁解牛」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行業的故
事),一隻牛,或說一整個眼前世界,可以就是一團,也可以一路分解開來,分解成已知的、可知的、未知的以及永遠無望得知的,分辨出人能夠的和不能夠的,你才曉得我們手中僅有這一把鋒利但也脆弱不堪的刀子,該正確的砍向哪裡、哪一個點。
豐瑋其人
豐瑋沉靜不太談論自己,是個令人生畏的好聆聽者,但我其實總是會破破碎碎知道她一些事。其實很容易把她描述成某種傳奇性的人物,比方說她出生於再平常不過的家庭,但在大陸比我們更像單敗淘汰賽的成長歲月裡,她是一路戰無不勝的頂尖者,最好的大學、最難的科系、最擠不進去的醫院(北京協和,咱們老國父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那一家)。我認識她時,她已任職跨國的最大藥商,負責亞洲地區最重要新藥的解說工作(她聰明且自嘲的更正朱天心:「不是解說新藥,是創造出新的病」),所得驚人,這樣的人來寫小說?而且,《九月裡的三十年》才是她第一部小說,這真是驚人。
這些話我忍到最後才講,猶豫再三的原因是,我相信豐瑋不會太高興我提這些,她不會要這些小說成績之外的傳奇性加分,當然她是對的。
這其實也正是我之前小小的杞憂以及我不得不講的真正理由──相較於她至此一路得勝的現實人生,小說其實是個古怪的行當,小說書寫更歡迎的總是挫敗不成的經歷,成功的習慣很容易把人誘引到那些有明確答案、有顯著成果的地方去,但那不是小說真正的戰場。
結果豐瑋比我想像的更好,我們從小說中清楚看出來,她不是個擁有者,而是不懈的追問者。
〈九月裡,度日如年〉
不見陽光的普世醫院地下室,四月的春天已無孔不入,聞起來味道甜膩。從實驗桌抽屜裡翻出一張紙條,上面一行電話號碼。久處地下室,嗅覺飛漲但眼力退化。
胡琴要做的事,和眼睛有關。
「訂五雙眼睛。今晚要,最後一次了。」
「老時間,晚上十點,帶冰盒!」
最後一次打電話給秦師傅。放下話筒,長吁氣。深呼吸,春天的甜膩自她的鼻孔進入,沿氣管順勢滑下,鑽進肺泡,隨即睏意四起。
一家屠宰場的存在,對於一個城市,並沒有太多人關心。若是豬肉漲價,倒是會牽動這世界的生物鏈條。為了畢業論文的豬眼睛,胡琴穿上放在它門口的那雙高幫雨靴,走進屠宰場。雨靴褪色由黑轉灰,夾雜暗紅。
北京南城,穿過「浙江村」的數層圍疊後,就是它了。真是活色生香。每晚十點,這裡燈光準時點亮,聲音旋即鼎沸。晝伏夜出的工人,新一天從這裡開始。他們套上塑膠圍裙,蹬上高幫雨靴,雨靴褪色由黑轉灰夾雜暗紅,穿插在喧譁的、倒立的豬群中。牠們被燙水,嚥氣,脫毛,分割。五六個小時之後,經過切分的鮮肉和排骨,在凌晨時運往各大菜場。一通討價還價、過秤付錢,進入牠這輩子的終極─各家廚房的案板。鍋碗瓢盆一陣響,腸胃蠕動,人們打飽嗝,得以有口氣繼續忙這忙那,順帶著煩這煩那。
這一年是世紀末。
四月,離胡琴畢業還有九十天。努了八年的弦,終於也到了這八年的終極─射箭的那一刻。射程其實有限。即便弩箭離弦,無非是大家都裝高潮談論的美國:拎兩隻行李箱,去那裡,重新翻開一頁,再去念一所大學,換個地方上自修。這終點讓胡琴意興闌珊。她只能在心裡妄圖拔高過程的份量。雖然終日與普世醫院、與像邊鐘一樣的大夫們捆綁在一起,有份量的過程也並非隨手可得。
離弦之前,胡琴得花一年待在普世醫院的地下實驗室裡。博士畢業課題可以隨便選科室,但必須有「品質」。符合九十年以來自普世醫學院畢業的那種品質。滲透高標、自豪、萬裡挑一的價值觀的品質。她選的畢業論文與眼睛有關。一開始,她以為是人眼睛。直到有一天,同實驗室的浙江人小瘦,激動地對她跳起來:「我要去取人眼睛了!」
胡琴渾身一機靈,問:「誰的?」
「執刑的罪犯,一共四個人!想想吧,四對眼睛。我都跟這兒待一年了,這頭一回聽說。」
「四對?人眼睛是論對的?怎麼取?」
「靶場上槍一聲脆響,人倒下了,你趴上去,用手術刀這麼一剜。我聽別人說的……一塊兒去的還有其他科的,各取所需,泌尿外科的扒腎,普通外科的扒肝……氣氛緊張,你爭我搶。我在外院聽說的!」
什麼樣的槍,什麼樣的靶場?遙不可及的軍訓記憶。浙江人小瘦說話時,眼睛中激起狂人一樣的光亮。平時那眼睛雖大,卻被長睫毛垂簾覆蓋,躲躲閃閃迴避著胡琴,迴避著眼前科學世界和老得快成骨灰的地下實驗室。
不想自己有一天眼睛閃得像狂人一樣,如同魯迅筆下「人吃人的社會」,胡琴暗自嘀咕要不換個課題算了。在她掂量自己絕不可能去取人眼睛時,實驗室老管家汪老太太塞給她一張紙條:「打這個電話,找秦師傅,去大紅門買豬眼睛,十塊一對,一樣做妳的課題。豬眼與人眼,結構差不多。普世醫院好幾代都這麼做研究的。別聽他的。我們幾代對人眼睛的認識,都是以豬眼睛為起點,從豬眼睛出發的。」
哦,這就以豬眼睛為起點,從豬眼睛出發。
「不,應該是十塊一雙。」數秒後,汪老太太又往回倒帶,糾正自己。不管眼睛來自人還是來自豬,應該是一雙,而非一對。她大半輩子都這麼認為。
真是普世醫學院的老畢業生。汪老太太曾用一個下午與胡琴嘮叨,對世間每一種在體形態,普世醫院的人從來保有最起碼的尊重。即便醫院外面那社會,早已不在乎這個。醫學院解剖學第一節課,老師帶著眾學生,先向眾屍體獻鮮花,鞠躬三次,沉默三分鐘。儀式感在空氣中點燃了本來零星且孤獨的自珍,敬畏給眼前這個大步快意走向失調的世界,重新帶來三分鐘的秩序。
屠宰場的秦師傅,沒知識份子這麼講究,他總在電話裡或是當胡琴的面說:一對眼睛。浙江人小瘦不也說嗎?「被執刑的罪犯,一共四個人,想想吧,四對眼睛。」小瘦也是論「對」的。他是外地讀完本科考來普世的博士生,不是純種普世醫院的人。小瘦後來沒取到那四對人眼睛。走到半途,有人攔住他,厲聲說:想什麼呢,上面早不讓了!
接過汪老太太的紙條,一段外人不知的旅行在胡琴面前揭幕。夜晚不同尋常了起來。不再是捧著一寸厚的醫學課本與眾人在七樓西教室裡埋首狂啃。也不再是只有胡琴知道的學校旁那條街一路往北的「忙瘋」酒吧,數支大院青年編雜的搖滾樂隊跳上台表演。與同宿舍五位實習女生趴在實驗桌上加完試劑然後離心的夜晚比起來,這夜晚更原始,更生猛,更鮮活。一條巨大的拉鏈打開,生活在這裡分出枝杈,通向別處。過程的份量非同尋常了起來。她想起大一軍訓拉鍊時,貼在《挺進報》上的自己那篇〈通向高山和流水的旁路〉:
林中分歧為兩條路,
我選擇旅蹤較稀之徑,
未來因而全然改觀。
為保證買到手的豬眼睛新鮮,胡琴總在晚上九點半出發,手裡拎只冰盒,走出普世醫院的地下實驗室。從醫院去大紅門的那段夜路,佈滿忐忑情緒。坐上公車,中間倒一次,下車後快步穿過暗黑「浙江村」數分鐘。畢竟,在一個城市裡,就人們目前的有限想像力而言,並不會把任何一個公共汽車站設在「屠宰場」。
夜十點半,胡琴到達屠宰場,蹬上一雙散發著腳臭和腥味的高幫雨靴,穿過血流如河的地面,耳邊喧譁,眼前中國紅飛濺。人群中豬群中,胡琴用一雙視力欠佳的眼睛,尋找秦師傅。像從一塊水果蛋糕上剜出一粒新鮮欲滴的櫻桃一樣輕巧,秦師傅用刀挖出以「雙」而論的豬眼睛,放入冰盒。胡琴遞給他五十塊錢。
只有在取回豬眼睛之後才捨得打車,打最便宜的黃色「面的」。零點,胡琴帶著五雙新鮮眼睛回到地下實驗室。
夜深了,氣氛變了,白天沉默的聲音此刻變得響亮,密涅瓦的貓頭鷹振翅起飛。
「為什麼要做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這樣的課題呢?那麼多科室,你們醫大的,盡可以隨便選。比我們強多了。」普世醫院食堂裡,邊鐘邊大夫問胡琴,一臉不解。
他面前陳列的伙食,顯示著普世醫院標準的住院醫生伙食水準。比實習醫生高一等:已經可以買兩份菜,一份飯,加一瓶優酪乳。有一天,胡琴聽到實習歸來的同宿舍女生,在上舖狂嘯:「我要留在普世,當一名住院醫生!那樣除了吃飯和菜,還能有錢再買一瓶優酪乳。每頓都有!」狂嘯聲中,每一位女生都被勾起了「做一名普世住院醫、每頓能再多喝一瓶優酪乳」的理想。
為什麼要做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這樣的課題呢?與眼睛有關,與時間有關。生物學上,與凋亡有關。生物學上的凋亡,不等於李金髮詩裡的凋零。胡琴導師問:為什麼人老了,黃斑會有退行性變,導致視力下降,進而會導致失明呢?也許是人的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的DNA,在老化過程中發生了什麼變化?DNA中有沒有什麼標誌物,能準確估算出這樣的老化呢?
是的,用某一種嵌入那副肉體裡的精確標誌物,來衡量時間留下的蹤跡。在眼睛這裡,時間掃蕩的蹤跡有可能是戕害。明確表現在DNA上的某種戕害。來,來,我們來探尋這蹤跡,這天地間的祕密之一。想辦法,認識它,解決它。智力上的滿足。(如解決不了呢?胡琴打岔想起某禪師說:那就放下它。)導師用的是普世醫院近一百年來的「啟發式教學」。就像很多很多年前那個在街頭廣場與路人對談、循循善誘的蘇格拉底,對談者如沐春風,朝向未知探索。這時,忘了首尾,過程的份量也會重起來。
被這一刻情景感染,是做這課題的理由之一。學就一身DNA本領以更便捷地去美國聽藍調和爵士樂,也是理由之一。眼睛、時間這兩件事,一樣重要,這可能緣於胡琴十三四歲瞎讀了些詩和哲學,又在十七歲糊裡糊塗地被送去軍訓踢正步打靶一年間,有了些不尋常的體會,接下來貿然闖入醫學世界,直面身體、疾病、生存期……這一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多出了些問題,總得用之後的大半生去嚼、去玩。各種方式都試試,科學的,文藝的。世上有些人,不就靠這些打發時間嗎?
十三四歲時戀愛─雖按軍訓好友凡阿玲的說法,嚴格來說那並不是愛情─最吸引胡琴的不是那人高而瘦因而凜然的身軀,不是那人張口珠玉滿濺的宋詞,不是那副低沉而溫良的嗓音,首先是那雙眼睛,靜駐在六百度的眼鏡後,不說話時尤其深,建造著自己沉默的場,向外一圈圈釋發能量,將被他吸引的人席捲進去。胡琴坐在教室裡,講台上是戴六百度眼鏡的語文老師。四十多雙眼睛中,他踱步,旁若無人,對著窗外泛綠的柳樹或是一大片黃燦燦的油菜花,凝視,停頓點頭,然後轉過身,在黑板寫下李清照的詞〈聲聲慢 尋尋覓覓〉。粉筆字豎排幾串,錯落繽紛。滿教室居然一片安靜。
是時間,改變了兩雙眼睛間的格局。十五歲,胡琴斗膽以文學的名義,去他家借了一本俞平伯、一本周作人的散文集,他倆侃文學時(主要是她聽他侃),面前就橫陳著他即將新婚的大床,書架緊挨著大床。十七歲被送去軍訓,被安置坐在中原一塵不染的桌前,整個地球像只剩下自己一個人,被濃重的鄉愁驅使,主動寫了第一封信,抄了剛讀來的尼采句子:「誰終將聲震人間,必長久深自緘默」。六百度眼鏡回:「斯世獨立,淡泊明志;橫而不流,寧靜致遠。」展開豎排字的信紙,激動串出來,令人眩暈,踢了一天正步本來兩腿癱軟的胡琴,從絕緣體變為導體,全身一陣電流。
大四,回普世醫學院念解剖,有天下課,胡琴解下解剖課沾滿油腥的塑膠圍裙,離開屍體出門打飯。正打著呵欠,收發室遞給她一封信。「眼鏡」已結婚七年,兒子已到背蘇東坡背李清照的年齡。信裡「眼鏡」第一次用了「愛」這個字,遲到的他頭一次膽大,特別撞眼。自十三四歲起,胡琴一直在胃腸裡醞釀這個字,慢慢壯大,曾有一段時間飽脹得必須吐出來,但時間多厲害,這個字竟也慢慢被咀嚼、消化、排泄。用一雙被福馬林熏得疲憊、整日竟只關注解剖細節的眼睛對著信紙,胡琴笑了。像看任性的兒童玩拼字,又像自己圍觀自己,中間錯開數年,難堪而悲情。她寬容地搖搖頭,繼以沮喪,專注吃完飯盒裡的最後一塊米粉蒸肉,棕色的,一如剛才解剖課上的福馬林泡過的屍體顏色……不過,以上按軍訓好友凡阿玲的說法,都不叫愛情。沒發生過親密關係,雖然借書那次,那張新婚大床曾橫陳在倆人面前數小時,他大講《紅樓夢》和《圍城》其實是一回事。甚至,連拉手都不曾在現實中發生過。想像中,倒幹過很多次。
如果這麼回答吵過好幾架進而熟識的邊鐘,在眼前謹慎、嚴肅、古樸的普世醫院裡,就太傻了。雖然近一年的地下實驗室生活、讓胡琴離眼睛、離時間的物理距離,又近了一步。期間,北京南城屠宰場、涉及DNA的分子生物學技術,無一不在幫她拉近。實習醫生胡琴吃的是一份菜、一份飯,僅此而已。沒有優酪乳。她用力嚥下飯菜,然後說,「隨便瞎選的,混個畢業而已。」筆挺白大褂裡的邊鐘直搖頭,胡琴得逞暗笑。
夜間零點,從黃漆「面的」下來,胡琴手拎冰盒再一次走進地下實驗室。冰盒歷史很長,上面有紅色剝落的手寫字跡:普世醫院眼科生化實驗室。下面一小塊鐵皮刻著它在普世醫院資產庫中的編號,前四位數是年份,一九八六。走進夜晚的地下實驗室,人、鬼、醫魂、北京人的頭蓋骨……在醫院曲折枯靜、四通八達的走廊裡,穿梭起來。
放張Pink Floyd的《雷霆之音》聽,打開超淨台電源,將各種試劑從冰箱裡如數取出,一一陳列手邊。有一份從祖上傳下來的實驗步驟,它古老得曾經過「蘇格拉底」導師的手、汪老太太的手。最近一次經過浙江人小瘦的手。在唱片播放兩輪之後,那些新鮮豬眼睛的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被分離出來,被放進一汪晶瑩的培養液中。黑暗中細胞們在徜徉,在貼壁,在生長。技術之後,無一不是眼睛,無一不是時間。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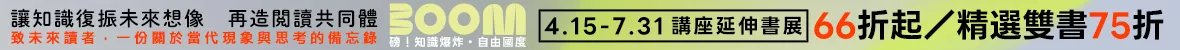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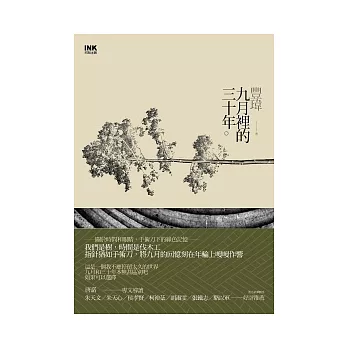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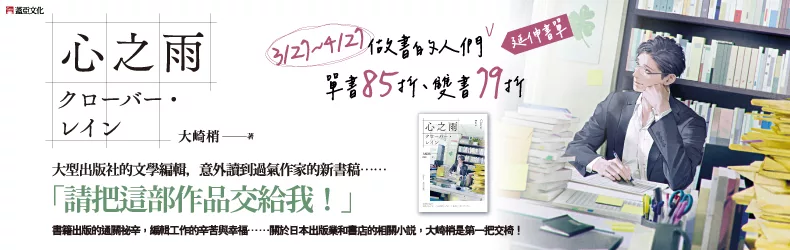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