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黎巴嫩詩人兼小說家古伊葛塔(Venus Khoury-Ghata)客居巴黎時,她的祖國爆發了內戰。情況慘絕,讓她無法回返。
但她還是比大多數流亡者幸運,因為她已能流利的使用容身之地的語言。而且還不只是遊刃有餘,她可以直接用法語寫作並出版。這種令人豔羨的外語能力卻得讓她付出高昂的代價:新語言把她擰成一個似乎沒有國籍的人,既不再屬於她的本籍文化,也不算是道地的法國作家。
古伊葛塔在寫給法文讀者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當她用阿拉伯語寫作時是從右寫到左;而用法語寫作時,卻是從左到右。一個是她的母語;另一個則是「讓她接受教育並經歷文學啟迪的語言」(借用她英語譯者的美妙說法)。這條「雙向路」充滿隱喻,兩種語言彷彿在紙上迎面相逢,但這竟讓她自覺是個非法侵入者。她本人用的類比喻體是「重婚者」:一個「藉語言的掩護而過著雙重生活」的女人。
古伊葛塔的用詞挑明了一點:她覺得精通兩種語言有點不妥,甚至不該被允許。正因如此,她才會為自己選定的文學語言進行辯護。提及「重婚者」的那篇文章的題目就是〈為什麼我用法語寫作〉。
說得也是。為什麼「硬要用不屬於自己祖國的語言」講述故國家園的故事?
「答案很簡單,」古伊葛塔自己回道:住在黎巴嫩,我不可能寫書;我會忙於育兒和煮食。因有距離,才有必要講述黎巴嫩。我需要重建它,模擬它的初態、分裂和傷痛,從而給自己一種幻覺,好像和留在那裡的同胞們一起分擔了日常生活中的恐怖。
重要的是,用法語寫作並不意味著阿拉伯語被迫隱沒。事實正相反,古伊葛塔的母語仍然想被聞見:「阿拉伯語把它的甜蜜和瘋狂注入法語」,雖然這也讓她成為「流離於兩種語言之間的那種人」。
在《與我的父親阿朵尼斯(Adonis)的對談錄》中,敘利亞最受尊崇的詩人不厭其詳地和他的女兒進行了一系列廣泛話題的互問互答。最終,語言的問題浮出水面。女兒請父親解釋他和阿拉伯語的關係。
「我無法想像自己使用別的語言,」阿朵尼斯坦承地說,「阿拉伯語旺盛地活在我的身體裡,以至於它會去嫉妒所有其他語言。我相信阿拉伯語已深切的植根於我,讓我在其他語言面前顯得笨拙愚蠢。」
無論這番話多麼謙虛動人,它並不完全屬實。別的不說,父女間的這些對談都是用法語進行的。阿朵尼斯不僅受過正式的法語教育,還在法國住了許多年,因而可以流暢無礙地使用這種語言。至於他的女兒,法語則是她的第一語言。「我可以寫一點阿拉伯語,」她在書中承認,「但只懂皮毛。這門語言更像是一種硬加在我身上的責任、甚或重擔。」
阿朵尼斯對女兒的困窘感同身受,但他還是堅稱:「如果你真想理解一位詩人,就必須用他的母語閱讀他。」
所以,她的阿拉伯語到底得要多好才能理解她父親?
「你必須通曉阿拉伯語,」父親回答說,「但你已經不太可能達到這種境界了。」不過,面對希望成為作家的女兒,他還是寬慰了一番:她只需要徹底掌握一門語言,就能符合作家該有的標準。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選擇法語;但這麼一來,我們之間就會存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詩意的以及語言的鴻溝……我不知道你吼叫和哀泣時用法語還是阿拉伯語,但我覺得,阿拉伯語將永遠是你的文化語言,而不是母語……
吼叫和哀泣時的語言:還有比這個更像「母語」的精準定義嗎?當我們陷入沮喪絕望時,要是不能毫無顧忌地依賴某種語言,它還怎能擔當我們最主要的溝通方式?
正是這個原因,古伊葛塔在闡釋她為何用法語寫作的文章裡還坦白了一點:「新近征服的語言對解決日常繁文縟節毫無助益」。用阿朵尼斯的說法,這是因為法語只是古伊葛塔的「文化語言」,而非她處理俗世問題時的母語。
這不是說一個人無法在第二語言中如魚得水,只用那種語言就能解決生活中的煩惱。只不過,要達到這種程度,他必須投入所有時間,一直使用他想要精通的語言。他必須徹底的棄械倒戈,直到在夢裡都說那種語言為止。
因此,讓兩種語言都保持完好無損的狀態簡直是異想天開。連古伊葛塔都承認,「保留舊語言並且掌握新語言,需要走鋼索的技藝。」
就算一個人有這種技藝,他還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嗎?想想日常生活中需要了解的零碎事物:新觀念,新流行語,新玩意兒,新人名和新地名──誰真有耐心以及決心同時用兩種語言學會這些東西?
所以,無論是否心甘情願,我們終究會疏遠一種語言,慢慢讓它老朽、蒙塵乃至閒置。每一週、每一月,我們又多忘了一些詞、幾句話,直到有一天才驚覺到,對於那種語言我們不再能夠運用自如,哪怕它是我們的母語。
二
不久之前,我的一部小品得了個獎,繼而也讓它的作者面臨了一個有關母語的問題:一個土生土長的臺北人為何選擇用英語寫作?
琢磨了半天,最終我只能說,因為我的英文比中文好,所以更適合用來寫作。
事實上,我不僅是英文寫作更好,就連一般思考也都是用英語。但我並不是所謂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美生華裔〕的縮寫)。其實,使用英語對我來說一點也不自然──至少一開始不是。
為了改變語言,我十五歲移居美國後就一頭扎進了英語。像一名船難中的水手,與其禱告救援在船沉前抵達,不如一個猛子地扎進水裡,奮力划動四肢,游向最近的陸地,因為這幾乎是唯一的生機。轉換語言的人都如此,必須在源源不絕的文字中急流勇進,試著不被險惡的語法暗流沖走,不被無窮無盡的詞彙淹沒。
回頭去想,這麼做還真得有點勇氣。但一個遭難的人很少會有當英雄的念頭,他一心一意只想要存活。對一個青少年來說,「存活」就是結交新朋友、融入新環境,在學校裡不做那種不敢張口說話、老是被取笑的可憐蟲。
因此我在英語上投注了不少功夫。這讓我沒有變成那種一眼就能認出來的移民。即使是在紐約這個出名的文化大熔爐裡,還是有不少外國僑民從未被「熔化」過。他們成天和同胞黏在一起,唯讀母語報紙,看那些從遙遠國度傳來的電視劇,除了祖國的傳統飲食什麼都不碰,就連衣著好像也從未隨著潮流更換過。
我年輕時常想,這樣的人去了異國有什麼意義?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後,他們仍不能用第二語言拼湊出一個像樣的句子。
但現在的我卻不再那麼肯定那些人需要憐憫,更不會去鄙夷他們。也許他們有意識的做出了抉擇,也許僅僅出於恐懼、甚或懶惰,無論如何,他們拒絕被「熔化」,因而妥善保存了自己的母語;他們的發音依然清晰,提筆時仍可運用大量的詞彙。這難道不值得褒獎嗎?
人們通常認為,一個人更改了他的主要語言,就切斷了自己和母國文化的重要紐帶。偶爾,還可能被詬斥為拋棄同胞和故國。
實際上,更換語言這種事頻繁發生,並不見得有太多寓意。為了開展一段新生活,人們往往需要同步接收一種新語言。
真該問個究竟的是,以我們使用的語言來「界定」我們的身分,這麼做是否合理?例如,一個女人必須說出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才能被認定為「阿拉伯人」嗎?難道只因為她更擅用另一種語言,就不再能屬於她的出生地?
不應該這樣吧?至少,我希望不是。理由很簡單:我們使用哪種語言通常都是由「命運」所擺布。這一點在猶太作家貝克(Jurek Becker)的生平故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闡釋:如果,今天站在你們面前的我被看作是一名德國作家,這只是出於一系列的巧合。我出生在枯燥乏味的波蘭小城羅茲……如果我出生後不久德軍沒有入侵;如果我的國家沒有淪陷;如果後來我和父母沒有被趕進猶太人居住區、然後又從一個集中營送入另一個;如果蘇俄紅軍沒有解放我最後被關進的那個集中營,那麼,我倒很想知道,今天我會站在誰面前,又會被看作是哪一國人……
戰後,我父親──也是我們家除了我之外的唯一倖存者──莫名其妙地在柏林住下了。如果他移民去了布魯克林,我豈不是成了美國作家?要是他選擇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或是臺拉維夫?可是他沒有。在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能性裡,他做出最驚人的選擇:他留在這裡……並安排我成為一個德國人。
貝克如此,可能我也相差無幾。或許我用英文寫作的「真正」原因在於,我母親在紐約生活了許多年。
如果她不是個作家;如果她沒有和我父親離婚;如果紐約的文化沒有那麼豐富;如果當初臺灣的教育體制沒有那麼糟糕,從頭到尾只強調死記硬背;那麼,我也不大可能會改變我使用的語言。
然而,生命中的重大決定往往都由不得我們自己做主。所以今天用英文寫作的我,才常被稱為「美國作家」,雖然這並不是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在內心深處,我仍舊是個說漢語的人。陷入沮喪絕望時,我依然仰仗這最初的語言來吼叫和哀泣。
三
在《天下之美》中,捷克詩人塞弗爾特(Jaroslav Seifert)談到了哈謝克(Jaroslav Hasek):
他總是坐在桌角寫作,每寫完幾頁,他的朋友就會把稿子直接拿給出版商,出版商也會按篇幅付款,一毛錢也不會多給。就這樣,一天的酒錢都解決了。倘若第二天他不想面對一個空杯子,他就必須繼續寫下去。
令塞弗爾特好奇的是,如果他祖國這位小說家「能夠平平靜靜、舒舒服服地在書房裡寫作」;如果他沒有從早到晚在「一家嘰嘰喳喳的酒吧」裡跟他那群酒友混在一起;如果他不需要「在一張啤酒四濺的桌子上」創作;如果他提筆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需要賺點酒錢」;那麼,《好兵帥克歷險記》是否會有任何改變?
然而,塞弗爾特也清楚,要是沒有上述的這些因素,很可能小說家根本就不會寫出他最著名的那本小說,也不會成為「那個揚名全歐洲的『哈謝克』」。
但這仍然只是一種猜測,誰也無法確定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這個或那個結果。就像塞弗爾特所說,任何一件事,從策畫到完工,都涉及到一連串可以「決定命運」、改變結果的「如果」。
這本書也不例外。要是我母親還沒有過世,要是她沒有留下一點遺產,讓我可以專心寫作,我也不可能有時間寫出這些絕不是為了討好市場,而只是因為自己想寫而寫的文章。
老實說,這世上沒有一個作家不想要有更多的讀者;不想看到自己的著作登上暢銷排行榜。問題是,在這個已不再關注純藝術、純文學、純哲學的時代,一個學者如果想要取悅大眾,唯一能做的不外乎是評論那些家喻戶曉的人物,闡釋那些眾所周知的作品,重述那些老掉牙的話題。
這麼做的結果就是,絕大多數討論藝術、文學、哲學的相關書籍都沒什麼新意,總是重複著那幾個人、那幾樁事,好像除此之外,沒什麼別的好說。
事實卻不然。有許多被大眾忽略的藝術家、作家與哲學家其實都是一流的,他們的才華與成就絕不亞於那些老是被吹捧上天的人物。
我想,這也是我寫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為我喜歡與流行唱反調,而是因為我覺得有必要把這些值得認識、甚至深究的人物、軼事介紹給更多的讀者。
薩克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三十六歲時,策畫了六組小說,每一組都由六部中篇構成。這六組小說的主題分別是愛情、財物、政治、戰爭、事業,以及死亡。每一組的前五部作品會通過虛構的故事來討論主題所涉及到的問題;第六部則會提供答案。這麼一來,薩克馬索克宣稱,他便可以描述「世上所有重要的問題、生存中所有的危險,以及人類所有的弊病」。
不消說,這位十九世紀奧地利作家並沒有達成他的夢想。他雄心勃勃計畫的一系列小說,只完成了兩組,而且一本比一本寫得糟糕。這兩組作品中唯一一部常被提到的,仍是《穿貂皮衣的維納斯》,一本打從一開始就備受爭議、描述「性變態」行為的小說,最後還讓作者的名字被心理學家用來命名「受虐癖」(德語中的「Masochismus」)。
當然,惡名昭彰也有它的好處。尤其在這樣一個對醜聞誹謗特別有興趣的時代,一個文人想要引人注意,或許真的得不擇手段。但我想,要是一個人能從薩克馬索克身上學到什麼,最踏實的,大概還是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能力。
換言之,與其宣布有一天,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寫出一系列的文章,把西方文化裡最經典卻又鮮為人知的東西介紹給讀者,還不如默默地寫下去,一篇篇文章、一本本書地發表。這麼一來,就算最終無法完成夢想,我還是寫了許多關於自己欣賞的藝術家、作家、哲學家的文章。每一人的作品都讓我在閱讀研究的那些深夜裡,在孤獨中得到樂趣;在黑暗中得到啟迪。
要說這是文化可提供的最基本報酬,或許也不為過吧。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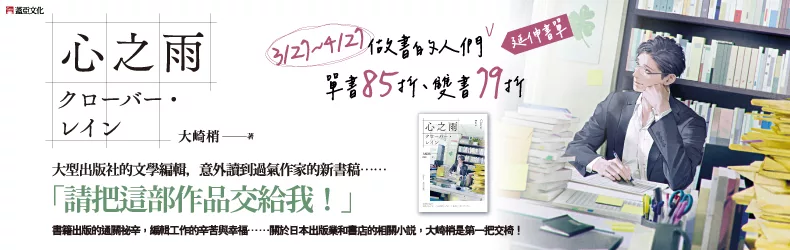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