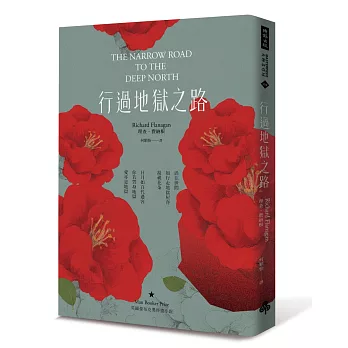
因為愛,也是地獄
——《行過地獄之路》書評
讓我們活與愛
甭理那些愛說教又不贊成我們的老傢夥
太陽下山,明日還會再升起
但是我們,當我們的短暫光芒逝去
就必須在黑暗中長眠
——古羅馬詩人 卡圖盧斯
“這個故事始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新加坡淪陷,一個帝國隕落,另一個帝國崛起……”醫生杜裡戈為戰俘同袍韓卓克思的畫冊序言中這樣寫。這個故事因而和新加坡,和我所在的樟宜,和1.8公里遠的二戰樟宜戰俘營遺址(今天的樟宜博物館)有了關聯。
我在樟宜的陽光下閱讀,在樟宜的大雨中閱讀,在樟宜樹的樹陰下閱讀,鼻端充斥著當年戰俘由此出發,穿越新加坡去往暹羅,修建“死亡鐵路”的死亡氣息。理查٠費納根筆下充斥潮濕氣息,一切都變得濕滑、粘稠,綠色藤蔓瘋長,竹子遮天蔽日試圖將一切都掩蓋,但是那支“杜裡戈的J部隊“(兩萬兩千澳洲戰俘)長眠於地下。花朵從他們的胸骨、小腿骨、肋骨和眼窩中生長出來,從他們最後的苦難和掙紮中生長出來,也從他們失去的活下去的希望中生長出來,最後變成繁花盛開的山谷。
“但是我們,當我們的短暫光芒逝去/就必須在黑暗中長眠。”
《行過地獄之路》,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拷問。我們應當時時自問:生存的意義是什麼?最真實的自我在哪裡?愛在哪裡?地獄是否無處不在?
理查٠費納根沒有回答,他不回答,主人公杜裡戈也不回答,他只有行動。跟著不得不如此的邏輯行動,被內在的虛榮所驅使,被他人的希望所驅使,成為自己並不想成為的那個人。他成為戰地醫師、澳洲戰俘中的最高指揮官、所有人的希望、後來的戰鬥英雄、著名的醫生、堪稱完美的父親、假裝仍舊有愛的丈夫,他和同袍的遺孀上床、和同僚的太太私通、他是偷腥慣犯、他駕車沖入大火拯救自己的太太和兒女、他擔任重要政府官職,但是,他不是他自己。他沒有愛,他是全然孤獨的。“他像是無法再散發光明的燈塔“,沒有希望,陷入虛無。
日本俳句詩人小林一茶說:活在世間 / 如行走地獄屋脊 / 凝視花朵。
杜裡戈走在地獄的屋脊上,直到生命的終點。他的夢裡,也只剩下曾經在舊書店的灰塵浮動之間閃耀過的大紅山茶花,那朵花,在“死亡鐵路“的汙濁泥漿中間,在暗暗的油燈照亮的小路旁,閃耀過第二次;在悉尼海港大橋上,陽光閃耀、雪浪翻飛,閃耀了第三次,可是,他錯過了……
藉由杜裡戈的思索,費納根將美麗人生的虛幻外衣剝除下來,給我們看到最真實的一面。並不是因為不相信有希望,也不是因為愛不夠真實,而是終其一生,全部努力,都只是如堂吉訶德一般,“向風車進攻“,結果如何呢——是杜裡戈在臨終前所看見的:空無。
追尋真實的自我
長日已盡
月亮緩升
大海與眾聲齊呻吟
來吧,我的朋友
尋找新世界
時猶未晚
——丁尼生《尤利西斯》
杜裡戈來自澳洲大陸邊緣的小島塔斯馬尼亞,幾乎是窮困家庭長大的唯一認字的孩子,丁尼生的《尤利西斯》貫穿了他的人生。他總是追尋新的世界,也追尋最真實的自我。
理查٠費納根揭示的人性困境之一,就是無法成為真實的自我。我們都困在某種社會角色中。家人、同僚、上司、情人、鄰舍、幫傭……期待我們成為某種人,我們得設法不讓他們失望,不論那是否違背自己內心的感受。這個過程中,有些人順其自然,很好地轉換,有些人享受,也有些人終生痛苦。
快樂的人沒有過去
不快樂的人除了過去,什麼都沒有
‘A happy man has no past, while an unhappy man has nothing else.’
例如杜裡戈,參軍之後,他在舊書店的二樓,與艾咪初次見面,什麼也沒有發生,但是他和她的眼睛彼此交代了太多,還有艾咪髮際的那朵大紅花,從此他走上地獄。但是無論在他已經訂婚的妻子愛拉那裡,還是在泰緬鐵路的死亡氣息中,他從來沒有忘記艾咪,只是,他無法找到真實的自己。周圍的人,周圍的事,一再強迫他成為不願意成為的人。
找尋真實的自己成為最不可能實現的期待。
在愛拉那裡,他必須成為一個風趣、善於應酬的年輕人,他也必須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他的愛,不過,他知道,“那不是愛”。
在死亡鐵路上,他成了澳洲軍隊戰俘的最高階軍官,他必須成為他們的領袖,他必須為了他們的生存而努力。為了拯救他們每一個生命,他,杜裡戈得要算計每一種可能性,儘量把病情較輕的戰俘派去上工,儘量照顧那些由於瘧疾、缺水、潰瘍、腐爛、挨打而生命垂危者。他們當面稱呼他“上校“,私底下,他們尊稱他”老大“。但是,那是否是他內心所需要的呢?
理查٠費納根把修建泰緬鐵路最慘痛的那一面展露給我們看。他寫出戰俘之間的彼此照顧,他更寫出杜裡戈內心的那些真實的掙紮。當手下拿來一塊難得一見的烤豬肉,他是費了多大的努力,才抑制住自己內心的焦灼與渴望!他揮手,斥責他們,拒絕那塊意味著多一點營養、多一點生存希望的豬肉,但是,那是他“理應“做的事情——成為他們所期待的那個人,那個道德高尚的領袖,需要多大的努力!
有些時候,我們確乎如同杜裡戈,認不清楚真實的自我到底在哪裡,或者是誰。照著自己想要成為的人去行動,很難。太多的責任被賦予在身上,讓我們無法自覺。當我們披上某種外殼,起初會不適應,會掙扎著要逃脫出來;時間一長,再堅硬的外殼我們都會習慣,最後會變成自己的一個部分。然後我們會依照世界所要求的那般去行事,依照人們為我們打造的形象去行事,如此這般。最後,我們會誤認為那就是自己,那就是我應當具備的形象:髮型、衣著、眼鏡、走路的方式、說話的腔調、行事的風格……我們說:那就是我。不,那是符合別人期待的我。契訶夫/果戈裡的小說中盡多這類的人物,而我們閱讀小說時,不也是常常為某人生活在“套中”而扼腕嗎?
這是杜裡戈的第一個追尋:真實的自我。
尋求活著的意義
生存之道在於無論多小的事情,都不要放棄。
受苦就是受苦。受苦不是美德,也不會誕生美德,美德也不會因為痛苦而湧生。
但是他告訴自己,想活,最需要的就是相信自己能活下去的那種荒誕信心。
在戰俘營的首要任務便是活著。杜裡戈的首要任務便是確保他的“J部隊”活著。然而活著意味著什麼?
費納根嘗試解釋。他透過杜裡戈說:“不受生命牽制,也不被死亡掌控”。活著是獨立而自主,有尊嚴。在另一本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書《這是不是個人》中,作者說:活著,是”為了日後能夠能帶著證據出去,能向世人講述……我們最後的權力,那就是:我們不認同他們的獸性的權力。”在費納根塑造的人物那裡,我們不容易看到這麼強而有力的表述,因為他們已經被折磨成為無力思考的動物。唯一比較容易滿足的“小黑”,總是依賴於比較快樂的想像而活著:還有一口飯團、還有一顆發黴的鴨蛋,還有三個小時的睡覺時間……但是,這樣容易滿足的小黑,僅僅因為被褥的折線沒有向外而被毆打,患上瘧疾,最後死在滿是蛆蟲的糞坑。那麼,活著的意義在哪裡?
費納根給我們看多種形式的愛:小黑與細漢(他在戰俘營的搭檔)彼此竭盡全力攙扶,杜裡戈為了讓生病的戰俘儘量不要上工,被日本軍人一個又一個耳光毆打卻決不放棄,杜裡戈和戰友遺孀的彼此慰藉……
他也給我們看見各種各樣的死:小黑、傑克˙倫波、“巨蜥”(戰俘營獄卒)、日軍上尉古田。每一次的死亡,都是一個終結,所不同的只是我們是否理解自己走到生命終點這件事的意義。或許小林一茶的俳句能夠很好地解釋費納根的生死觀:“覆蓋露水的世界/每顆露珠/都是掙扎的世界”。
為何而活著?這一向是一個難以輕易解答的問題。也許,因為有所牽掛,因為有一些值得忍受一切痛苦來追求的人或事,因為有不能不去發現的愛,因為有一定要完成的責任,或者,因為活著,這件事實本身的意義就指向人類的本能。杜裡戈竭盡全力地維持尊嚴,追尋活著的意義,但是,在臨死的最後一刻,他意識到,這一切,都是如同堂吉訶德的瘋狂。他說道:“諸位男士,向風車進攻”!
尋找愛的含義
《行過地獄之路》,英文名為<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即是日本詩人、俳句大師松尾芭蕉的詩集《奧之細道》的英文翻譯。
松尾芭蕉行遍日本北部,病歿于荒野,留下經典的俳句集《奧之細道》。其中著名的詩句:“日月乃百代過客,年亦旅人耳”。這一句,仿寫李白的詩句“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理查˙費納根在多處借著日本軍人和工程師的對話引用了松尾芭蕉和弟子小林一茶的俳句,滲透出濃濃的虛無的感覺。
費納根讓他的主人公杜裡戈和艾咪的人生三次交會:一次在舊書店、一次是在海灘的酒店房間、一次是在戰後的悉尼海港大橋上。最終,他沒有讓他與她的故事有圓滿的結局,反而一轉筆鋒,寫到杜裡戈如何得知妻子和孩子可能身陷火海,於是駕車前去營救。
“車行之處也稱不上道路,而是燃燒的樹枝、雨般紛飛的火星、濃煙所構成的混沌,偶爾還看到仍在燃燒的廢棄車輛……他偶爾才能瞥見被地獄怒火染紅、黑煙狂哮而過的天空露出一絲本來面貌。”
我們知道,多年來,他和愛拉之間已經沒有感情,只是出於慣性生活在一起。那麼,他不顧一切,駕車沖進大火,尋找孩子們和愛拉,他在尋找什麼?愛,還是救贖?或是僅僅是為了忘卻之前悉尼海港大橋上錯過的紅花?他奮不顧身,投身地獄,只是為了遺忘?
費納根沒有說,但這不過是一種責任使然。在死亡鐵路,是責任驅使他扛起一切;在這裡,也是責任,驅使他忘記自我。“這不是愛,也不是不愛……他們是家人。”責任是他的地獄,愛也是他的地獄。無論最後將會剩下什麼,或者其實什麼也不會剩下,或者一切都歸於荒蕪,這就是地獄,杜裡戈背負著他的地獄前行,終點在哪裡?我們又如何?我們是否也背負著我們的地獄過日子?有多少人背負著自己的地獄過日子?
愛的含義是什麼?它是生命中短暫的泡影,是神許給我們的短暫夢想,是我們在夢中才能偶爾瞥見的光亮。人的一生中,它出現一次,是奢華;出現兩次,是奢侈;出現三次,是奢望。你一旦擁有,就得背負它帶給你的地獄。所以,“空無”或者才是最符合邏輯的結束。
“地獄”與“風車”的隱喻
讓我們還是回到小林一茶的那一句:活在世間 / 如行走地獄屋脊 / 凝視花朵。
毫無疑義,“花朵”隱喻艾咪,因為那一朵鬢角邊的大大的紅花搖曳,是杜裡戈離開“正常”生活軌道,發現自我的開始,當然也是誘惑。“因為戴了大紅花的女子走到他這排,陽光與陰影在她身上形成相間的條紋,她,就站在他面前。”自這一刻開始,艾咪成為杜裡戈生命中最為獨特的存在,也是來自地獄的呼喚——我們怎能不聯想到海妖塞壬的歌聲?怎能不想到杜裡戈並沒有成為奧德修斯?若是他此生就是這樣度過,那麼塞壬在他漂流的生命之海上將就此離他遠去,再也不會影響他的一絲一毫。
然而,命運的風暴將再度施展威力,將杜裡戈的航船吹送到他命定的港灣,——那個面對海洋的“康沃爾王”酒店房間,那是他的天堂,亦是地獄。那裡有海的時間,亦有人的時間。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理解理查٠費納根的如下句子:“他將置身地獄,因為愛也是地獄”。
不過這還是不夠,若艾咪是地獄,那麼和杜裡戈曾經同床共寢的那些女性呢?他的髮妻愛拉呢?她們是否也是地獄的一部分?當然。因為薩特寫過如下著名的句子:他人即地獄。這句話不是說他人對自己的折磨。若是這樣理解,未免失之膚淺。首先,我們都有自由意志,我們依據自由意志來行動,這樣才是完整的人。然而,我們的行動是藉由他人的反應才能顯現出來其影響,當我們的行為映射在他人的身上,並反過來構成映射的時候,我們會憎惡這樣的映射,甚至憎惡自我,這樣,我者與他者的關係將會扭曲、惡化,他者由此成為我們的“地獄”。因此,杜裡戈愈偷腥,便愈在他人身上看見自我,愈覺察出自我的空洞。他和愛拉愈是牽扯在一起,便愈是感覺到這樣的生活的無味,因為——是他自己將愛拉轉變成了一個乏味的女人。因此,“他等待遲遲不至的結局。但是她所受的傷害、痛苦、啜泣與哀傷並未終結他的靈魂冬眠,而是睡得更深。”
我們見識到費納根曲折入微的隱喻。他慢慢地為我們揭示出“愛是地獄”的真正意涵,一如艾咪別在發邊的大紅山茶花,它鮮豔、懾人而又殘酷如利刃。
一如“地獄”這個隱喻,“風車”同樣是一個關鍵性的詞句。我們都熟知賽凡提斯的堂吉訶德,他和桑丘的旅程,遠征——征服——歸來,早已成為英語世界小說的經典模式。不過,博學的費納根反復提到“向風車進攻”,將它作為一種不言自明之物加以表述,他的“風車”象徵什麼?當然是巨大、恐怖、虛無、假想之敵。這敵人是外在的不可能達成的目標,當然也是杜裡戈自己心中臆造的目標。在死亡鐵路,“風車”是外在之力強加於他的使命,如同摩西一般拯救“杜裡戈的J部隊”,帶他們回家;在愛拉那裡,克盡職守,將生活進行到底;在眾人面前,扮演他們需要的戰爭英雄;最後,他亦沉入自己的臆想,朝向死亡,他喃喃道“向風車進攻”。
然而,唯有在艾咪那裡,他,杜裡戈才是真實的。“為什麼萬物之初總是有光?”因為艾咪是他的光,指引他發現自己,發現自己在光線中飛舞撞擊的軌跡。艾咪不是他的風車,艾咪是他的港灣。
“暮晚/從海灘上那個女人/傾倒在整個夜浪上。”小林一茶這樣寫道。
理查٠費納根給我們看杜裡戈的三重追尋。更殘酷的是,他給我們看這三重追尋背後的虛無和空寂。
他讓我們明瞭愛的可貴,卻也把它毀掉給我們看。
這部小說,既殘酷又美麗,既纏綿又決絕。它令我們一再回味,並且思考:地獄無處不在,愛將在何處容身?我們在刻下的世界又將如何自處?我們將和杜裡戈一起,頑強抵抗命運的疾風,舉起困頓的長矛,驅動命運的蹇驢,朝前方行進,向風車進攻!

荒蕪之地 最後一人
——馬賽爾٠索魯和《極北》
我的人生算不上什麼磨難,只是風寫在雪上的一個漫長且殘酷的笑話。
——梅克皮斯٠哈特菲德
世界上有足夠多的小說描寫未來,世界上有足夠多的小說描寫人性,世界上有足夠多的小說描寫荒野的殘酷,但卻沒有一部小說描寫未來的荒蕪和僅存的人性,除了《極北》。
我不在乎《極北》寫了什麼年代的故事,甚至沒有興趣去翻查一下。作者虛構了什麼年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是人類曾經到達的境地,也是所有人類最終一定都會到達的地方,那是我們最後都會到達的荒蕪之處——不只是物質上的荒蕪,而且是對生命的輕蔑。
根據小說文本,在未來的某日,梅克皮斯跟隨父母等一群人,遠離高度文明已經開始吞噬人類的美國城市(紐約?或是華盛頓,這已經不再重要),向北一直越過北極圈,越過阿拉斯加,到達最後的荒蕪之地,向俄國政府購買了一片土地,在西伯利亞的某處定居下來,後來,梅克皮斯有了弟弟查洛、妹妹安娜。他們帶來了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工具、種子,希望在這個遠離腐敗的文明的荒野裡,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依靠簡單的生活方式,建立自己的城市,以簡單的虔誠之心確立自己的規則。他們企圖創造自己的世界:簡單、純潔、虔誠,用手勞動,用心感恩。然而,世界的動盪卻從未放過他們。
一個關於荒蕪之地的殘酷故事於焉展開。
人如何與荒野競爭
人與荒野的競爭就是人與惡的競爭,因為人的生存需要生活資源。當生活資源不虞匱乏,我們盡可以努力地向善。但是,當我們最終不免於饑餓、疫病,生活資料的爭奪就變得如此重要。我們不是依靠陽光、空氣就能存活的動物,生命的維繫完全依賴于食物和水的取得。即使在缺乏生活資料時,也沒有人會主動放棄生命,因為生命只有一次,對於個體來說,生命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真正稀缺的東西,生命是最後最有價值的物品,生命是我們最後能夠討價還價的資本。
在《極北》的故事設定裡,我們看到“五月花號”的影子。如果你記得《聖徒與陌生人》這影片,你會想像梅克皮斯的父親就是“五月花號”上的牧師布萊斯特的形象,帶著虔誠的信仰來到這片世界上最北的土地。這裡馴鹿遍佈,一年只有短短四个月看得见阳光。这四个月中间,需要尽力耕种,努力收获,让生命借助于陽光和水肆意蔓延,留下收成好度過接下去的漫長極夜。
1621年11月11日,來自英格蘭的普利茅斯41名清教徒們也是這樣做的。他們在布萊斯特的帶領下,懷著對應許之地的嚮往,經歷漫長的旅程,登陸北美。他們當然也曾因糧食的匱乏和印第安人起了爭執,正如小說中的詹姆斯٠哈特菲德,同樣因為糧食的匱乏而煩惱。不過,在《極北》中,生活資料的爭奪來源於不斷從高速公路前來的形形色色的旅人。外部世界的混亂和崩潰,使更多人投奔、或是經過極北的新移民城市伊凡傑林。強悍的人留下來,投機的人也留下來,信仰最終無法戰勝生活資料的缺乏。人類需要一切能夠讓自己存活的物質,由此產生了爭鬥,爭鬥意味著秩序的喪失和信仰的淪陷。美好生活和簡樸生活的嚮往至此開始分崩離析,人的驕傲抵敵不過生存的需要,然而,在這樣的時候,牧師卻執意固守信仰和秩序。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他需要發現公共的敵人,讓大家再度圍繞在他周圍。如果沒有,那就創造一個。他暗中安排人洗劫了自己的家,強姦了自己的女兒梅克皮斯,毀壞她的臉——這樣,他就有了公敵。他祈禱:“啊,就連聖彼得都舉劍保衛我的上主啊!”
這是惡?這是信仰?某種形式的獻祭?還是人性的巨大空洞?我沒有答案。但是,小說裡的牧師最後無法忍受這樣的喪失:某日,他走進森林,割開了自己的喉嚨——在極度的混亂中,惡最終戰勝信仰。
人性的惡,植根於我們的生物性需求,植根於我們活下去的動力。反向來說,戰勝內部的惡,這就是我們終其一生致力於提升自我的目的。
生命的價值在哪裡
想努力在這荒蕪之地活下去,就得找出一些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不論是物質的荒蕪,還是人性的荒蕪。我们知道:糧食也罷、蔬菜也罷、種子也罷,終會有枯竭的一日,生命在這星球上也終於會有荒蕪的一日。因為荒蕪是一種必然,這一日終將會來到,問題是:我們是否有足夠的種子讓生命繼續?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土壤營養我們的肉體?我們是否有足夠的陽光清洗我們的內在?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足夠的理由,繼續艱難地、困苦地希望?
父親死後,伊凡傑林進一步陷入混亂,梅克皮斯成為了治安官的一員,在混亂荒涼的極北城市騎馬巡邏,手持武器,驅趕暴徒。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伊凡傑林一步一步最終陷入荒涼無人的境地。直到最後的最後,弟弟查洛、妹妹安娜和母親在她的懷裡一一離開,她獨自一人生活在這被拋棄的空城。她收集種子,收集書本,收集彈藥,獨自製造彈藥,獨自獵殺馴鹿,獨自騎馬巡城,在極北的漫漫長夜傾聽母親留下的自動鋼琴,夢想有一日能夠回到春暖花開的田野,手捧鮮花,細細嗅聞香甜的橘子。直到她“發現了”平——從奴隸營逃脫並且懷孕的亞洲女人。
其實,這才是小說回歸人性的起點,也是小說真正的開頭。
發現懷孕的平,這個事實給梅克皮斯一個重要的提示:生命的價值不只是“活著”,而是更加重要的事。兩個孤獨的女人,在極北的荒涼城市,一邊看著荒野逐漸吞噬城市,一邊默默守護著腹中踢動的孩子。生命的開始和生命的敗亡,在世界邊緣奮力撕扯,這就是《極北》驚心動魄的一面。
也許你還記得比較類似的場景,出現在2015年的影片《荒野獵人》(The Revenant)中,毛皮獵人休·格拉斯目睹自己的兒子霍克被殺死,他撫摸著兒子的遺體,那樣的絕望,那樣的哀慟,那樣無處可逃的無言的創傷,來自於我們對於生命價值的懷疑。在那樣的時刻,我們,身為人類,不論是否有信仰,都會感到心靈的巨大黑洞,在那裡,極地風暴粗暴地橫掃一切。
“我沒辦法詳述接下來發生的事,因為太痛苦了,我沒辦法下筆,但是六月,平死了,她的寶寶也死了。”
“在那件事情發生,我的人生目標消失之後,日子非常難熬。相較之下,我自己的厄運和在這之前多年來碰上的一切不幸,都顯得微不足道。”
我們的生存渴望到底有多強
1995年,影星凱文٠科斯特納(《與狼共舞》、《保鏢》的主演)執導並主演了一部口碑很差的科幻影片《未來水世界》。影片講述在21世紀初極地的冰蓋融化,海平面上升,覆蓋了地球上的每一個大陸。倖存的人類散落于海洋上,生活在環礁上,從廢金屬和破舊的海上船隻大多建搖搖欲墜的浮動社區。在不遠的將來,儘管土地為基礎的社會已經最終被遺忘,許多人仍然固守信仰神話“旱地”。在種種艱難中,一位“水手”(有鰓和蹼的怪人)帶領一個小女孩,解開密碼,抵達了最後的大陸。當然,這樣的科幻題材確實並不新奇,以凱文科斯特納的身份(《與狼共舞》獲得七座奧斯卡獎,另獲五個奧斯卡獎提名),理應創作更有深度的電影,但是,我卻印象深刻。至少,這影片探討了一個問題:身為人類,我們的生存渴望有多強?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大陸”,我們究竟願意付出多大代價?
如果說,“平”和寶寶的死亡是我們在小說中遇到的第一個“意外”,那麼,在縱身投湖、決意一死的瞬間,梅克皮斯卻透過湖水,看見了天空中的一架飛機墜毀,這是小說的第二個“意外”。
“找到殘骸的時候,已經半夜了。我很久沒有見過像這樣的東西了,感覺上像個幻影。我半信半疑,以為自己已經沉到水底,夢見了這些東西。”
“平”的死亡帶走了梅克皮斯心中最重要的東西,帶走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對生的渴望,帶走對未來的期許。當我們和她的心一起沉入湖底,飛機的出現拯救了我們也拯救了她。如她所想,飛機定是從白令海到伊凡傑林之間的某個城市飛來,那代表還有同類,還有希望。我們人類就是依靠最後的希望活下來的。億萬年來,我們逐漸離開動物界,成為能夠思索,有自主行動能力的物種,度過許多劫難,乃是因為我們總是會看向未來。未來的不可知給我們以模糊的希望,那光點再小,也值得我們為之付出,並且奮力活下去。為何死亡是不好的?哲學家說,因為它帶給我們“被剝奪”的感受,“被剝奪”了在未來享受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正是可能性,讓我們能夠鼓起勇氣面對目下的困難,勇敢地將破碎不堪的過去丟在身後。
於是梅克皮斯就這樣走開,封死代表過去的窗戶和房間,牽著兩匹馬,行走在極北荒涼的雪地上。當然,可以預見,她在這生命的荒蕪之地只會遇見更加殘酷的打擊啊!所以,小說帶著我們,陪伴她走到霍瑞柏,一個同樣荒涼的小村。然後,我們看著她在霍瑞柏一步步走上絕境,一步步因她倔強的自由天性被歧視,一步步成為偏執之徒的奴囚。她走在奴囚的道路上,重過家園伊凡傑林,我內心裡多麼祈求作者放了她,讓她就此逃回自己的小屋,回到孤獨但是平靜的生活!但是小說家偏要進一步抓住她、折磨她、摧毀她,給我們看:她的生存渴望到底有多強?
我帶著流血的傷口看梅克皮斯艱難前行:在奴囚營中努力生存,偽裝自己。我在她身上看见:在盧旺達屠殺中東躲西藏的人們;在赤棉屠殺中倖存的人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給孩子講述美麗人生的父親;在切爾諾貝利之後委屈求存的母亲——這些人,逆著狂暴的命運風雪前行,每一步如此艱難但確實未曾退讓。每一步自有其前行的價值,”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一過“,未經努力的生活也不值得一過。
追尋自由,這就是梅克皮斯努力的價值。
世界的盡頭在哪裡
“每個人都料到總有一天會來到某件事情的終點;
沒有人料到的是,我們竟然會來到一切的終點……”
世界的終點在哪裡?取決於我們討論地理上的終點還是形而上的終點。若是看過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遺跡的圖片,或是去過復活節島,一定會認為:那就是世界的終點。關於復活節島,社會人類學家賈德٠戴蒙德在其三部曲社會人類學巨著(《槍炮、病菌與鋼鐵》、《昨日世界》、《大崩壞》)中描述過最後的韓德森島島民(和復活節島一樣是荒蕪的南太平洋小島):“最後的韓德森島民是否一代連著一代,孤獨地在海灘上度日,望眼欲穿地看著無邊無際的大海,等待著獨木舟再度駛來?”那是否世界的盡頭?一切的終點?
如果你看過一部皮克斯的動畫電影《機器人瓦力》,想必也會記得小小的滿身鐵銹的瓦力,在一隻蟑螂的陪伴下,孤獨地在地球漫遊的情景?你是否也如我一樣倍感辛酸?
我們的心酸來自同情心,因為我們身處富足社會,衣食無憂,身邊有朋友、家人、同事和數不清的陌生人,我們未曾體會過他們的境況但是能夠感受到。不過,如果有朝一日,我們淪落到他們的境況,我們恐怕沒有時間感傷。正如梅克皮斯終於獲得了某種自由的象徵,可以去“特區”,她揀選了最好的朋友夏蘇汀和朱爾複嘉同去,結果卻發現——那是類似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遺址的輻射重災區,她終於在這空城裡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尤其是,當唯一的朋友也行將離開世界。
“到中午,夏蘇汀死了,然後馬也死了。但我活下來了。嗯,我就是有這種運氣。”
當她走到這世界的終點,梅克皮斯終於發現了當年強姦她的那個人,她幸運地——不如說是作者仁慈地——得到了復仇的機會,她複了仇,離開這一切最後的殘存的醜惡,最後的關於舊世界的荒涼回憶,“我穿越大地。夏季來了又走。等我走到最後一段往北的路程時,夜裡已經有霜,北極光也已經出現第一道綠光”,她回到一切開始的起點,極北的荒涼城市伊凡傑林。
但是這裡是家鄉。
所以這裡是世界的起點而不是記憶的終點。
更何況她有了和夏蘇汀的孩子。
我想,讀完小說最後一個字的時候,極地的風雪聲猶在耳邊呼嘯,但是,春天開始傳來將要到來的訊息,這真是一個令人釋然的訊息。梅克皮斯,這個無比堅毅的女人,在經歷了那麼多無常、折磨和命運的翻騰之後,似乎終於能夠放下過往人生中的種種,在世界盡頭的城市裡,看著自己的孩子成長。但是,一股沉重的感覺卻還是久久不能散去,在我心頭縈繞。
我再度想到賈德٠戴蒙德在《大崩壞》一書中所描繪的最後一人的場景。那樣的境況在我們的歷史上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過了;再度發生並非不可能,也許只是何時而已。我們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我們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紀,我們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星球。若說有什麼能夠讓我們暫且安心的,也許只有訴諸於內心的良善、溫暖和希望。
身為人類,如我之前所說的,我們對於未來的期待總是能夠推動我們持續前行,就算我們並不知曉明日將會有怎樣的命運在等待,我們總會覺得那不會比過去更糟。有時這是盲目樂觀,但有時這是唯一的動力,梅克皮斯若沒有這樣的希望,她早已沉沒在湖底——當然就沒有如此驚心動魄的旅程。
所以,她在故事的結尾說:“在大風吹倒消防站的瞭望塔之前,我會一直站在那上面眺望你在雪地上留下的北行足跡,輕聲對自己說:平啟程回家了。”這是她給孩子的信,這是她留給孩子的書。
孩子,回家,回北方去。
如何优雅地老去?
... 看更多-----《最好的告别》书评
什么是衰老?
衰老是时间之箭的象征?是我们的肌体无法抵抗损耗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还是我们给予自己的一种暗示?
阿图·葛文德医生借助他的朋友菲利克斯之口给我们的定义是:“老年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第一阶段,丧失对自己的躯体全面掌控能力;第二阶段,丧失对自己的行动的掌控能力;第三阶段,丧失自己的家,熟悉的房子、家具和对生活步调的掌控能力;第四阶段,丧失对于生活的信仰;第五阶段,不得不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医护人员,丧失了自己的隐私;最后,丧失了对于自己死亡方式的选择。
阿图医生引用作家菲利普·罗思(Philip Roth)在小说《每个人》(Everyone)中说的话:“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来说明步入老年,生活充满了“苦涩”之感。
在现代社会,步入老年的年龄定义随着科学的进步而不断推迟。原始社会的人们活到30岁已经不容易,东方古代社会则以70岁为“古稀之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依旧健步如飞,甚至还在继续工作。但是,不论如何,我们都会来到这一天(如果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不能如厕、进食、穿衣、洗浴、整容、下床、离开座椅、行走(‘八大日常生活活动’),那么说明你缺少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如果不能自行购物、做饭、清理房间、洗衣服、服药、打电话、独自旅行、处理财务(所谓‘八大日常生活独立生活能力’),那么,你就缺少安全地独自生活的能力”……问题是:当我们来到这一天的时候,我们还能期望保有自己的哪一部分生活?这时候的选择非常严峻。是留在家中让老伴服侍(如果你幸运地拥有这样的老伴)?还是进入疗养院,让专业的护士来管理你的饮食起居?显然地,后者的代价是丧失自己的隐私和对生活的掌控力,这一点常常会伤及我们的自尊。
针对这个问题,阿图医生指出:“对于人们最要紧的目标:在我们衰老脆弱、不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如何使生活存在价值”,或者说,“是什么使生活值得过下去”?
我有几位叔伯长辈,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看来个个都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在社会生活中也颇为成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先后受到家族遗传的困扰,中风、高血压、老年失智症、以及各种癌症侵蚀他们健壮的躯体,最后把他们彻底放倒在病床上,彻底或者几乎彻底失去了意识,完全依赖家人的照顾,才能在没有任何尊严的情况下,艰难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如今,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的父亲身上。所幸我的母亲尚能照料他,但是,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他的记忆就会像老旧的磁带那样,一点一点变成空白。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我应该强行把他从自己所熟悉的家中带走,交给陌生的护士照管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剥夺了他在家中离世的权利呢?对于目前这种生活,他是否认为有“价值”呢?当我凝视着他浑浊的双眼,我很想从中读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显然地,我找不到答案,因此,这个问题只能无限期地搁置起来。
仿佛是对我的回应,阿图医生在他的书《最好的告别》中写道:“衡量人们对药物的依赖下降了多少、多活了多久比较容易,而衡量人们从生活中得到的价值感则困难得多”。针对这一点,他举出了一些例子,一些想要帮助老人追求生活价值的人建造的不同概念的疗养院。他们的共同理念是: 帮助处于独立状态的人们维持存在的价值。比如:提供生物给人们照料,或者,给他们一扇可以上锁的门和一间属于自己的厨房。因为,“唯一让死亡并非毫无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某种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区、社会”。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才“有可能保留塑造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故事的权利——根据自己的优先顺序作出选择,维持与他人的联系”。
思考到这一点,也许我还是得尊重双亲的选择。他们决心留在家中养老,当然存在诸多的不便,对于我的家庭来说,也可能意味着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尤其是东方社会的伦理压力。但是,也许,这也是他们“塑造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故事的最后一段机会”,或许,我们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直到某个不可预知的时刻到来?
当然,在东方社会,尤其是在医疗以及社区养老还不甚发达的地区,我们很难侈谈老人的尊严。由于各种现实情况的变数,老人们即使在养老机构也未必可以享受到专业的护理,更不必说在家中期待社区养老,但是,我们还是得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自己将来总会老去的事实,也得有足够的勇气来思考自己希望怎样优雅地老去。正如阿图医生所指出的那样,认识到人的必死性,才有足够的勇气来思考怎样结束。“结尾不仅仅对死者重要,也许,对于留下的人,甚至更重要”。像阿图医生所说和所经历的那样,“宁静的终了是一种祝福”,这样的终了,不应该是躯体插满各种管子,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戴着氧气面罩的结束。
我想:在离自己的终点看似遥远的时候,在自己的发梢浮现第一缕白发的时候,在爬了一段楼梯感到气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做好准备,具备阿图医生所说的两种勇气:“面对人终有一死的勇气”,和“依照我们发现的事实采取行动的勇气”,清楚地做出决定,确定自己希望以怎样的方式面对衰老,要以怎样的方式面对万一发生的病痛,以及——在将来的日子里,要如何优雅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