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喜歡看相?結構學派也許會這樣回答:因為我們希冀征服時間;將過去和未來,都濃縮成手心的痕跡,時間即盡在我們掌握之中。音樂和神話,都接近最純粹的形式。其實手相也好、面相也好、骨相也好、紫微斗數也好,不也都是純粹的形式嗎?我考慮血肉之軀的存在,單憑線條和數字,就能推斷人的過去未來,正是形式主義的極致。所以看相,和音樂或神話一樣,也是「征服時間的機器」。
這幾年來,我數度應邀擔任報社「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工作,因此讀了不少篇報導文學的作品。許多作品都流於一種新的窠臼,無以名之,姑且稱為「歷史感的窠臼」吧。有些作者,或許受了時代潮流的影響,努力尋根。於是,破落的古廟、即將拆除的老宅、沒落的小城鎮……都成了報導文學的最佳對象。這類作品,在大張旗鼓的作了今昔對比之後,免不了加上一段半帶感傷、半帶無奈的文字結尾,惋惜古廟、老宅、小鎮不能維持舊觀。
讀多了這類充滿「歷史感的窠臼」的作品,我反而不免懷疑,為什麼要保存這些已成空洞的形式呢?即使它們代表祖先及前輩征服時間的努力,和活著的人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不能闡明其間的關係,這樣的報導文學作品,就不免成為濫情的感傷主義作品。
從野蠻到文明,我們喪失了這整體的宇宙觀;但我們仍舊希冀征服時間,獲得不朽。文學於是成了神話的替代品。但現代文學經常墮落成為空洞的形式,徒然反映現代人被割裂的靈魂。
野蠻人的整體的宇宙觀,在生態學及環境污染問題受到重視之後,倒通過種種方式重現。如果人的意識的確有其結構的話,野蠻人和文明人的意識結構,自然是共通的。整體的宇宙觀今天會再被哲學家、經濟學家、生態學,甚至政治家發掘出來,因此也就不足為異了。
韓韓女士與馬以工女士這本文集的主題,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她們所鼓吹的,也可以說是整體的宇宙觀。由於有了這個整體的宇宙觀,文集中許多篇報導作品,無疑更加有意義。她們的努力,經常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也產生了實際的影響。我很欽佩她們的精神,不僅期望她們能繼續堅持下去,也期望有更多的人能參加她們的工作。也許,野蠻和文明的分別,就是野蠻人自然而然就相信整體的宇宙觀,文明人卻必須接受兩次大戰的教訓,生活在核子毀滅的陰影下,才能重新尋回這片心靈的樂園吧!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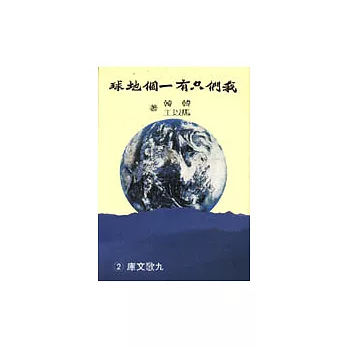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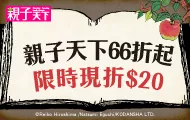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