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莫非此生就是地獄
作家/郝譽翔
初識文音,是在上個世紀的九〇年代,我們因為文學獎而結緣。那時台灣的文壇仍然有如奧林匹斯山眾神的國度一般熠熠發光,而剛戴上文學桂冠的我們,更是天真的以為從此自己就踏上了峰頂,至於未來呢?恐怕也只有更高的峰頂了,壓根兒沒有想到桂冠也有枯萎的一天,更不用提老。
尤其是文音。年輕時的她活脫脫就是少女三毛的翻版,長髮飄逸,纖細溫柔又透露著野性,矛盾的混合顯得格外迷人而且神秘。我還記得她的《昨日重現》剛出版時,台北車站地下街的櫥窗貼著大幅長條的新書廣告,彷彿處處都是海報上她那雙深邃迷離的大眼,在注視著過往的行人,來去匆匆如流水的世界。
其實在二、三十歲的年紀談「昨日」,多半帶著點浪漫懷舊的意味,就像是旅行遠走一樣,都是一個人自由自在的追尋探險。地球是圓的,沒有邊際可言,而時間更只有當下,無牽無掛,揮霍不盡。
然而一眨眼,那些卻真的變都成「昨日」了,我們還來不及驚詫,就一腳跨過了半生,如今文音的「昨日」猶在,卻不再流浪天涯,而成了深情戀家的老靈魂。她現在要說的是「高齡求生」,而「故事未了,黃昏已來」,昨日已經不可能「重現」,但它也未曾死去,一縷魂魄悠悠附著滲入了物件,在日常生活中點滴堆砌,累積固著有如老少女一雙臂膀上肥大的贅肉,攬鏡見著了只讓人膽戰心驚。
女人誰不怕老?誰不自欺芳華猶在?然而文音這一回卻毫不迴避,《溝》書寫「老」到了殘忍的境地,甚至用放大鏡去逼視—―—「有點年紀的女人流的淚會滑過皺紋,卻無法灌溉歲月。」「都說老人的淚是伊底帕斯王,想哭沒淚,想笑卻掉淚。」這些警語也未免太讓人倒抽了口涼氣,彷彿一針見血戳中了老的荒謬與無奈。
文音以幾近於諂刻少恩的手法,寫盡了各式各樣的「老」,可悲、可笑、可憐又復可恨之處,推翻了老年書寫一貫充斥著養生慢活的陳腔濫調。且看她揭露了郊山安養院的真面目―——「連這裡的交誼廳都是有地盤的」,而老人一點也不因為老而溫良恭儉讓,反倒是彼此之間心機用盡,狠烈廝殺;喪妻的老男人在倒下之後,全身差滿了鼻胃管、導尿管等,淪為一個靠兒子把屎把尿的「管管大人」;K歌坊中聚滿了一群「不唱歌,像一千零一夜,談八卦保持求生,搭配曖昧氛圍求年輕」的老台妹們……,《溝》的三十多則故事組成了初老之人的眾生相,他們聒噪喧囂,反抗老去卻又不得不老,從肉身到靈魂無一不在掙扎喊叫,只得訴諸於靈修、觀落陰、醫藥、保險到心理治療,最終卻還是要色相敗壞,天人五衰,衣冠頓萎,味覺嗅覺聽覺與觸覺一併腐爛,而漫漫一生到頭來只餘「老後江湖,引海成沙。」文音寫得辛辣蒼涼,幾乎把老年書寫推到動人心魄的極致了,我實在很難想像還有誰能夠超越?
其實我和文音這一代人都還未老,或者應該說是來到了門邊上,正忐忑不安窺探著門內幽深的世界,但她對於這一切,卻似乎比我們都更早瞭然於胸,提前道出了「黃昏已來」的求生之志,而其志是如此的沛然莫之能禦,哀豔淒厲,讓我不禁想起了吳道子的〈地獄變相圖〉。論者評〈地獄變相圖〉是在「寺觀之中,圖畫牆壁三百餘間,變相人物奇臥異狀,無有同者。」《溝》竟也是如此,三十多則故事所勾勒出來的高齡人生,光怪陸離之形狀,成住壞空,滿紙風動不已,而人生無邊苦海的本質立現眼前,莫非此生就是地獄。
推薦序二
讓我們一起老
作家/郭強生
一直記得與鍾文音初回的素面相見。
當年我剛回台任教,落腳於東海岸的大學,她來學校演講,結束後郝譽翔開車載我們去吃路邊熱炒。小小的廣場,初秋的晚風舒爽,我們坐在大榕樹下喝著啤酒。現在想起來,都才三十來歲的我們還是孩子,只有孩子才能很快就混熟,沒有世故的拘謹和再過幾年都將出現的疲憊。文音愛笑,那笑聲帶著鼻音,我邊聽著她旅遊的趣事,邊抬頭東看西看那個當時我還未熟悉的東部生活環境。很鄉土,卻也像置身異國。
就這樣流年偷換,舊識卻算不上熟識,直到最近這些年,我們都成了得要獨力照護年邁至親的單身子女。
無人能伸出援手,只有彼此互相打氣,交換著只有當事人才知的甘苦。那個熱愛異鄉漂泊的波西米亞靈魂,與另個依賴老歌老酒為伴的書房宅男,就這樣出現了新的交集。去擔任研究生的論文口試委員,一次碰到的題目是《郭強生與鍾文音的單身中年書寫》,一次則是《鍾文音與郭強生散文中的老年照護》。
最近一次碰面,文音明顯瘦了一大圈,身影變得格外單薄嬌小,我本能地擔心問她怎麼了?年過半百,單身獨居又要擔負著長照重任,這些年下來我變得杯弓蛇影般神經質。結果文音告訴我她在改變飲食作息,減重有成。不但如此,她還完成了新的小說作品。哇不得了,我在心中讚嘆著:前年才剛出版了擲地有聲的長篇小說《想你到大海》,創作力大爆發呢!
這回寫什麼?我問。
老年地獄圖,她說。
語未竟,我們都同時笑了出來。我聽到自己笑聲裡的無奈,卻聽見文音的笑聲裡,依然是那帶著鼻音的少女。
然而,翻開這本新書書稿的第一篇故事〈狐仙已老〉,又讓我吃驚了。明明眼中還是她纖盈的背影,怎麼會寫出有「嬸味」的懺情?《中途情書》、《愛別離》、《寫給你的情書》……中那個迷離哀訴的敘述聲音,如今卻出落得異常生猛俐落,句句都戳到痛處:
「還是一個人好,雖然有時很孤獨,但出去更孤獨,好像老了不該出現在路上。」
「習慣養成需要時間,但她已沒有太多時間。所以很多事變成偶爾。」
「未完成的故事都屬於天涯海角了,天涯海角再也去不得。現在要完成的故事都屬於過去。」
單身中年如今已逐漸邁入初老,照護者即將要成為無人照護的孤老,我只不過是活成她筆下的那句「接受比反抗容易」,她卻如此昂首闊步地直搗她口中的老年地獄。畢竟是寫出過《豔歌行》,《短歌行》、《傷歌行》百年物語三部曲的鍾文音,過往冽豔陰鬱的文字這回添進了辛辣與直白,一腳踢開什麼「熟齡樂活」的自我催眠,冷眼犀利地直視自己可能遭遇的老後,這真的需要一些氣魄。
全書三十四個故事,如一帙畫卷節節展開,緊鑼密鼓讓人無法不一口氣往下讀。
與其說是老年地獄圖,恐怕更接近高齡求生的教戰手冊。文音勾勒人物的功力既準又鮮活,叔嬸伯姨出現的場景更是多樣真實得令人過目難忘。從養老院到棺材店、從部隊軍旅到保險業務,生活氣息的逼真摩寫,這種日常生活中的田野功力,值得小說後學者好好見習。
曾經,那個追隨著莒哈絲、普拉斯、伍爾芙的步履浪跡天涯的鍾文音,現在哪兒也去不了,與臥床的母親相依為命於淡水八里。但是這一點兒也限制不了她總欲探訪下一個邊境的靈魂。
這回,她要探險的新大陸不在遠方,而就是眼前快進入超高齡化社會的台灣。一如青春時對愛情真相的勇於索問,如今她對病老死的辯證,對獨身的反思,展現了同樣的義無反顧。
讀完這些故事,腦海中不禁又浮現大榕樹下喝啤酒的當年。
三十多歲的我們都還在愛著,還想要愛著,怎想得到半百之後,竟然在憶起那些愛與不愛的糾纏起落時,只能嘆一聲都是虛枉?
故事未了,黃昏已來。兜兜轉轉還是放不下,影影綽綽盡是傷心人。
早就注意到,銀髮商機主要鎖定的還是有家有後的族群,甚至那些養生抗老保健補品廣告想打動的消費者不是老人,而是那些於心有愧的離家子女。君不見,廣告片中總是出現兒孫輩友孝,奉上燕窩人參高鈣銀寶維骨力,最後老人與晚輩一起勇健跑步,闔家笑嘻嘻樂融融?
高談長照,鼓吹銀髮樂活的年代,獨身的大齡子女們都還在忙著照顧更年邁父母,何來樂活?獨身二字在一般的認知中也只有樣板的概念,「眼光太高了吧?」「個性難相處吧?」殊不知,是因為我們對情字的執著,放不下父母,容不下曖昧,只能用後半生修習放下,超脫情字帶來的磨難。
在先前的散文集《捨不得不見妳》中有一段,聽見母親對她說「沒有我,你會很難過的」,文音寫下了思索之後的心情:
「我當時聽了心想怎麼會,我會悲傷,但同時我也會覺得自由。我沒有體認到我的自由感其實是建立在擁有母親的安全感上,我不曾擁有真正的自由,我的自由只是一種逃脫,心仍牽掛許多東西。無所牽掛,才有自由。」
總是在牽掛著,以至於最後我們都忘了如何釋放自己。作為讀者,我要謝謝文音寫下了這些故事,關於我們這些處在新舊交接、五年級世代中的少數族群。
從私散文到小說中的紅塵眾生相,她拿自己的傷口去碰撞,在我輩同類間一個又一個似陌生又熟悉的遺憾中,撞擊出共鳴,或許終能讓老年擺脫社會眼光的規範,讓單身者的餘生出現真正自由的可能。
能夠這樣發願書寫老年,我必須說,既需要極大勇氣,也需要滿懷慈悲。
書近尾聲,那篇〈滅絕師太〉的結局場景讓我意外地笑了。搬離前夫家的女人,決定「即使餘生要照顧母親也是自己的餘生」,為了自由,把其它的都丟了,除了自己的母親。結果馬路上的人都在看著這奇異的畫面,竟然有人推著電動病床在街上移動,床上還躺著瘦弱的老人家。
前進吧,別人的眼光哪裡需要在乎?
彷彿聽見,畫面外的文音也吃吃地笑了,依然帶著她那有些頑皮的鼻音。她說,讓我們一起老。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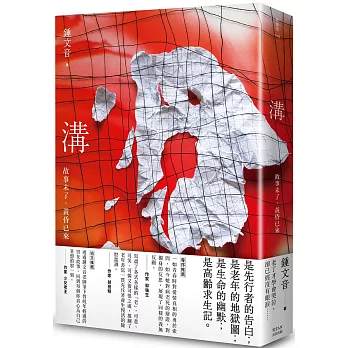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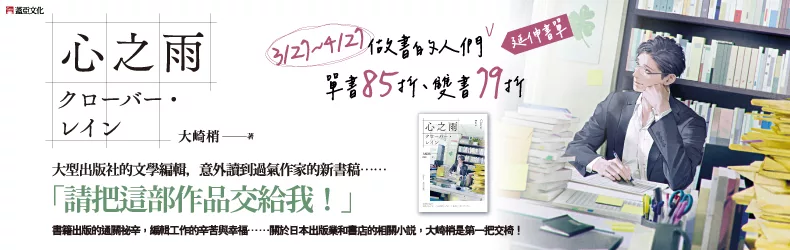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