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飛駛在沒鋪枕木軌道上的民主與愛情
須文蔚
朱國珍在二○一五年發表的詩作〈Nhari〉,以太魯閣族語「快」一詞,表現出時代巨輪呼嘯而過,原住民族不僅被拋諸在偏鄉或都市角落,更讓勞動體制與槍枝管制等看似文明的法制屈辱,但凡漢人的鼎故革新,總是族人的滄桑悲涼。所以當她繳出《古正義的糖》一書時,從部落汩汩流出的淚水,哀嘆著島國崩壞的紀事,無論是故事中的政治菁英或是戀人,彷彿都飛駛在沒鋪枕木的軌道上,享受速度的快感,但無一倖免於出軌的悲喜劇。
接續朱國珍在《慾望道場》一書對台灣政治、媒體亂象的針砭,在新作中聚焦在原住民部落政治和台灣地方選舉,從而暴露出台灣民主的黑暗面,充滿了誹謗、誣告、賄選甚至謀殺,讓人觸目心驚。
主角古正義的故事原型,來自朱國珍舅舅的親身經歷。類似的民主哀歌,彷彿一道魔咒,牢牢盤據在花蓮原住民族的歷史。早在十二年前,我就聽秀林鄉人說過廖守臣的故事。漢名廖守臣的馬紹‧莫那生於民國二十八年,畢業於台大歷史系,大學時代就投身原住民文化的田調及研究工作。在民國五十六年返鄉任教於花蓮高中。在這段期間,他不僅是一個學生敬重的歷史老師,更勤快地上山下海,挖掘原住民的文化、歷史根源。廖守臣在擔任教師十年後,辭去教師出馬競選秀林鄉長,高票當選,並獲得連任。他卸任後,卻因為官司纏身,鋃鐺入獄,同一時間,從高雄醫學院畢業的獨生子,竟在一場車禍中亡故,讓廖守臣陷入空前的悲劇中。而和廖守臣一樣有著司法困擾的原住民政治菁英,不在少數。
古正義面對的時代,又和前一代的族人大相逕庭。在一九九○年代,台邦.撒沙勒就提出「原鄉戰鬥」和「部落主義(tribalism)」的主張:
「部落主義」就是我們的實踐哲學,是我們對原運長期發展的攻堅戰略。我們主張,原住民的運動團體和運動家們,應全面放棄在都市游離而回到原鄉部落;遠離霓虹燈彩的迷惑,投向山海的懷抱,去實踐自我,去耕耘土壤,去擁抱基層,去關切民眾基本的生存問題,這才是擴大原運實踐空間、充實原運內涵、強化原運實力的根本知道。
古正義就是在這股風潮下,回到原鄉,開展部落工作,投身社區營造,以他服務公部門的資源與經驗,辦民間圖書館、電腦教室、合唱團、社區導覽等,以為帶給村民現代化的力量,就能夠取得民意,進而領導原民鄉鎮。他所沒有思慮到的是地方政治,終究還是金權打造,不配合這個邏輯的人,縱使自身清廉,也難保不受到誣陷。朱國珍在剖析部落選舉的光怪陸離時,手術刀般的筆鋒也指向另一樁政商勾結,黑幕重重的地方選舉。《古正義的糖》另一條故事軸線,彷彿向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的《預知死亡紀事》致敬,預言為了汪志群勝選,不擇手段,一定要殺一個人,製造悲情,換取選票。候選人、黑道、殺手與讀者從小說開篇就知道凶案必定發生,隨著角色一一登場,讀者或許會為他們祈褔,期望正義實現,峰迴路轉,可是終究讀者會發現朱國珍對摯愛角色總是萬分殘忍,正說明了她冷靜面對現實的精神力量。
在處理愛情故事上,《古正義的糖》也出奇冷靜,闡釋了幾個世代,充滿了陰影的愛戀關係。無論是古芝琪與戴登綱的原漢結合,老夫少妻,互不理解,終究婚變。他們的下一代,戴安若有著台大經濟系文憑,隨著先生赴美,美國夢也因為先生走私坐牢,離婚後帶著兒子回台灣,陷入了汪承熙的愛情陷阱中,也捲入家族的漩渦。古、汪兩家的青年人,醫生古恩和學戲劇的汪洋洋,看似一對歡喜冤家,各種巧合撮合了他們,在來去如飛的都會生活中,他們的愛戀是否如同搭上一趟失速列車?就有待讀者解謎。
整篇故事中,最模範夫妻的典型莫過於古正義與宋美怡,他們患難與共,不離不棄,宋美怡無論面對貧窮、分離與丈夫的牢獄之災,她都能隱忍而堅強,雖然台灣看似充滿機會,也讓這一家人從小康漸漸累積出安定的成果,孩子甚至考上醫學院,但一旦丈夫起心動念,沾染了選舉,政治會使這一家人誠實打拚的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
推敲朱國珍有意告訴讀者的似乎是:在台灣,紅塵男女的情愛與家庭充滿了裂痕,即使能克服了故事中鋪設下的種種困難,無論是門第觀念、認同差異、生涯分歧或是災厄困境,戀人還會碰到其他的挑戰,命運一樣會拆散他們。人間情愛不是單純的浪漫結合,如果大環境就是邪惡敗壞的,那麼「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的慨嘆,就會一直迴還復沓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縱使身心交瘁,也無法求得完滿。
勇於揭露現實的朱國珍,並不打算為政治亂象和世間怨偶提出解方,如同契訶夫所說:「小說家是發現問題的,不是解決問題的。」朱國珍以看似報告文學和大眾類型小說的筆法,讓他熟悉的部落親人,輪番證言,汪洋宏肆,辛辣荒謬,極盡黑色幽默,語言操控的力道又勝過前作《慾望道場》。
台灣原住民擅長幽默,最菁華者,莫過於每年公廣集團製播的《聲翻笑哈哈》,每年推陳出新,依舊笑聲不斷,可以作為明證。而朱國珍顯然從生活中出發,沉浸在族人的黑色幽默中,無論是殺豬慶賀的傳統、古學良的「汽車旅館」、搭承包機出國旅行的歡愉等等,在在讓人忍俊不止,但說這些笑話並不是冷酷麻痺,而是以笑聲傳達失去的和諧,以驚愕道出生活中的困境,最終反覆傳誦在世人往上微彎的嘴角上,在笑後化為眼角的一滴眼淚。就像老舍所說:「經驗是生活的肥料,有什麼樣的經驗便變成什麼樣的人,在沙漠裡養不出牡丹來。」朱國珍透過這部長篇的書寫,充分展現出她從太魯閣族人身上汲取的養分,以及她在山風海雨中生活的經歷。
處處充滿原鄉氣息與寫實風格的《古正義的糖》,朱國珍並沒有朝向大眾小說的筆法,而是在敘述、描寫或評價上,突如其來進行後設的書寫,以學究的筆法,逼迫讀者放緩閱讀的節奏。例如,在古恩帶女友錢盈君回家,漢人女子面對著狩獵與殺戮,不免暈眩於血腥的氣味中,朱國珍如是描寫:
味道是一場儺戲,它戴著面具翩翩降臨,幻化天使或鬼怪。力比多分泌旺盛的時候自動製造多巴胺香水激素,纏綿在體液交換之間不會在乎他/她上一餐吃的是和牛或鹹魚,喝的是香檳或保力達B。飢餓的公式也差不多,三天不吃東西可能會讓人看到皮鞋都想吞下肚,此時若是湧出一陣烤肉香……那可是人間最催情的味道。查爾斯•蘭姆認為人類是因為意外燒掉房子才發現烤豬這種美味,讓飲食文明由生食進入熟食。
於是一場看似《誰來晚餐》的族群文化衝突,就以詩化語言佐以科普知識,更深刻地探討了箇中哲思的多種取徑。
朱國珍顯然鍾愛族人,他形容步入中年的古清輝五官俊美依舊,只是歲月滄桑,折損了神氣,因此:「即便如此,並不妨礙他的大腦在有限時空中思索無限人生哲理,片刻的沉靜雷同法國藝術家羅丹的青銅雕刻『沉思者』。」小說家不滿足以遠取譬的精彩,神來一筆:
聽說羅丹的靈感來自於但丁《神曲》地獄篇:「從我這裡走進苦惱之城,從我這裡走進罪惡之淵,你們走進來的,把一切的希望拋在後面。」
又點出人類有限智慧無法擺脫苦惱與罪惡,道出本書悲觀與絕望的宿命觀點。
《古正義的糖》所描寫的太魯閣族部落,沿著中央山脈的腳下,星羅棋布,從北邊的秀林鄉,一路散居到壽豐鄉、鳳林鄉乃至萬榮鄉,都是腹地狹仄,地形險惡,窮山惡水的所在,也曾經一度是台灣失蹤少女人數最多,乃至於背上「雛妓之鄉」的惡名。朱國珍看似輕描淡寫部落同胞在都市中遭剝削、賣女兒蓋高樓的故事,在小說中插入:
馬路和黃春美不會認識二○一八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娜蒂雅•穆拉德(Nadia Murad),他們也不會知道六十年後還有人為保衛部落而奮戰。娜蒂雅•穆拉德被滅族的時候她只有二十一歲,恐怖主義極端分子的武裝團體伊斯蘭國以宗教名義在中東地區持續進行大規模屠殺與迫害,亞茲迪部落正是其中之一。
在朱國珍筆下,馬路、黃春美、湯英伸與娜蒂雅•穆拉德都一樣,都是在殖民、階級與資本的壓迫下,淪為勞工甚至性奴隸,成為勞力市場的物件,無情地遭到販售。讀者或許會對小說家不斷岔題、指點與推論的後現代敘事,感到不耐,但能從論述中靜下「延伸閱讀」,思考多少邪惡是假正義之名?或許能理解作者的微言大義。
《古正義的糖》是一部虛構與真實並濟的「家族書寫」,雖然家人輪番上陣,但是篇幅最多,形象最立體,內心的描述也最飽滿的角色還是戴安若,既透過她銜接了部落與漢人世界,也透過她串連了過去和現在,而她失去母親疼愛的背景,加上古和平與林春華五個子女,古明珠、古清輝、古學良與古正義都次第登場,佔有一席之地,只有古芝琪成為「失蹤人口」,既在故事中離家,也在小說篇幅上缺席,呼應了朱國珍從《三天》以來,經常出現母親不在場的抱憾與疏離,究竟是小說結構上的疏漏?或是作者有意的剪裁?相信讀者應當會有不同的評價。
在我閱讀《古正義的糖》的過程中,朱國珍三易定稿,展現出她認真與執著的一面。也讓我體會到,她在這本黑色幽默中的笑聲,絕對不是嘲諷、奚落或挖苦,而是同理、同情與憐憫。在最後定稿時,她將詩作〈Nhari〉壓卷,成為迴盪在山風海雨中的歌謠,也為整部小說「悲喜劇」的性格定調。「悲喜劇」的定義始於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他開創此一劇種無非想跨越悲劇的沉重,喜劇的輕鬆,形塑一個新的話語空間,他曾以以婚姻關係來定義「悲喜劇」:「開闢了通向新型喜劇的路途,比以災難結束的悲劇更悲哀,誠如不幸或者無比幸福的婚姻,都比火車事故更可悲一樣。」因此,《古正義的糖》一書中的人物,都像是飛駛在沒鋪枕木軌道上的火車一般,無論是涉足政治,或是企求愛情,在全書結尾時,讀者很難預期誰會死去?誰會失敗?更不會有童話般「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大團圓結局。朱國珍留下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古正義的厄運還能壞到什麼地步?他灑下的糖果會如同甘霖滋養仰首向上的孩子?還是不忍卒睹地讓汽車與貨車碾碎?故事最後出現的新生代戴正和古真能否顛覆島國的不義?
對台灣總保有一絲希望的我,期待朱國珍的《古正義的糖》不是預知島國崩壞紀事,而是一服湯藥,讓患者發熱甚至發顫,終究能理解自身的貧弱,終究能重新起身、奔跑與在世界上競逐。
(本文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特聘教授)
後記
說一個政治愛情與道德裂縫的故事
「這時候一定要有一個人死掉。」
叼著香菸,身材瘦小的男人這麼說。
另一個身材魁梧,留著八字鬍的男人點頭同意:「若沒,這齣戲就歹演啊!」
這是我在長篇小說《古正義的糖》作為開場白的對話,也是全書的核心符旨:一齣即將開演的人生大戲,一個必須死掉的人。
俗話說「殺人不過頭點地」,相較於人死斷氣的瞬間,它的另一面「生存」可能才是個大問題,不只是因為活著的時間忒長,還有活著時「生存的意義」。存在主義先驅,丹麥哲學家齊克果以美學與神學的觀點將「存在」區分為「道德領域」與「美感領域」,兩者之間有昇華有掙扎。美國文學評論家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裡闡述:「只要我們真正認真地體會故事中的人物,這些人物所面臨的道德選擇,以及我們自身發生的或好或壞的道德變化,我們的生活便會改變。」
從寫作者視角來看,小說中的神聖或世俗、好或壞、都只是裂縫的差距。
所以走到《愛情的盡頭》時莎拉必須死;不忠的《安娜•卡列尼娜》也必須死。
我很少在小說裡以死亡作為高潮的催化劑,除了一開始就設定必要之惡的終結,例如〈慾望道場〉離經叛道的新聞女主播與〈美到這裡為止〉高智商殺人犯。這次在長篇小說《古正義的糖》處死兩位女主角,一方面是堅持《詩學》的信仰,讓悲劇誘發憐憫與恐懼的情緒,達到洗滌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明白自己老了。悠悠呼已過半百年歲,五十不一定知天命,但凡親身體驗更多至親好友的生老病死,有善終也有暴斃,深深感觸人生愈苦愈惡愈需要一種溫柔的調和劑,姑且稱為「善之必要」。我們在悲劇裡看到高尚的人遭遇不幸,也看到處於不幸之中人的高尚,藉此得以獲得某種陶冶,尤其是在道德上震撼人心的同時激發出理性力量與審美感受。《安蒂岡妮》劇中都是無辜的人死,惡人繼續享福,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創造出戲劇界與精神分析界天王伊底帕斯,索氏手下留情,讓弒父娶母的伊底帕斯判處瞎眼流浪的徒刑,然而他的獨生女安蒂岡妮卻在違背國法、服從家法、宗教依靠的倫理觀念鬥爭之間殉身,帶著原罪的伊底帕斯家族最終以死亡作為犧牲或救贖的象徵。
《古正義的糖》小說也是如此,讓最無辜的人代替罪人受過,企至悲劇的哀憐恐懼。過去我處理小說人物的死亡心狠手辣,畢竟那是虛構的人事物,與現實生活毫無干係。只是這次我完全沒有想到,啟發我創作這篇小說的原型人物,一位正值壯年的原住民菁英,也在小說完成之後的第十天,驟然過世。
他是我至親的小舅舅,待我如父如兄如摯友。小時候都是他帶我們去玩,在山上教我們騎黑黑的水牛,把我們丟在牛背上要我們抓住牠的角,我第一次摸水牛,發現水牛皮好硬,上面還長毛。他帶我們在一大坨牛大便裡面用引線放鞭炮,有次風向轉變,牛大便炸開後的味道直撲而來,他說這是毒氣戰。在山上,每次看到姑婆芋都警告我們不能用這種植物擦屁股(那個年代的衛生紙很貴,不是一般人家裡用得起),也會帶我們去尋山泉水源,教我們認識水蛭,撿蝸牛,烤田鼠還有挖竹筍。去溪邊玩泥巴堆城堡和炸彈鵝卵石,看誰把石頭丟得最遠。夏末,我們在河床砂石地撿拾農民遺棄的西瓜,從中間用石頭敲開,直接用手挖果肉吃還把西瓜汁塗滿全身,最後把瓜皮當帽子戴,那時候他就說這是「敷臉」。漫長的暑假,夜晚星星滿天,藉著幾盞煤油燈聚焦,他在橋頭外婆家的露臺舉辦歌唱比賽,邀請左鄰右舍的小孩一起參加。我的熱歌勁舞被他這個唯一的評審形容為「不小心吃到辣椒」,害我滅絕明星夢。
有一次他說要去鳳林鎮看電影,騎著古舊的腳踏車從橋頭出發,看完電影回家已經晚上九點多,在空無人車甚至燈光黯淡的台九線,他一直騎一直用力騎腳踏車。我坐在後座的方形鐵條上抓著他的腰睡著了,手一鬆開,他立刻把我叫醒,要我抓緊別摔下去。這件事一直讓我記到現在,因為我不再看晚場電影,潛意識裡總覺得深夜回家的路好遠好辛苦。
他念軍校時有一年送我鑲金紅色絲絨相簿做生日禮物,在封面寫著「不遭人嫉是庸才,能受天磨方鐵漢」。喂!我是女生ㄟ,這樣祝福生日快樂,又讓我記住一輩子。
故事從很久以前就開始了……我的童年寒暑假都在鄉下度過,起初根本不知道這世界有那麼多分類,包括階級、種族與血統。每一次我帶著歡喜飽滿的心情回到台北與同學鄰居分享部落奇聞,卻讓我的朋友愈來愈少,鄰居愈來愈不喜歡來我家玩,在逐漸覺察的差異中,我也愈來愈傾向疏離。長大以後才發現,原來有一種邊緣人,內心永遠充滿恐懼。他必須先戰勝自己,才能戰勝別人。美國小說家雷克萊爾頓創造半人半神的《波西傑克森》獲得廣大的共鳴,反映出許多人在心理層面投射的混血或雜種基因。在台灣,原住民族經過數百年的異族通婚,早已失去血統的純正,現在只剩下符號,然而大多數人,卻是貼著底層標籤的符號。
我曾經在火車站的便利商店,與一個相似的人擦身而過,他個子不高,身材削瘦挺拔,穿著一套深灰色的西裝,藍格子襯衫,搭配鵝黃幾何圖案的領帶,拖著黑色造型質感高尚的登機箱,也因為有這個登機箱,讓他看起來不像個業務員或是銀行職員,而像個商務人士。
但是當我看到他的眼睛時,頓時明白,我們都是類波西傑克森的邊緣人。
他的眼睛深邃且形狀完美,有著西方人式的雙眼皮,烙印在黝黑的皮膚上,線條俐落的五官,堪稱俊美,卻糾結著眉頭,滲透某種壓抑的神秘。他同樣定定地凝視我,當我朝著他的方向走去,那麼幾秒鐘,我嗅聞到血液裡相同的氣息。
我看過太多這樣長相與我類似的男人、女人。他們都有一雙圓廣明亮的眼睛,高挺的鼻梁,稜角剛毅的臉龐,然而他們大部分不修邊幅,衣著撩亂,以駕駛怪手或砂石車,手工剝除桂竹筍硬殼或摘撿檳榔果實零售維生。
那個男人,已經脫離勞動的宿命。他穿著剪裁合身的西裝,梳起油光立體的髮型,聰明地以摩登的拖車式行李代替遠征的步伐,將現代化質感發揮得淋漓盡致,也使得他粗獷霸氣的臉龐上,浸潤了文明的色彩。他儼然是個文明人,不再以出草的姿態書寫身世,就像我一樣,曾經努力漂白皮膚。這一切一切的修飾與琢磨,就是害怕別人沒來由地直觀論述,在來不及認識我們真誠的靈魂之前,先鄙視我們的出身。
《古正義的糖》就是描寫這樣一群不斷奮鬥、努力活下去、渴望向主流價值靠攏,和所有人一樣追求肯定的人。古正義是我小舅舅的化身,他年長我六歲,更早比我體認到力爭上游的艱辛。
原住民部落的一場民主選舉,讓滿懷抱負的古正義進入監獄。都說好山好水,但賄選消息依然浮動於後山偏鄉,立冬剛過,溪河意外鼓噪,滔滔流水翻滾著謠言,鎮日嘶隆作響。古正義的妻說她親眼看見有人收下敵營賄選的鈔票,拜託熟識朋友探詢,那人答:「我只是拿他的錢,票還是會投給古正義。」
肅颯冬季,埋葬祖靈的聖山,抵擋不住季節的殘酷,政治暴風圈襲捲,吹亂公平與正義。怒吼的空氣撕裂呼嘯,淒厲如女巫嘶語,向黎明之前的陰闇咆哮。是預言或詛咒已經不重要,三天後,古正義以22票的差距落選。
選舉反映出原住民部落的「現代化」,在此之前,古家的親族,以務農和工地粗活維生。唯一可能光宗耀祖的族人之光古正義,卻被指控賄選,三審定讞坐牢兩年出獄之後,何去何從?這一家人,以及族群部落的命運,又會走到哪裡?古正義曾經是家族唯一的希望,他研究所畢業取得特考資格返鄉服務,踏入偏鄉「政壇」,他是原民菁英,熱心基層服務、他可以安穩領取公俸等著退休金,卻在眾人簇擁與使命感催生下投入鄉長選舉。只有六千多人的偏鄉,同樣上演派系鬥爭的政治戲碼,在人情與利益的糾葛恩怨中,古正義三次高票落選。最後一次被敵營羅織賄選汙名,直到他走進監獄的最後一刻,他都堅持自己是清白的。
我最後一次採訪小舅舅時直視他的眼睛,認真詢問:「你到底有沒有賄選?」他完全沒有迴避我的眼神,同樣直視我,堅定地告訴我:「沒有。我相信『正義』這兩個字直到三審定讞那一天。我始終沒有為我沒做的事情認罪。」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我會用小說還你一個公道。」這是我和他面對面說的最後一句話。
小說當然不是復仇的工具,它是人物與故事交錯的錦繡精織。政治愛情畢竟沾了愛情的光,還有那麼一點旖旎懷想。若是將政治與愛情分開來看,那就是一門計算金融的學問,涉及風險分析。凡事一旦涉及風險就會激發保護利益的本能,這利益關乎多數人或少數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既得利益者如何繼續鞏固利益,道德的裂縫就在政治與愛情的對價關係中如瓷器開片迸裂。釉層開片原本是窯燒缺陷,然而汝瓷卻創造出獨一無二的藝術珍品,這似乎也隱喻小說中的真相並不重要,因為,故事才是我們主要的道德老師。
不承認賄選罪的古正義坐牢了,古正義的大哥古清輝,只是開著閒置已久的怪手到河床為孫子們堆疊沙石挖出一個安全戲水的小池塘,也被警察以盜採砂石的罪嫌逮捕。生命的輕薄與操弄,人跟人的命運交錯,在故事之間演化。我們都渴望甜蜜幸福,卻常常分不清楚「糖」與「糖衣」的差別。
我始終認為小說有兩種演技:通俗與精緻。但是它只有一個結果:樂趣。愈悲涼愈要懂得微笑,讓眼淚滴落在揚起的嘴角,哀傷就會轉彎。
因此我必須說一個政治愛情與道德裂縫的故事。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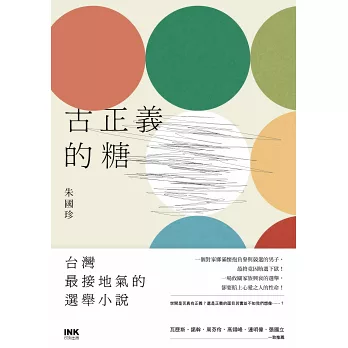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