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1
逃離自己的影子
在詩、劇場與電影的領域裡,如果要舉出三個在我這二十世紀少年心中發生過魔法、施下過咒語的名字的話,應該就會是碧娜‧鮑許、塔可夫斯基與寺山修司。
尤其是在三個領域同時都發散著神奇魅力的寺山修司。
從還沒有解嚴的青春時代,第一次透過地下管道看到他的電影《上海異人娼館》開始,除了輕度駭然於眾多的異色尺度,片尾克勞斯‧金斯基連開三槍之後踹開房門,門外竟是一片洶湧波濤場景,彷彿才更是讓我被命中的開端,那樣自由混雜著考據與不考據、支配與反抗、革命與情慾,都拋擲進了這片超現實主義的大海。我開始追索起這個謎樣的作者,陸續出現了《死在田園》(亦有譯:死者田園祭)《拋掉書本上街去》……所有在台北找得到的影像作品(天曉得比起二十一世紀的此際那是多麼需要一種狂熱的困難),而離這個「據說」也是劇場人的電影導演過世的一九八三年還不到一個世代,但也都遲了些,只剩追趕。而在預期之外一頭栽進劇場的我,雖然不是因為寺山的啟發,卻也私自地、深深將他的劇場傳奇當作目標鎖住,連結了自己猶仍躁動著的劇場青春。
但是,始終太不可解、太難思議到底造就了這些穿走夢與超現實作品的會是怎樣生活著的一個人?
九O年代初期,擺盪在社會化的職場與難以放手的劇場之間的那段日子,神奇地再度遭逢寺山修司,一九九四年初次造訪已經沒有演劇實驗室「天井棧敷」的東京,太晚了嗎?寺山留下什麼在劇場裡呢?正懷疑著,卻碰巧遇上了美輪明宏主演的女裝劇《毛皮瑪麗》,那個充滿惹內風格的寺山的著名劇作,一個年華老去、卻每天還要剃著腿毛的男大姐,雖然不是劇作家親自執導的版本,但寺山的謎樣風格貫穿著……回到台北,剛好那年的金馬影展邀了一組寺山修司風格強烈的實驗短片,這是一組部分要求劇場性現場演出搭配的作品,他生前的特別助理、後來入籍成為義弟的森崎偏陸帶著作品來到台北(也因為他同時是在其中一部叫《Laura》的短片中被包括蘭妖子在內的三名張狂女人剝光衣服施虐、然後抱著衣物狼狽地「逃出」銀幕、奔進電影院現場觀眾席的主角),影展主辦單位讓我協助了諸多現場劇場性演出的工作,甚至,因為演員臨時缺席,我必須替補地走到銀幕後方,在《二頭女》那個現實與影子互相解離的作品裡,成為片尾現場的影子演員之一。
接著進入了自己的中年,接近了寺山修司辭世的四十七歲,更常進出東京,卻好像去一個朋友家、明知他不會在卻也無所謂的自顧連結著一個詩人的記憶。學了一點極其粗淺的日文,透過英文的翻譯與注音,就讀起了他的短歌。很長的日子裡,在終於脫離困難睡眠、從深重夢中回返、開始一日生活的時刻,我像日課般地讀一、兩首他的短歌,也藉此新學幾個日文詞彙,我有限的日文一半是寺山的語言,好像近了一些,但更常重新感到困惑—這些從少年到壯年匯聚起的鬼魅與寂寞意念,又是哪樣的謎般次元才能流淌的聲音?
我一直好奇,但畢竟已經不是一個狂熱的追索者,回頭看他的作品,他的影像是從未世故的青春暴動,劇場則像是必須穿過黑森林才能去到(還不一定找對)的遠方。也深知那與自己的風格有著距離只能保持的神祕美感,看來只剩短歌或詩集,是最長遠而平穩的聯繫了,那種異質的寂寞,即使不同次元仍輕易觸動每個人的寂寞,讓我確定自己對他的一種愛。
於是書寫著一篇想要推薦《我這個謎:寺山修司自傳抄》這本書的文字,竟又深陷某種記憶的迷宮了,但即使仍然是個介於真實與虛構、現實與超現實之間的迷宮,寺山修司這個男人的身世終究層層疊疊、若隱若現了。你會看到《死在田園》《草迷宮》(以及劇場《身毒丸》)裡的母親原型如何還原到真實的成長記憶,又抽長成從沾染口紅的廉價香菸漫散開的迷霧;看到《毛皮瑪麗》還原成一個其實是父親但「扮演」著母親、死去的女人卻露出長滿腿毛的屍體;看到對家的恐懼、憎恨以及相反的渴望,在無法實現的「家」的基礎上,母親,如他所言—已經不是一種人格,而是思鄉的隱喻。那麼,「我們回青森吧。」—寺山先生,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在這樣謎般的自傳迷宮書寫中,把青森當作某種如二頭女般「逃離自己影子」的寂寞血緣隱喻?
而也是透過這一場肉身化的顯影(與二度的虛構),我開始感到有著虧欠的感激,他的放浪形骸、他的天馬行空(甚至他對賽馬的熱衷)。所有寂寞的詩、所有絢麗超現實的影像,其實也是那麼階級、那麼底層的,瞭解了他從來不是一個莫名的虛無者,只是用來革命與對抗的,是一種迷離的存在風格,這讓我感到重新察覺的迫切、以及重新想像寺山修司宇宙的必要。我想到那次與森崎偏陸先生短暫共處的機緣,我問起關於他們的生活,他說他像個弟弟也像個門徒,白天他出去到處玩耍時,中年的寺山辛勤而賣命地在家寫稿,玩夠的森崎深夜回家,就開始替已經累得睡著的寺山進行謄稿的工作。
我們必須感激這樣的靈魂,不管合不合時宜、夠不夠對應當代處境,這就是一個詩人的現實與價值。謝謝你,寺山先生。
劇場導演╱黎煥雄
推薦2
原來已經老了的,是我們
在這本書裡,寺山修司扮演著自己人生的說書人、劇作家、演員、詩歌吟誦者,一如他在真實人生中一樣。
生於一九三五年、卒於一九八三年(四十七歲)的寺山修司,活躍在距今半世紀前的日本,他寫作詩歌散文,創作戲劇並擔任電影導演,評論藝術還評論賽馬,被譽為「日本新浪潮的核心人物」「亞洲前衛藝術的領航員」。他做什麼都出色,行動力十足並勇於嘗試,創立的劇團影響深遠,文集和小說直到今天仍然被重新出版,甚至改編成戲劇。
但上述這一切,對第一次閱讀本書,初次認識寺山修司的讀者來說,都不會知道。讀者將會看到一個文字輕快活潑,身世不可思議地崎嶇,對偏狹的日常細節充滿著迷,說起自己的語氣自嘲,甚至帶點惡作劇氣味的作者。在書中占了甚大篇幅的自傳式隨筆,爬梳童年,整理親情對自己的人格影響,可以說是核心。他曾在小學時為了存錢「改手相」,偷走家裡的掛鐘想拿去賣;他在中學一年級那年,在美空雲雀〈悲傷的口哨〉歌聲裡和母親在車站訣別;他和父親在深夜衝到家門外的草地去「猜火車」的回憶,是僅有的父子連結;他在十歲那年家鄉青森遭受大空襲,在漫天如雨的燒夷彈中東躲西藏,則是地獄般的圖像……
在這些文章背後,我們看不到成長在戰後的日本,父親早逝、母親無法陪在身邊的寺山修司,對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際遇的不滿。寫作這些隨筆的他,約莫三十歲上下,有的甚至才二十多歲,但是那接受了命運,仍從中找到值得玩味的事物和付出熱情的形象,正提供了我們認知書外的他,作為一個跨界藝術家的活力充沛。
這同時,對於母親的惦記和父親的「不在╲無能」,這些在他戲劇中出現的元素,也藉由這些回憶重述,而透露些許線索。
「你今天七歲。已經獨當一面了。把你媽媽的照片和玩具埋了。」
〈啊!雨傘╲引自《鼬鼠》對白〉
被迫離別和被迫長大,是寺山修司在回顧過去的時候,忍不住閃現的意象。離開母親是他的創傷,而(在他的想像中)母親對此亦無奈,無法善待他卻以反面的形式孕育了他,這或許可以被視為「時代」的象徵。反之,父親的淡漠、距離感和早早消逝,則是「歷史的產能」的無力。他厭惡鏡子,認定它帶著讓人溺死的惡意,因為波赫士寫道:「父親和鏡子皆使其宇宙繁殖、擴散」,於是他自認無法成為父親,也確實沒有成為父親。
在這種種總是挫折,卻被輕巧帶過的生命經驗裡,寺山修司示範了萬物皆可為戲,而自己就像在演出自己的人生。據說他曾瀟灑地宣稱:「我的職業就是寺山修司。」將生涯變成一場展演,不啻是面對惡世的豁達良方。
這同時,本書後半收錄了他和藝術家的交遊,以及對詩歌、文學、作者們的分析統評。有時專注在單一段落上,有的則是人物側寫,從中不難看到他和當時西方藝術界的領頭羊的接觸,也佐證了他本身「世界級」的地位。此外,他對賽馬身世的娓娓道來,津津有味的品評,勢必會讓不熟悉此道的讀者眼界╲腦洞大開,為之莞爾。
整本書閱讀下來,如果沒有事前資訊,讀者甚至不會感覺到這是個「上上上一代」人物的自傳隨筆。這樣跨領域、通曉知識、對什麼都好奇的作家,若放在本世紀,將是社群網站上的風雲人物吧。然而那是半個世紀前的殘敗國度,異文化碰撞的被動洪流中,恰巧生成的一朵生命奇葩。寺山修司曾寫道,害怕自己成為「一輩子在玩捉迷藏的鬼」,當他拿下蒙住眼睛的雙手,會發現外界已經過了好幾年。他還真沒有料到:其實是閱讀這本書的我們,會發現自己都老了,而他依然活潑、健在。
影評人‧《釀電影》主編╱張硯拓
推薦3
通往歷史背面的捷徑
記憶實在是非常不可靠的東西。因為在二O一三至二O一七年間連續五年為高雄市電影館策劃日本電影新浪潮導演專題,策劃出版《她殺了時代:重訪日本電影新浪潮》一書,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把大島渚和篠田正浩當成私人電影的啟蒙。這個誤認,直到閱讀《我這個謎:寺山修司自傳抄》一書,召喚出一九九四年金馬影展在大銀幕上參見《死在田園》《上海異人娼館》和實驗短片《蝶服記》《番茄醬皇帝》的震撼印象,才得以糾正過來。
永遠記得克勞斯‧金斯基在《上海異人娼館》裡打開一扇門,卻見一片洶湧汪洋;念念不忘《再見箱舟》村口那個深不見底的黑洞,究竟通往何處;還有《死在田園》裡臉上塗滿白粉的少年與他母親和隔壁鄰居太太的微妙關係……二十五年前我完全沒看懂寺山修司的電影,時至今日我仍然沒有把握能夠完全理解,然而寺山修司的影像畫面早已不動聲色深植在我腦海。
他身兼劇作家、詩人、和歌創作者、演員及電影導演等多重身分,卻說「我的職業就是寺山修司」。他是哲學家,羅織著各樣不斷進行分裂再重組的謎樣場景,這些場景有著為數不少的出口,偏偏一旦走進去就會身陷其中,進退不得。身為他的讀者與觀眾,為了降低闖關難度,必須攜帶這本《我這個謎》充當參考指南。
此書分成三個部分。其一是「自傳抄」,既收錄私密的童年少時記憶又剖析自己和父親母親的關係,他切入的視角非常有趣,由空襲、戰時廣播、美國以至美空雲雀,甚至從父親的嘔吐物著手。其二是「巡迴藝人的紀錄」,表面上寫各種稀奇古怪的遊歷與見聞,實則挖掘個人對於時間的見解,其中一篇〈空氣女的時間誌〉奇趣古怪,文中藉由質疑手錶和時鐘的正當性,做出如果掛鐘是「家」的隱喻、基於時針運行,那麼手錶便是等同從家逃開的浪遊馬戲團,猶如秒針忙不迭地繞行個人內心一周的創意結論。其三「我這個謎」寫寺山修司眼中奇形怪狀的藝術家們,從父親不在身邊的波赫士寫到超現實主義的達利、後現代主義的品瓊,還有新寫實主義起家卻走向不同方向的導演維斯康堤和費里尼等等。
寺山修司因為看了同樣有嚴重戀母情結的超現實主義名導亞歷山卓‧尤杜洛斯基的《鼴鼠》而成為雨傘控。他認為雨傘不只是防雨工具,也可以變成見證兩人存在的屋頂。《草迷宮》和《再見箱舟》都有傘,豈只是傘,在寺山修司的謎樣場景裡頭,充斥形形色色令人眼花撩亂的鏡象和符號,稍一閃神就會淹沒其中。
因為錯認《死在田園》是他的自傳,便把此片和費里尼的《阿瑪柯德》連結起來,以為這是他之所以被稱為「東方費里尼」的原因。直到讀了〈《死在田園》手稿〉一文,才知他所寫的母子關係其實出自捏造—那是希望發生的,而非實際上發生過的事。創作之於寺山修司,也許更為重要的在於,針對「過去」進行創意改寫。《死在田園》之於現實,是另條平行線;然後《我這個謎》這本書之於電影《死在田園》,又是另道軸線,至於與寺山修司經歷的真實相交與否,根本沒那麼重要。
寺山修司的電影經常攸關時間、記憶與歷史,不過他在意的不是教條或數據堆砌出來的系統性圖表,而是更具有溫度的靈魂告白。尋求意義的存在本身,是更接近詩人的工作。發生的成為歷史,沒有發生的或者沒有被記載下來的,則是歷史的背面。寺山修司終其一生用創作去探究歷史的背面,《我這個謎》此書則是長驅直入這個由各項「背面」層層交疊起來的影像迷宮,最有效率的一條捷徑。
影評人╱鄭秉泓
推薦4
面對世界的老去,為何現代年輕人需要閱讀「寺山修司」?
如同太宰治一樣,寺山修司的作品始終都有種少年感的靈魂,來對抗不動如山且無法扳倒的大人世界。
在台灣,人們熟知太宰治,他不惜以生命來反諷陳規。但寺山修司則是以活著來百鍊成鋼,他的詩歌俳句、評論、劇本與所導演的作品,曾被視為其藝術成就可比擬義大利電影大導演帕索里尼(《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奇才。這個生於日本二戰投降前的人,童年目睹了敗戰之際,日本國內人心的浮動與尊嚴喪失,因此他的筆下文字真的如帕索里尼的作品般是開了滿滿的惡之華。
不同的是寺山修司筆觸承襲了日本古典的冷調優美,讓他所陳述的殘酷事實,都開出敗壞中重生的異樣花朵來,散發猩紅點點的文字情調,簡直如他所說他童年時在寺院看過的《地獄圖》。
但我們現在為何提到這位昭和時代詩人與劇場鬼才?因為他的作品無比的「青春」,他那種初識世上的眼神,看待這世界是中性的、無偏斜的,妖豔且滿是赤裸的慾望,如同她身為養女的母親受人作踐的玉體橫陳,如他父親終究無法成為自己的男性悲劇,他筆下敗戰前與戰後發展快速的日本,都呈現一種慾望的奔流,讓你知道為何莎翁名著《馬克白》會寫出「美就是醜,醜就是美」的互為表裡。因此當年寺山修司開創的舞台劇團「天井棧敷」,震驚了當時封閉的日本,以前衛藝術揭開了日本的假面,開創了影視感官迸發的先驅。
二○一七年日本上映了一部電影《啊,荒野》(這是寺山修司的唯一長篇青春小說),海報上的標語「擊碎孤獨」,並反問著觀眾:「二○二一年,人類依舊孤獨嗎?」這齣劇的兩個年輕靈魂漂流在新宿熱鬧的「荒野」,無歸屬地找尋一個渺小的座標,打動了許多年輕人。事實上,從他逝世三十週年的二○一三起,他所寫的歌詞與俳句,再度被掛在淘兒唱片行門口,這昭和年代的反叛青年,讓日本再度興起了「寺山熱」,點醒了寺山修司作品為何需要被現代的年輕人看見,因為他的文學描寫的這個世上並不是高牆與雞蛋的兩極,而是腐朽與青春的對照。
這世上的今日無論極權復甦還是財富的分配都老朽得如同被過去的鬼魅附身,而現世拋售的「青春」都是樣板而無靈魂的傾銷,如何讓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能真正感受到「青春」的真義,才是不分世代靈魂衰老的救援與希望。
在寺山自傳《我這個謎》裡就是呈現這樣的勃勃生機,即使他描寫的世界一如我們所知的麻痺不仁。戰敗後的日本如同世界的盡頭,人如走獸的命運,竟是他的親人的遭遇,但寺山的筆與眼仍雪亮,文學在他這本傳記中有了起身的高度,如狩獵者看著外界昏昧嗜血的老獸,準備向他撲襲而來,這才是年輕人還沒被世道擄獲前的神魂所在。
這是無關於年齡與世代,而是面對這老去的世界,我們眼中與心中是否仍有當初寺山修司筆下翻天倒海的焰火,讀他的作品,才能召喚出點「青春」的血氣,這是他為何被讚譽為「語言的鍊金術師」。《我這個謎》他從自己被虛構的出生地—火車開始描寫,帶出他之後深感漂浮的人生,身處亂世如觀望周遭的馬戲團。書中無論是空襲後那河裡浮沉的屍體、日本人多怕美軍的接管;將他們形容為巨大的陽具、空中飛人的接拋自身,如此大的信任禁得起一個念頭的磨損嗎?他母親改了三個名字,也改不掉那必須以身體換取一點安全的際遇、那做刑警的父親,每次喝醉嘔吐都將穢物吐在軌道上,感受那遠離的車輪帶走他的不甘去遠方。
他形容家裡有「綻放螢火的妖光」,那是來自於父母對自己運命的「憎恨」,他更點出人的臉其實是不斷的「列印」。他如指揮「馬戲團」般將此種種化為絢爛,那些不堪與底層的無意識的過活,都被他寫出詩情的樣貌,如他所說,歷史從不是一門自然科學,歷史在讀取其中的靈魂。
我彷彿初遇見一個孩子,他看這世界仍是新鮮的,殘酷無妨、挫折無關,他用他的方式這樣愛著人細碎的歹念,日本俳句之精神,不畏世俗,自此才懂。
作家╱馬欣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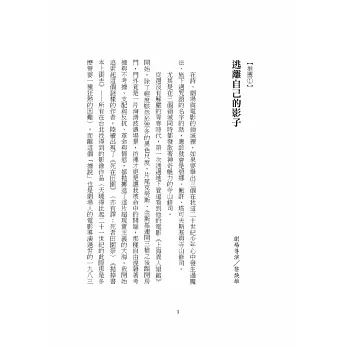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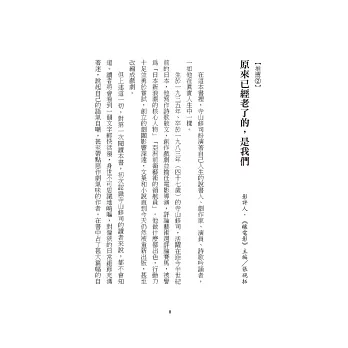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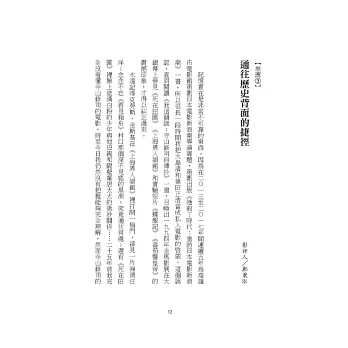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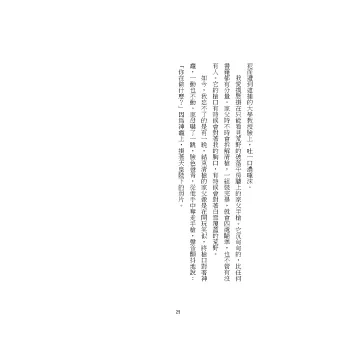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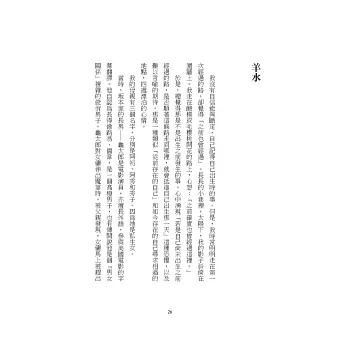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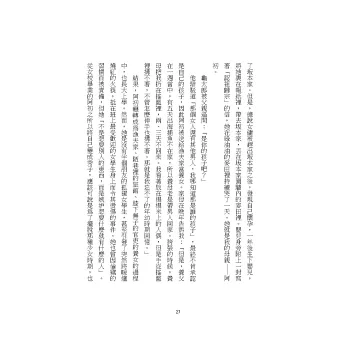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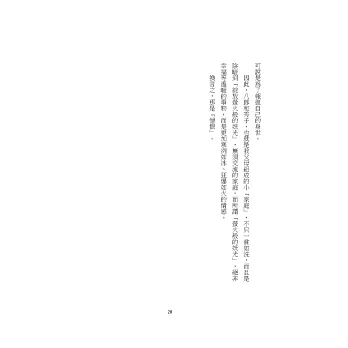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