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論述的第一道聲音
南方朔
過了半個多世紀,這本曾經震驚了黑人世界與歐美知識份子的經典名著《黑皮膚,白面具》,終於有了中譯本。這本書的作者法農(Frantz Fanon)曾被法國名作家高德(David Caute)稱為「被殖民化的曠野之聲」。他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傳奇悲劇英雄之一,也是我最崇拜的偶像裡的一個。在《黑皮膚,白面具》翻譯本出版的此刻,我樂於將此書此人向朋友們介紹,以表達對法農的崇敬。
在二十世紀,有三大悲劇反抗英雄:黑人世界,是法農;在拉丁美洲,是格瓦拉;阿拉伯或是更廣泛的伊斯蘭世界,則是最近剛剛去世的阿拉法特。這三位人中豪傑和他們的族人,都受盡舊新殖民帝國主義的荼毒,於是他們奮然而起,要帶著族人衝出一片新天。但因為舊新殖民帝國主義是如此的強大綿密,因而他們的反抗之路都走得悲愴慘烈,甚至連他們自己也都在屈辱中仆倒在地。但他們的死並非結束,而是化為一種新的召喚,讓更多人接續著他們的足跡,繼續往前行。
在這三大悲劇英雄裡,出現得最早、理論水準最高、反抗經驗最痛苦的,毫無疑問要以法農居首,他是一則黑人世界的史詩式英雄傳奇。
法農的一生有如狂飆,捲動了整個時代。他出生於法屬西印度群島的馬提尼克島,在那裡唸小學,並往法國唸中學。一九四四年,法國面臨納粹的侵略和壓迫,他志願入伍,參加法國軍隊在歐洲服役。戰後復員,他前往里昂大學攻讀醫學和心理治療,並同時編輯黑人學生報「多姆報」(Tom-Tom)。一九五一年醫學院畢業後,他即成為專業精神科醫師。在他唸大學的時候,即痛感於黑人的被迫害與非人化,而開始關注黑人存在情境問題。此外,他也和當時的思想家沙特頻繁往來。沙特的情人西蒙.波娃就如此回憶法農 :「他和沙特一直談到凌晨兩點。最後,我很有禮貌地打斷他們的談話。我說沙特需要睡眠。法農是個憤怒的青年,這個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派,就像古巴人一樣,從來沒有一天睡超過四個鐘頭。」
一九五二年,法農奠定歷史地位的經典之作《黑皮膚,白面具》出版。由這本書的敘述,我們可看到他對黑人處境問題,具有一種存在精神分析的超絕能力。他把西方以「個體發生學」為基礎的精神分析作了大改變,而將它轉往政治、經濟、文化、價值和語言支配這種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的層次。除了存在精神分析的基礎在他手上被改變了之外,他也從沙特的《存在與空無》(L'?tre et le neant,英譯名:Being and Nothingness)裡借到了「自我存在」(being-in-itself)和「自為存在」(being-for-itself),以及「他者」(the Others)等核心概念。由於在方法論上的突破,使得他在觀察黑人問題時,遂能將經驗整合到一個更大的解釋架構下。他指出:「白人文明、歐洲文化,在黑人身上強加了一種存在的偏差。......黑人心靈,經常是白人的建構。」
因此,《黑皮膚,白面具》乃是一本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它推翻了殖民時代長期以來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白-黑」、「優-劣」的刻板觀點,而將它拉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平面上,而將那種宰制關係做了深層的文化與價值觀照。法農的這本著作,等於讓黑人和白人全都重新洗了一次眼睛,也等於是替「後殖民論述」發出了第一個聲音,在近代思想史上有著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後來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就從這本著作裡得到了許多啟發。黑人民權領袖如卡麥可(Stokely Carmichael),以及克利佛(Eldridge Cleaver)等人,因而都尊稱法農為「我們的兄弟」。
出版《黑皮膚,白面具》的第二年,即一九五三年,法農和一個白人女子結婚,而後到阿爾及利亞一所醫院擔任精神科主任。在這裡,法農由理論實踐轉往行動實踐,並開始了他生命裡最壯闊、痛苦、英勇但也悲慘的新頁。
阿爾及利亞於一八三○年淪為法國殖民地。法國對這個地區推行的乃是「徙置式殖民政策」。大量法國人自本土遷來,佔領了平原地帶最好的三百萬畝農田,統治機器全由白人掌控,只有極少數的阿爾及利亞人擔任買辦報的工作。在非洲,像阿爾及利亞這樣被深入殖民化的國家並不多見。也使得阿爾及利亞的反殖民獨立戰爭遭遇到最大的抵抗。非洲有許多國家,由於殖民模式不同、殖民化程度較弱,可以不經戰鬥或只要有輕微的戰鬥,即可達到獨立的目標,但阿爾及利亞為「徙置式殖民」程度最深,設若阿爾及利亞獨立,法國所受損失也最大,使得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兼具了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雙重性。這乃是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要血戰七年,終於在一九六二年簽訂「艾維安協議」,問題始告解決的原因。
一九五四年阿爾及利亞獨立革命剛開始,法國總理即決定全面鎮壓。一九五七年左翼總理莫耶(Guy Mollet)上台,壓制手段更趨嚴厲,於是阿爾及立亞總督拉可士(Resident Minister Lacoste)將軍警權交給法國強人馬蘇將軍(General Massu)協同作戰。他們堅壁清野、大舉掃蕩,並不斷增強刑求恐嚇;最酷虐的乃是為了壓制游擊隊,在一九五九年將兩百萬阿爾及利亞人驅逐出村莊,俾使游擊隊失去落腳的地點,以及號召人民的基礎。
也正因此,阿爾及利亞的反殖民戰爭一開始,法農即加入支持獨立戰爭這個陣營。一九五六年,他參加在巴黎召開的「第一屆黑人作家與藝術家會議」,大力抨擊殖民主義。同年,他即正式獻身獨立戰爭,擔任「阿爾及利亞國家解放陣線」的機關報總編輯,成了獨立戰爭的革命宣傳家。
一九五九年乃是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黑暗期。法國的軍隊為了切斷阿爾及利亞游擊隊的外援通道,特地用大軍封鎖了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突尼西亞的邊界,並在邊界一帶廣佈地雷。當時法農奉命突破封鎖線,但卻不慎在阿摩邊界碰觸到地雷,脊椎受裂傷,下肢癱瘓,膀胱擴約肌也受傷。而後他前往羅馬治療,但在羅馬機場就被法國特務丟擲炸彈,他幸以身免,但卻有兩個路人不幸被炸死。當他進了醫院,消息外洩,暴徒夜晚又來暗殺,幸而他已悄悄換了病房,再次逃過大劫。由這一段被沿途追殺的故事,當時法農處境的險惡與悽厲已可概見。
養傷一段時間後,法農重返阿爾及利亞,仍為突破封鎖線而在南撒哈拉一帶奔走。一九六○年,他被叛軍的臨時政府任命為駐迦納大使,但就在此時,他發現自己罹患白血病。他說:「我知道自己大概還有三、四年好活,我必須更快地去做事了。」一九六一年,他最先赴莫斯科求診,而後又轉往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但為時已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他病逝美國,遺骸被接回阿爾及利亞,以戰士的禮儀葬於軍人公墓。他死亡的那天早晨曾與妻兒談話,他說:「昨天晚上,他們要把我放到洗衣機裡去洗。」由這句話可看出黑與白的膚色問題對他造成了何等巨大的傷害!就在死亡之前,他那本更淒厲的經典著作《受詛咒的大地》(Les Damn?s de la Terre)出版。那是本以描寫獨立戰爭為主、穿插著他哲學見解的著作,文字飛揚、動人心魄,被許多人認為是二十世紀「受創傷者」的最沉重告白。
法農只活了三十六歲,就帶著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但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留下的《黑皮膚,白面具》和《受詛咒的大地》,卻成了二十世紀的重要經典,召喚著世人繼續努力。他曾主張白人要以歉疚之心,自己先「脫殖民化」,幫助黑人展開心靈和國家重建。他的這個想法,後來成了全球的新標誌--它就是一隻黑手和一隻白手相互緊握的那個圖案。這是個人們常看到的圖案造型,很少人知道它是出於法農的思想。
法農是二十世紀重要的原創型人物,今天,我們重讀他這本已有五十二年歷史的《黑皮膚,白面具》,仍能感受得到他那精湛的思維,以及銳利的解析能力。當我們在談論「後殖民論述」時,法農這個名字絕對不容或忘。他這個人既是思想家,同時更是行動家的醫生,慷慨悲歌,不正值得我們去敬仰和效法嗎?而由法農那,或許我們也應該對另外兩位傳奇悲劇英雄格瓦拉和阿拉法特,也寄與同樣的崇敬吧!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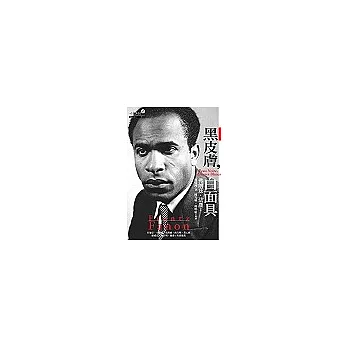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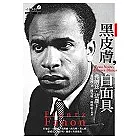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