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芳名周四‧夏的女子
「……特殊勤務網」是為了處理太過出奇或太過專門,一般執法機關無力應付的治安職責而設立的。此網總共有三十個部門,從較為尋常的「鄰里紛爭部」(特勤三○)往上到「文學偵查部」(特勤二七)和「藝術犯罪部」(特勤二四)等等。所有特勤二○以上的單位都是機密,然而大家都知道「時空特警部」是特勤十二,「反恐部」則是特勤九。謠傳特勤一就是監督特殊勤務網本身的部門。至於其他單位負責什麼就只有天曉得了。唯一確知的是探員大多為退伍軍人或是前任警員,而且都有輕微的心理不平衡。「如果你想當特勤探員,」俗諺如是說,「只要舉止古怪就成了……」——墨方.佛洛斯《特殊勤務網簡史》
我父親有張能讓時鐘靜止的臉。不是說他醜或什麼的;時空特警用這句話來形容能將時間減緩成極慢的涓滴細流的人。爸以前是時空特警部的上校,對工作內容口風很緊。事實上他的口風緊到了有天早上他那些維護時序的同事來突襲我們家,亮出無限「逮捕正法令」,質問他在哪個時空哪個地點時,我們才知道他變節了。
從那時起爸就一直在逃;其後,在他不時造訪的時候,我們得知他認為整個部門在「道德和歷史上腐敗」,並選擇孤軍對抗官僚的「特殊時空穩定局」。我不懂他是什麼意思,到現在仍舊不懂;我只希望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且不要因此受傷就好。他能讓時間停止的技能得來不易,而且無法還原,現在他成了時流之中的孤寂巡遊者,不歸屬於單一時代,而屬於所有時代,除了片段的時空之外,無處為家。
我不是時空特警部的成員。我從來不想加入。無論怎麼看那份差事都不好玩,雖然薪水很高,當局還以無與倫比的退休制度自豪:去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單程票一張。但那不適合我。我是特勤二七所謂的「一級探員」。
特勤二七是特殊勤務網中的文學偵查部,總部位於倫敦。我的職位實際上遠不如頭銜響亮。一九八○年代起,大型犯罪集團插手利潤豐厚的文學市場,我們要做的事多,可用的經費卻少。我歸區域主管鮑斯威管轄,他是個矮小肥胖的傢伙,看起來像是長了手腳的麵粉袋。他以工作維生,文字是他的生命和摯愛——他在追蹤偽造的柯立芝或是費爾汀的假貨時最為快樂。我們在鮑斯威的指揮下破獲了盜取販售初版山謬.約翰生的集團;還有一次我們揭穿了試圖將一份可信度低到荒謬的玩意蒙混為莎翁失落名作《卡戴尼歐》的嘗試。這些時候很有趣,但卻只是特勤二七平淡乏味的日常汪洋中微小的興奮孤島: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黑市販子、著作權侵害和詐欺。
我加入特勤二七隸屬鮑斯威手下已經七年,和我的寵物匹克威克一起住在梅達威爾的公寓裡。匹克威克是一隻基因重建的渡渡鳥,曾經有一陣子逆轉滅絕大為風行,你可以輕易買到家用複製組自己動手。我很想——不,我非常迫切地想離開文學偵查部,但調職乃前所未聞,昇遷更是天方夜譚。我唯一能成為探長的方法就是上級昇官或離開。但這種事從未發生;透納探長嫁得金龜婿光榮離職的希望維持原樣——祇是希望而已——因為金龜婿到頭來總成了說謊大師、酗酒醉漢或是已婚先生。
正如先前所說的,我父親有張能讓時鐘靜止的臉孔;某個春日早晨,我正在離辦公室不遠的一間小咖啡廳吃早餐的時候,就發生了這種事。世界閃爍、震顫、然後靜止了。咖啡廳的老闆話說到一半嘎然而止,電視影像也瞬間定格。窗外的鳥兒動也不動地懸浮在空中。車輛和電車停在街上,正發生車禍的單車手頓在半空,離堅硬的柏油路面只有兩呎距離,恐懼的神情凍結在臉上。聲音也靜止了,被一種單調的嗡嗡聲取代,全世界此刻的噪音都無限地停頓在同一音調和音量上。
「我的漂亮女兒好不好啊?」
我轉過身。父親坐在桌前,他站起來親切地擁抱我。
「很好,」我回道,緊緊回擁他。「我最喜歡的爸爸好嗎?」
「沒有怨言。時間是最佳良醫。」
我瞪著他好一會兒。
「你知道嗎,」我喃喃道,「我覺得每次看見你你都變年輕了。」
「是啊。妳要讓我抱孫子了嗎?」
「憑我現在這副德性?永遠沒指望。」
父親微微一笑,揚起一邊眉毛。
「我暫且還不會這麼說呢。」
他遞給我一個伍爾沃滋百貨的袋子。
「我不久前去過一九七八年,」他說。「替妳買了這個。」
他給我一張披頭四的單曲。我沒聽過這首歌。
「他們不是在一九七○年就解散了嗎?」
「不是一直都這樣的。一切都好嗎?」
「老樣子。辨證真偽、著作權、盜竊事件——」
「——同樣的爛玩意?」
「嗯。」我點頭。「同樣的爛玩意。你怎麼來這兒了?」
「我去了妳的時間未來三星期後看了妳媽,」他回答,查看手腕上那只大時空錶。「就是為了——嗯哼——那個原因嘛。她會在一星期以後把臥室漆成淡紫色——妳去跟她說說,叫她不要好不好?顏色跟窗簾不搭。」
「她還好嗎?」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
「永遠容光煥發。麥考夫特和波莉也希望有人記得他們。」
那是我叔叔和嬸嬸;雖然這兩人瘋狂透頂,我還是深愛他們。我最感遺憾的是太少看見麥考夫特。我已經有好多年沒有回老家跟親人見面了。
「妳媽和我都認為妳該回家一下。她覺得妳工作太認真了。」
「這話從你嘴裡說出來,實在太扯了,爸。」
「哎喲,一針見血。妳的歷史學得怎樣?」
「還不壞。」
「妳知道威靈頓公爵怎麼死的嗎?」
「當然,」我回答,「他在滑鐵盧之役一開始的時候被一個法國狙擊手打死了。為什麼問?」
「喔,沒什麼,」父親裝出無辜的樣子喃喃道,在小筆記本上寫字。他停頓了一會兒。
「所以拿破崙贏了滑鐵盧之役,是吧?」他非常專注地緩緩問道。
「當然沒有,」我回答,「布呂歇爾元帥適時干預,扭轉了局勢。」
我瞇起眼睛。
「爸,這是最基本的歷史。你在打什麼主意?」
「妳不覺得這有點碰巧嗎?」
「什麼碰巧?」
「納爾遜和威靈頓,兩位偉大的英國國家英雄,都在他們一生中最重要、最具決定性的戰役裡早早被人打死。」
「你在暗示什麼?」
「法國修正主義者可能有干預。」
「但這並不影響兩場戰役的結果,」我堅持。「兩場我們都贏了!」
「我沒說他們有本事。」
「這太荒謬了!」我嗤之以鼻。「我猜你以為同一批修正主義者在一○六六年殺掉了哈洛德王,以利於諾曼人入侵呢!」
但爸並沒笑。他驚訝地回問:
「哈洛德?被殺了?怎麼死的?」
「被箭射中,爸。正中眼睛。」
「英方還是法方?」
「歷史沒說,」我回答,一連串古怪的問題惹惱了我。
「你說射中眼睛嗎——?時序確已脫軌。」他喃喃道,又記了一筆。
「什麼脫軌了?」我沒聽清楚。
「沒事,沒事。不幸匡正其誤乃吾之天職——」
「《哈姆雷特》?」我認出他引用了莎士比亞。
他無視我,寫完他要寫的東西,啪地一聲闔上筆記本,然後心不在焉地用指尖按摩著太陽穴。世界往前輕移了一秒,在他按摩太陽穴的時候重新定住了。他緊張地舉目四顧。
「他們找到我了。謝謝妳幫忙,小甜豆。見到妳媽的時候告訴她,她讓生命的火炬更為閃亮——而且別忘了試著叫她不要重漆臥室。」
「除了淡紫色都好,對吧?」
「沒錯。」
他對我微笑,輕撫我的臉。我感覺眼眶濕潤;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實在太短暫了。他察覺我的哀傷,臉上的微笑是所有小孩都希望父親給他們的那種笑容。然後他說:
「我投入過去,至特勤十二可見之處——」
他停頓下來,讓我接腔,這是小時候爸教我唱的一首時空特警隊的隊歌。
「——目睹世界願景,和所有可行之路!」
然後他消失了。世界震顫了一下,時鐘再度走動。酒保說完了一句話,鳥兒繼續歸巢,電視畫面播出「微笑漢堡」令人作嘔的廣告,街頭的單車手砰地一聲撞在柏油路面上。
一切都照常運行。除了我之外沒有人看見爸來去。
我點了一份蟹肉三明治,心不在焉地嚼著,不時啜飲似乎要花一輩子才會涼一點的摩卡咖啡。顧客不多,老闆史丹佛忙著洗杯子。我放下報紙望向電視,螢幕上出現「蛤蟆新聞」的台徽。
「蛤蟆新聞」是歐洲最大的新聞網。幕後經營者是哥利亞巨人集團,這個二十四小時的新聞台隨時都有最新報導,公營的媒體根本無從望其項背。哥利亞讓這個新聞網財源無缺地穩定經營,但同時也帶著某種啟人疑竇的氛圍。沒人喜歡這個集團對政府的致命掌控,而蛤蟆新聞網雖然一再否認母公司主導其政策,卻仍舊招致接連不斷的批評。
「這裡是,」播音員在悠揚的樂聲中宏亮地說道,「蛤蟆新聞網。蛤蟆給您全球視野、最新消息、即時新聞!」
燈光亮起,打在對著鏡頭微笑的女主播身上。
「這是一九八五年五月六號星期一的午間新聞。我是雅莉珊卓.貝爾費吉。克里米亞半島,」她報導,「本周再度成為焦點。聯合國通過了第一七二九六號決議案,堅持英國和俄羅斯帝國政府重開克里米亞主權的協商。克里米亞戰爭邁入第一百三十一年,國內外的壓力團體都極力促進以和平方式終結敵對。」
我閉上眼睛,暗自呻吟。一九七三年我在那兒為國盡忠,親眼見識了虛勢榮華之下的戰爭真相。熾熱、嚴寒、恐懼、死亡。主播繼續說著,聲音裡帶著極端愛國主義的氣息。
「英國部隊在一九七五年將半島上最後一個據點的俄軍逐出時,被視為極度不利情勢中的一大勝利。然而從那時起戰局便呈現膠著狀態,上個星期,戈登.賈勞力士爵士在特拉法加廣場的反戰示威中,總結了全國人民的感受。」
畫面轉變為倫敦市中心的大型和平示威影片。賈勞力士站在台上,對著一大叢雜亂的麥克風發表演說。
「一八五四年從藉口要遏止俄羅斯擴張主義而開始的行動,」議員說道,「經過這麼多年來已然傾頹成了只是為了維持國家面子的……」
但我並沒在聽。這一套我以前已經聽過幾兆次了。我又啜了一口咖啡,覺得頭皮因汗水發癢。電視畫面配著賈勞力士的話聲播放著半島的紀錄片:塞巴斯特堡,一個戒備森嚴的英國軍事要塞城鎮,當地的建築和歷史傳承已然蕩然無存。我只要看見這種影片,腦中便充滿了煙硝味和彈藥爆炸的聲音。我不由自主地撫摸我光榮參戰留下的唯一記號——下巴上的一道小傷疤。其他人可沒這麼走運。一切都未改變。戰事依舊延宕不決。
「周四,那全是屁話。」近處一個粗嘎的聲音說。
那是咖啡廳的老闆史丹佛。他跟我一樣是克里米亞戰爭的退伍軍人,但從軍的時間比我早。他跟我不一樣,失去的不只是純真和幾個好朋友;他靠著兩條鐵腿蹣跚走動,身上殘留的彈片足以做出半打燉豆罐頭來。
「克里米亞跟聯合國根本一點屁關係也沒有。」
雖然我們觀點相反,他還是喜歡跟我討論克里米亞問題。沒有其他人真的想這麼做。參與和威爾斯持續爭戰的軍人較受人敬重;打克里米亞戰爭的傢伙通常都把制服留在衣櫃裡。
「我想是吧,」我不置可否,望著窗外街角一個背誦幾句朗法羅以乞討幾文錢的克里米亞榮民。
「要是我們現在交還克里米亞,那些人不都白死了嗎
?!」史丹佛粗暴地說。「我們從一八五四年就在那裡了。那是屬於我們的。你等於是說我們應該把懷特島還給法國人。」
「我們的確把懷特島還給法國人了,」我耐心地回道;史丹佛對時事的了解大致侷限於甲組槌球聯賽和女星蘿拉.范福的愛情生活而已。
「喔對,」他喃喃道,眉頭糾結在一起。「我們還了,是不是?好吧,我們不該還的。而且聯合國自以為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但若是可以停止殺戮的話,我會支持他們的,史丹。」
酒保悲哀地搖搖頭,賈勞力士替演說做結。
「……沙皇羅曼諾夫.亞曆希四世絕對擁有半島的主權,這點無庸置疑,我期望我們從這虛擲無數人命和資源的無謂戰爭中撤軍的那天到來。」
畫面回到蛤蟆新聞女主播,她持續播報下一條新聞——政府打算把乳酪稅調高到百分之八十三,這個不得人心的政策毫無疑問地將會讓更多激進分子包圍乳酪店。
「只要俄國佬撤軍,戰爭明天就可以結束了!」史丹佛殺氣騰騰地說。
這根本不成論證,他和我都心知肚明。無論哪方贏了,半島都已然沒有任何值得擁有的東西。唯一一塊沒被砲彈轟爛的土地上滿是地雷。無論從歷史還是從道德上來看,克里米亞都屬於俄羅斯帝國;歸根究柢就這麼回事。
接下來的新聞是威爾斯社會主義共和國邊界的紛爭;沒人受傷,只在海伊附近的瓦伊河段互開了幾槍。一向難以自抑的年輕終生總統歐文.格林杜爾一貫地指責英國想要統一不列顛的帝國主義野心;而國會也同樣一貫地對此事件連聲明都不發表一句。新聞繼續播放,但我並沒注意在看。一座新的核電廠在鄧傑內斯啟用,首相去主持了啟用典禮。他在此起彼落的閃光燈下盡責地露齒而笑。我回頭看報紙,有一篇關於渡渡鳥數目暴增的報導,國會打算通過廢除牠們是瀕危動物身分的條款。但我無法專心。我腦中滿是克里米亞戰爭及其不愉快的回憶。幸好此時呼叫器響了,讓我得以回到現實。我在櫃檯上丟下幾張鈔票,衝出門口,「蛤蟆新聞」女主播正嚴肅地報導一位年輕超現實主義者遇害的新聞——他被一幫法國印象派激進分支的傢伙用刀刺死。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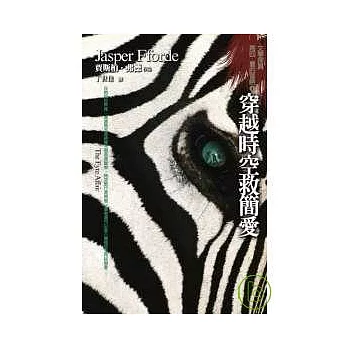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