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滄海
我是父親的獨生子,父子倆相距四十年。在我記憶的童年時期,我經常纏著家父在夜間帶我外出,無論颳風下雨。當時我們島上還沒有電,最多的就是興隆雜貨店的煤油燈,看看煤油燈,看看雜貨店裡的雜貨,看看那些國共戰爭、二戰時期的老兵在店內喝高粱消磨人生的歲月,常常問著自己,說:「他們是哪裡來的人?」
颳著風,下著雨是我島上秋季的氣候,父親裸著上身,而我是全裸的被他揹起,離開雜貨店煤油燈照明的範圍之後,那真是一片漆黑的世界,父親的雙腳走在部落的石子路上,他的腳掌似是走在平面的水泥路上,我形容父祖輩們,那個世代的人的腳掌是靠著體內電波走路的人,父親邊走邊跟我說達悟人的童話故事,起來的時候已是天亮了。
天氣良好的夜色,月亮照明部落的空景,孩子們在海邊玩著自創的遊戲,流了汗就衝入海裡泡。彼時,部落的男人經常聚集在最靠近海邊的家人庭院說著古老的故事,說著男人在海上的故事,一回寧靜的聽著長老的故事劇情,一回兒眾人合聲唱著古老的歌,而我就沉睡在父親的胸膛,直到我會跑步,不被颱風浪趕上之後,我開始坐在父親與小叔公身邊繼續聽屬於這個島嶼民族的神話故事。
島上墨之色的夜躺在涼台上,從母親哪兒聽到關於天空的眼睛的故事,聽見關於pina langalangaw(註1)(仙女),也聽見達悟人與魔鬼戰爭的故事,那些記憶裡的故事,在我進入了漢人的學校教育之後,老師所有的故事跟我聽的完全不一樣,於是何者是正確的,何者是錯誤的,在我的腦海開始被攪混。
一九七○年小學畢業時,老師告訴我說:「將來當個老師好好教育你們蘭嶼這些『野蠻』的小孩成為『文明人』。」
一九七三年台東中學畢業,我寄宿的神父告訴我說︰「考不上大學就去輔仁大學念西方神學,將來當神父馴化你們蘭嶼那些不認識上帝的『野蠻』人成為『文明人』。」
在我的記憶裡,他們都是外國人,都很希望我們變成他們想要形塑的「人樣」。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我與表弟都有同年同月出生的兩個妹妹,父母親上山,或是父親出海抓魚的時候,我們經常在一起玩耍,一起照顧妹妹。秋天的太陽,秋天的灘頭海浪梳理我們的童年記憶;我與表弟在微浪波及的砂粒上築起小海池,讓四個小妹妹在池內泡海水,彼時我們就拿著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發放給我們的蚊帳游泳捕魚,那個時候我們是八歲的小男孩,可是早已有了如何區分男性吃的魚(註2)與女性吃的魚(註3)的基礎常識,也至少知道十多種淺海魚類的名稱,更妙的是,妹妹她們的年紀,在傳統上是最適合吃kuvahan魚的年紀。因此我和表弟用肉眼(沒有水鏡)潛水,就只有網kuvahan,其他的魚類就放回大海。
回到部落的家,我們也知道父母親分類沸煮男性、女性魚類的鍋,以及木盤,那時妹妹她們分別是五歲,三歲,妹妹她們吃得非常的高興。不過我的親妹妹和她同年的表妹,在那年的冬天也同月的辭世。父親土葬二妹的同時,母親帶我與大妹在河溪清洗肉身時,對我們說:「願你們兄妹的靈魂兇悍(「兇悍」的意思是,希望我們的肉體能夠抵抗疾病,適應自然節氣),小妹的靈魂是被天上的Pina Langalangaw(仙女)招回的。」
彼時我性格的「兇悍」是呼應自然環境的鼻息,融入在父祖輩們人格化環境生態的信仰裡,做個卑微的自然主義者,而仙女就生活在某個星球裡,成為我挫敗時告解的對象(母親告訴我的)。
老師、神父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不約而同的,帶有濃厚的殖民者心態,說我民族是「野蠻」,要我將來走上符合他們價值觀的職業,形塑我由「野蠻」轉向「文明」這個意義好像我的民族真的是「野蠻」。然是我體內的血脈,腦紋似乎對這樣的文明職業不是非常的有興趣,老師與神父最後對我偏離他們形塑的航道的表現,當然是非常的失望,當然我靠自己完成大學課程也令我的父母親非常的失望,畢竟同時符合父母原初的「野蠻」條件,老師,神父進化的「文明」標準是困難的。這是兩條平行線,兩個世界的人的想法,我被夾在中間,我認為他們都是正確的。我的經驗解釋是,這是人類與自然環境的親疏關係;愈接近自然環境生活的人稱之「野蠻」(跟生態環境情感濃厚)愈遠離自然環境生活的人稱之「文明」(用自然科學解釋生態,沒有情感),信奉西方宗教的一神論者是「文明」(outsiders),泛靈信仰的自然主義者是「野蠻」(insiders)。
我無法精確的選擇,無法判斷何者是正確,何者是錯誤。最後在飛魚季節每天選擇夜間划著自製的拼板船出海捕飛魚,給自己尋找一個寧靜的空間,在海上欣賞天空的眼睛,繼續的盯住那顆既不明亮也不昏暗的nuzai星(達悟人航海的星座),天上仙女為我亡靈選擇的星座。其次,用達悟族的視野思考月亮的出沒,思考她的盈虧為何不像太陽那樣永遠從東邊上升,永遠是飽滿的而刺眼的。假如我可以選擇的話,我選擇月亮的盈虧過生活,上旬月從西邊出現,飽滿的時候從東方上升。
在飛魚汛期結束後,在每天的午後拿著自製的魚槍在水世界上下浮沉的潛水,潛到海底選擇女人吃的魚給我孩子們的媽媽吃,而水世界裡的浮游生物會告訴我潮汐變換的強弱時段,此時我開始跟孩子們的媽媽敘述我在海裡的故事了。然而,水世界裡的綺麗美景,即便就在她的腳下,她也只能想像我在海裡潛水,在夜間划船捕飛魚是蘭嶼島達悟男人天生該有的生存本能。
是的,達悟男人天生該有的生存本能,在我回家定居之後都做到了,然而那些事並不是我內心感到最為欣慰的。當自己年過五十之後,是兒時小叔公,父親,大伯是我最思念的人,是他們的故事教育了我。
小叔公在我父親他們出海夜航,在部落鄰近的海域用火炬,用掬網撈飛魚的時候,往往是午夜過後的時辰。小叔公抱著我觀賞十人船舟用掬網撈飛魚,要我長大時把青春獻給海洋,才可以創作美麗的詩歌歌詞,才可以編劇男人與海洋的故事。如今回想起來,小叔公為何如此喜歡對我說故事,父親,大伯也是,甚至仍健在的叔父,他們都喜歡跟我說故事。
二○○七年,叔父與我合力建造一艘雙人四槳的拼板船,彼時他已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他在我們家族公用的林地敘述我叔公們的故事,他的達悟語彙經常使用masyakan,語意是說,身體潛在的「野蠻」體力是用來與巨木「格鬥」的,即便那時他已八十二歲,然而他斧削的木塊一根木絲也沒有,非常的乾淨,但叔父未曾對我說,「他累了」,濃縮叔父的話,「就是尊敬每塊取來造船的樹材」。他伐木的同時,寧靜是他原初的體能的泉源。
學校教育學來的知識,對我而言是「理性」看世界,父祖輩們給我的教育是,用「寧靜」觀賞海洋。我聽得懂他們的故事,他們划過的海我划過,他們潛過的海我潛過,他們走過的山林我走過,他們抓過的魚類我也都抓過了,也回敬了我這些尊敬前輩,原來他們跟我說許多的故事就是要我將來當個「作家」。
然而,我還未進階到他們用「寧靜」看世界,在自然環境裡萃取「寧靜」的層次。
《老海人》這本小說的配角,安洛米恩、達卡安、洛馬比克他們各自擁有很美的達悟名字,但美麗的名字在他們的現實生活裡卻不美麗,他們是部落裡的邊緣人,在陸地上「酒精」是他們喝醉時對話的對象,清醒的時候,他們在海洋裡恢復自尊的寧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海洋」終究一直在包容他們,當然也不可能拋棄他們。畢竟海洋本身是沒有邊陲,也沒有中心,她有的只是月亮給他的脾氣(潮汐)。
在此,誠摯的感謝《印刻文學生活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朋友們給我的支持與關懷。
當然更要感激我孩子們的母親,在我靈魂先前的肉體度往生後,認真的經營兒子的田產,常常孤守我們蘭嶼的家屋,而遺忘了化妝,而我也時常遺忘買保養品給她,於此同時,也祝福在大西洋海上工作整整一年的兒子,平安歸來,也欣慰在台北的兩個女兒過了叛逆期,多了美麗。
夏曼.藍波安(○八∕○九 二○○九)完稿於蘭嶼家屋
註1:達悟語,指天上的仙女祝福人出生的,以及死亡的靈魂,就是生死之時辰由她掌握。某些改宗後的達悟人,生死之魂已交給了西方宗教的上帝了。
註2:男性吃的魚稱之rahet,意思是「不好的魚」給男性吃。
註3:女性吃的魚稱之uyud,意思是「海裡真正的魚類」給女性吃。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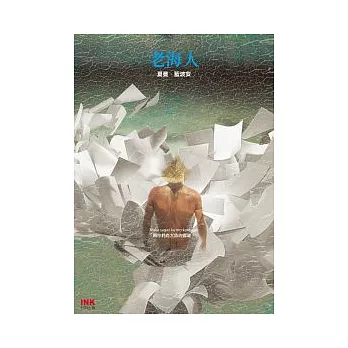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