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1
孩童們的生存遊戲
《蒼蠅王》是高汀的最高傑作,全面性地表達了他的創作價值觀。五十多年來,分析這部作品的論文多不勝數,無論是從高汀的宗教觀、人文觀,或其隱喻手法、象徵手法,甚至談他貴族學校的教師經歷、參與二戰的戰爭體驗,都一再挖掘出此作既豐富又複雜的爭議性內涵;而在傳記作家約翰.凱瑞(John Carey)的《威廉.高汀:寫出《蒼蠅王》的人》(William Golding: The Man Who Wrote Lord of the Flies,2009)裡,甚至揭露了他強暴少女未遂、酗酒、有虐待狂傾向等幽微面……這些新發現的事實,在在顯示此作未來仍有繼續探究的深沉空間。
《蒼蠅王》所描寫的主題,是人類的野蠻與鬥爭天性,絕不因年幼而有任何差異。「所謂的人類,就像蜜蜂生產蜂蜜一樣,會生產邪惡」──對於人性,高汀極度悲觀地認定,一旦外在約束消失,邪惡就會甦醒,不但將大肆破壞,甚至吞噬自我。
《蒼蠅王》擁有多層次、多面向的寓示魅力,充滿各種重新解讀、重新詮釋的可能性,引來無數創作者追隨,在當代大眾文化,特別是恐怖小說、冒險小說、青少年小說、漫畫、影視的領域裡,是「生存小說」(survival novel)的濫觴。
在小說方面,如高見廣春的《大逃殺》(1999)、貴志祐介的《深紅色的迷宮》(1999)、丹.西蒙斯(Dan Simmons)的《極地惡靈》(The Terror,2007)、蘇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的《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2008);漫畫則有?圖一雄的《漂流教室》(1974)、山田惠庸的《逃離伊甸園》(2008)──在這些新進作品中,有些題材是孩童的戰爭、有些是劣境的克服、有些則是弱肉強食的生存遊戲,由於當代強調的娛樂性,人物越加異常、衝突越加野蠻,但關於罪惡、暴力的人性論述,同樣脫離不了《蒼蠅王》指陳的範圍,顯見其無與倫比、超越時代的影響力。
再讀一次《蒼蠅王》,依舊讓人冷汗涔涔。當人類已然征服世界、對一手創建的文明引以為傲之際,《蒼蠅王》提醒著我們──人類依然是動物。
文∕既晴(作家)
推薦序2
重返青春殘酷舞台
威廉高汀的《蒼蠅王》絕對是當代小說中最值得一讀的經典作品。
它囊括了許多冒險小說的關鍵元素,劫後餘生、孤島探險、未知恐懼、同儕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懸疑、動作、驚悚,這些元素像海棉似的被吸進故事?,其中最駭人的部分,莫過於考驗人性的貪婪與恐懼。
這個世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天文學家也許知道,上帝可能更清楚。然而,標榜著文明與進步思想的人類,其實並不是地球最早的原住民,而是比較晚來的房客,透過生火與農耕,歷經了數千年所創造出來的今日世界。但我們並不知道,我們始終沒有逃離大自然環伺的潛在威脅,文明隨時有可能在一夕之間崩毀。
當我們透過電視新聞看見大海嘯吞沒日本東北沿岸的城鎮,核能電廠發生爆炸幅射塵大量外洩,龍捲風瞬間摧毀一個美國小鎮。直到目睹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災難電影真實上演,才真切體會到相較於大自然無常的毀滅力量,人類的存在是多麼地卑微渺小,我們卻依然停留在遠古穴居時代弱肉強食、彼此陰謀傾軋的循環生態鏈中,為的是什麼?除了生存,此外無他。
別再拿那種道德上的高標準來批判社會了,因為真實的世界往往只有立場、沒有是非,每個人為了謀生存做出自私自利的事情實屬必然,但是人性良善的一面,總是在最艱難黑暗的時刻,更加突顯它的光芒,互相傷害的結果只會導致滅亡,唯有信賴、互助、團結才有活下去的希望,才能獲得最終的救贖。
《蒼蠅王》就像是人類社會的微縮膠捲,你看這群天真瀾漫的孩子們,在飛機失事後,他們降落在一個不被大人管束的小島上,展開前所未有的大冒險。別把他們當作孩子看待,他們可是有相當厲害的模仿能力,竭盡所能的去模仿那個還來不及長大的成人世界,試圖重建新的秩序,卻渾然未覺無知將帶來暴力與黑暗。
在諸多條件的限制之下,作者把荒島設定成生存遊戲的殘酷舞台,你是否聯想到深作欣二執導的《大逃殺》中令人為之震撼的衝擊影像?沒錯!原著小說的創作靈感也是源自於《蒼蠅王》。
書中人物我最欣賞的是拉爾夫,他是普世價值、良善的代表,傑克則是貪婪、暴力、墮落的毀滅性角色,而小豬身上有著天真、理性主義的精神,他們各自代表著社會上抱持不同立場的群體,然則缺一不可,社會本來就是以多元並存的面貌呈現,我們不需要獨裁者,合理的民主制度可以共同面對問題並思考出解決之道,以暴制暴,少數壓制多數都不是應行的王道,倘若不是最後的團結,他們可能撐不到救援的船隻,早就自相殘殺無人倖存。
當我們身處地殼劇烈變動,天災隨時都可能降臨的今日,重讀經典《蒼蠅王》更能體會作者想傳達的意圖,如果我們希望這個世界更美好,社會更加詳和安樂,必得摒除一己之私,多站在他人的利益著想,也不要為了大量生產、速效便利的生活,去製造可能會危害我們的巨大毀滅兵器,我們根本不需要去憂慮世界末日可能降臨,應該要好好珍惜和把握每一個當下,只要活著,總會見到明天的陽光。
文∕銀色快手(文學評論家、布拉格書店主人)
專文導讀
人性即獸性
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如果還不了解,『惡』出於人猶如『蜜』產於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腦袋有問題。──威廉.高汀
《蒼蠅王》究竟是一部什麼內容的小說?它又為什麼會在西方引起如此的重視?
小說的情節並不複雜,它描述在一場戰爭中,一架飛機帶著一群男孩從英國本土飛向南方疏散。飛機被擊落,孩子們乘坐的機艙落到一座世外桃源般、荒無人煙的珊瑚島上。起初這群孩子齊心協力,後來由於害怕所謂的「怪獸」分裂成兩派,以崇尚本能的專制派壓倒了講究理智的民主派告終。
「蒼蠅王」即「蒼蠅之王」,源出希伯來語「Baalzebub」(又有一說此詞出自阿拉伯語),在《聖經》中,「Baal」被當作「萬惡之首」,在英語中,「蒼蠅王」是糞便和汙物之王,因此也是醜惡的同義詞。小說以此命名,似取意獸性戰勝了人性,孩子們害怕莫須有的怪獸,到頭來真正的「怪獸」卻是潛伏在人性中的獸性。野蠻的戰爭把孩子們帶到孤島上,但這群孩子卻重現了使他們落到這種處境的戰爭,追根究柢,不是什麼外來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樂園變成了屠場。
高汀被西方評論家列為「寓言編撰家」,他的作品被稱為「神話」或「寓言」,英國文學批評家伊文斯(I. Evans)就稱《蒼蠅王》是一部關於惡的本性和文明脆弱性的哲學寓言式小說,這話不無道理。就《蒼蠅王》而言,小說中的人物、情節和環境描寫等各方面都具有某種象徵性。
情節的發展是從拉爾夫和傑克這一對基本矛盾出發的。拉爾夫是個金髮少年,從小過著中產階級的安寧生活,心地善良,不乏主見,象徵著文明和理智(不完全的);與此對照的是傑克,紅頭髮,瘦高身材,教堂唱詩班的領隊,象徵著野蠻和專制(對基督教有所諷刺)。矛盾在於,以海螺為權威象徵的首領拉爾夫最關心怎樣才能得救,他堅持生起火堆,作為求救信號;他還要大家築茅屋避風雨,要大家講衛生、在固定地方上廁所。這些想法和要求代表著文明和傳統的力量。傑克則著迷於獵野豬,對其他事情置之不理。隨著矛盾的加深,傑克日益得勢,支持拉爾夫主張的卻寥寥無幾,最後連他自己也差點被對方殺掉。在矛盾衝突的過程中,除了如讓火堆熄滅的事件之外,對「怪獸」的害怕也占了極重要的分量。從全書看來,所謂海中來的怪獸,空中來的怪獸都是一種渲染,無非是為了突顯真正的「怪獸」來自人本身(也就是「獸性」的發作)。小說結尾的部分,拉爾夫熱淚盈眶,他「為童心的泯滅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為忠實而有頭腦的朋友小豬墜落慘死而悲泣」。而因為拉爾夫和小豬在大雷雨的時候也參與了殺害西蒙的狂舞,所以他倆的童心也不復存在。區別只在於拉爾夫終於認識到「人性的黑暗」,小豬卻始終否認這一點。
所謂「人性的黑暗」,主要是指嗜血和恐懼。嗜血從傑克開始,逐步發展為他那幫獵手的共同特性;恐懼從害怕「怪獸」出發,最終成為支配孩子們的異己力量。在這兩種因素的制約下,傑克等人把臉塗得五顏六色,在假面具的後面,他們「擺脫了羞恥感和自我意識」,並伴之以「野性大發作」。這代表獵手們已可悲地蛻化為野蠻人。拉爾夫反對塗臉,實是堅守著文明的最後一道防線。
在這場文明和野蠻的角力中,分別依附於拉爾夫和傑克的小豬和羅傑構成兩個極端。小豬是個思想早熟的善良少年,身胖體弱,常犯氣喘,他出身下層,經常用不合語法的雙重否定句來表示肯定的意思,講的是倫敦方言,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他的眼鏡是生火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可以把眼鏡當成科學和文明的象徵。儘管透過鏡片聚光為孩子們帶來了至關重要的火,但小豬始終受到嘲笑和挖苦。在作者看來,小豬的缺點在於他過分相信科學的力量,根本看不到「人性的黑暗」,因此他無法理解所謂「怪獸」或「鬼魂」都出於人的「恐懼」之心。小豬過分相信成人的世界,他沒有意識到,正是大人們進行喪失理性的戰爭把孩子們帶到了荒島上,所以,大人並不比小孩高明。陰險而凶殘的羅傑扮演著劊子手的角色,作者對這個人物著墨不多,讀後卻使人感到幫凶有時比元凶更凶惡。手持海螺的小豬最後就是死於羅傑撬下的大石。小豬之死和海螺的毀滅意味著野蠻終於戰勝了文明,拉爾夫被追逐只不過是尾聲罷了。
與《蒼蠅王》的命名直接有關的是西蒙,一個先知先覺、神祕主義者。他為人靦腆,不善言詞,但有正義感,洞察力很強。在眾人對「怪獸」的有無爭論不休時,西蒙第一個提出:「怪獸應該就是我們自己。」他想說最骯髒的東西就是人本身的邪惡,孩子們卻把他轟了下來,連小豬都罵他「放屁!」正如魯迅所說:「許多人的隨意哄笑,是一支白粉筆,能將粉塗在對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話好像小丑的打諢。」
為了弄清楚「怪獸」的真相,西蒙無畏地上山去看個究竟,中途他在一塊林中空地休息,看到當中豎著一個滿布著蒼蠅的死豬頭(這是傑克等人獻給「怪獸」的供品)。天氣異常悶熱,西蒙的癲癇症再度發作,在神智恍惚之中,他覺得滿是蒼蠅的豬頭彷彿化成一隻會說話的碩大蒼蠅王。作者藉蒼蠅王之口指出「怪獸」是人的一部分(與前文西蒙直覺的判斷相呼應),並且預告了西蒙會被眾人打死的可悲下場,這一段是揭示題意的核心。西蒙甦醒之後,繼續朝山頭前進,結果他看清了所謂的「怪獸」原來只是腐爛發臭的飛行員屍體。他不顧自己正在發病,爬下山去訴說實情,不料此時天昏地暗、雷雨交加,傑克等人反把西蒙當成「怪獸」活活打死。更諷刺的是,孩子們所殺死的「怪獸」是唯一能向他們揭開「怪獸」的祕密、使他們免於淪為真正野獸的人;孩子們把西蒙叫做「瘋子」,但真正喪失理性的卻是他們自己。不難看出,西蒙的悲劇是許多先覺者的共同悲劇,一種卡珊德拉式的悲劇。第一個直立行走的猴子據說是被其他猴子打死的,第一個說出某種真理的人也常難逃毀滅,屈原如此、布魯諾如此、中外古今皆如此。
被統稱為「小鬼頭」的孩子大約六歲,他們漫無紀律、隨地大小便,只知道吃睡玩。西蒙看不起這些孩子用沙蓋的小房子;小豬把這些孩子稱為不懂事的「小鬼頭」;拉爾夫統計自己這方的力量時把小鬼頭除去,認為他們不算數,在危急時也希望「怪獸」挑小鬼頭吃;而傑克則把小鬼頭稱作「愛哭鬼和膽小鬼」,如果被「怪獸」吃掉,那「真是活該」!帕西佛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原本還記得自己的姓名、家裡地址、電話號碼,這在文明社會中不失為有效的護身符,但在沒有法律和警察保護的荒島上,這種護身符毫無作用。故事尾聲帕西佛墮落成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記不得的野蠻人。
小說中的人物雖然都是少年、兒童,但高汀的目的是透過這些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物來揭示他的道德主題——人性本惡。高汀認為,社會的缺陷要歸結為人性的缺陷,身為一個作家,他的使命是醫治「人對自我本性的驚人無知」,他的作品是使人正視「人自身的殘酷和貪欲的可悲事實」。當然,《蒼蠅王》的成功不只是因為高汀的道德主題,普列漢諾夫指出,藝術「表現人們的思想,但並非抽象地表現,而是用生動的形象來表現」(出自《沒有地址的信》)。《蒼蠅王》中的孩子們雖然各具有一定的象徵性,但他們本身是栩栩如生的。作者採取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寓人物於故事情節的發展之中,對人物進行了多面向、多層次的細節刻畫。小說前半部呈暖色調,後半部漸轉為冷色調。作者寓情於景、藉景抒情,在某些地方做到情景交融、動人心弦,例如描寫大火、雷雨、海市蜃樓、西蒙之死等段落。小說的結構有一種簡練明快、直截了當的風格,一開始讀者就隨著主角直接進入場景,戛然而止的結局又給人回味和反省的空間。
如同所有真正的文學作品一樣,《蒼蠅王》也有其源流:源是指作者所處的環境對他創作思想的影響;流是指作品在文學史上的承繼性。
高汀關於人性本惡的觀點是抽象的,但這種觀點的形成是具體的,它濫觴於作者的經歷及其所處的時代。殘酷的戰爭粉碎了青年詩人的浪漫主義思想,導致了作家創作中嚴峻的一面。一九五七年,法國作家卡繆在瑞典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曾說過:「這是一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出生的人們,在他們二十歲的時候,希特勒政權剛建立,同時革命有了最初的進展,而他們完成教育後,面對的是西班牙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充斥著集中營、受拷打、被囚禁的歐洲。就是這些人,今天不得不來教育人,並在核武威脅下的世界上工作。我認為,誰也不能要求他們是溫情主義……」荼毒生靈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確實使許多善良的人們大開眼界,西方文明和道德走進了死胡同,比較嚴肅的作家想尋求出路,又無法在現實社會中找到出路,於是只好在作品中逃向大海或孤島,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人物難以逃脫困境,從而表現出一種充滿禁閉感的冷酷心理(如海明威於一九五二年發表的《老人與海》就是一例)。
出於這種強烈的感受,高汀對貝冷汀(R. M. Ballantyne)的《珊瑚島》很不以為然。《珊瑚島》發表於一八五七年,是英國文學中盡人皆知的兒童小說,描寫拉爾夫、傑克、彼得金三個少年因船隻失事漂流到一座荒島上,他們如何團結友愛、抗強扶弱、智勝海盜、幫助土人。顯而易見,此書屬於傳統的荒島文學。從《魯賓遜漂流記》開始的荒島文學,一向以描寫文明戰勝野蠻為宗旨,魯賓遜使土人星期五歸化可為例證。在這樣的作品中,文明、理性和基督教信仰總會戰勝野蠻、本能和圖騰崇拜。高汀在《蒼蠅王》中反其道而行,他揭露了真正野蠻的就是自詡為基督文明傳布者的白人本身,這無疑是深刻的,也正是這一點,使《蒼蠅王》別具一格,讓人耳目一新。高汀的作品經常由別人的作品衍生而來,如《蒼蠅王》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就脫胎自《珊瑚島》,但他的作品又具有針對性地帶上自己的特色。
高汀認為當代文學對他的影響很小,他說:「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有,但非要說我有什麼文學源頭的話,我會列出諸如歐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也許還有希羅多德這樣大名鼎鼎的人物。」《蒼蠅王》與歐里庇得斯的《酒神》確實有某些相似之處,可資佐證。首先,從主題思想來看,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希臘神話中代表本能的力量,《酒神》一劇即描寫了這種自然原始力量的勝利,《蒼蠅王》描寫的人性本惡,與酒神代表的非理性力量一脈相傳。其次,從作品的重心來看,《酒神》一劇描寫忒拜王彭透斯不相信酒神,有一次他化裝成女人去偷看酒神女信徒的祭祀,而女信徒們(彭透斯之母也在內)在極度的狂熱中把他當「野獸」撕得粉碎,這是酒神對彭透斯的懲罰,西蒙之死也與此相仿。再者,從結構上來看,《酒神》一劇是以酒神突然出現作為結尾,採用了所謂「機械降神」的手法。在《蒼蠅王》快結束時,拉爾夫被傑克等人追得走投無路,卻突然出現了來營救的軍艦和軍官,也有點像「機械降神」。關於這一點,高汀認為成人的戰爭只是更大規模的孩子們的獵捕,軍官可以把孩子們重新帶回「文明」的世界,但又有誰來拯救軍艦和軍官呢?
《蒼蠅王》之所以能在客觀上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為《蒼蠅王》出版之際,正是東西方冷戰激烈的時期,核戰的陰影籠罩著全球,不少人不只想到核武將會給人類帶來怎樣的直接危害,更想到萬一核戰爆發後倖存者將會如何,《蒼蠅王》大膽預言了歷史上可能發生的可怕一頁,因而迎合了人們對核戰的後果感到憂慮和思考這個議題的需要。另一方面,當時大學裡的文學教學受到「新批評派」研究方法的影響,以精讀課文為基礎。《蒼蠅王》具有多層次、多面向的象徵性,正好給人們提供了「見仁見智」的各種可能。相信弗洛伊德的人,從中得出孩子們的行為是對文明社會和父母權威的反抗;道德主義者認為由此可知,一旦脫離社會制約和道德規範,「惡」會膨脹到何等程度;政治家則說《蒼蠅王》說明了民主的破產和專制的勝利;基督教徒歸之於原罪和世紀末;還有人索性把高汀視為存在主義者。由此可見,在這樣的社會現實和這股文學潮流中誕生的《蒼蠅王》,能夠很快引起共鳴、受到評論界的重視,也就不足為奇了。
身為一個具有獨創性的作家,高汀一向否定創作中表面化和簡單化的做法。他強調作家要擺脫一切傳統的政治、宗教和道德信條,透過自己的眼睛獨立觀察世界,但他觀察到的結果卻令人絕望。高汀對黑暗的社會現實深感不滿,但他卻把這些弊端歸之於解決不了問題:抽象的人性本惡。在此有必要指出,《蒼蠅王》的人性本惡主題並不新鮮,在東方思想史上,荀子早就說過:「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韓非更是力主性「惡」說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認為人是凶惡的動物,在原始狀態下人對人,就像狼一樣。這種說法的缺點在於把人看成孤立的個體,把人性看成抽象的存在。「但是,人的本質並不是單一個體所固有的抽象存在。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西方的一些評論家強調高汀與貝冷汀的區別,但他們沒有看出他們倆殊途同歸:兩者都從抽象的人性出發,只不過前者描寫的是「惡」的征服史,後者描寫的是「善」的征服史。荒島固然為文學上的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提供了充分的想像空間,但荒島文學的弱點也在此,就某種意義上而言,這種文學畢竟是背對現實的。
總而言之,高汀的作品並沒有、也不可能「闡明當今世界人類的狀況」,從中反而可以看出嚴峻西方社會現實的曲折反映,看到作家想尋找出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惱。高汀的本意是想透過《蒼蠅王》,複製一部袖珍版的人類發展史,但他忘記了個體發展史並不完全重現種系發展史。當然,這不代表《蒼蠅王》沒有發人深省之處。恩格斯說過:「人起源於動物這個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擺脫的多寡;在於獸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異。」(出自《反杜林論》)人類的前途無疑是光明的,但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不見得沒有烏雲蔽日的時候;人類的未來是可以樂觀的,但盲目的樂觀主義者不見得比認真的悲觀主義者更高明。至少在提醒人們警惕和防止一部分人「獸性」大發這點上,讀讀《蒼蠅王》也許會有所啟示。
文∕龔志成(本書譯者)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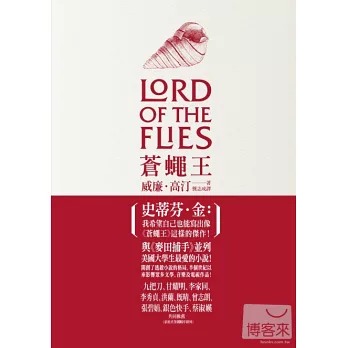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