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安洛米恩的哥哥齊格浪,是我與吉吉米特、卡斯瓦勒的小學、國中同學。我們是蘭嶼國中第二屆的學生,島上六個部落的孩子,除去朗島部落外,五個部落的孩子聚集椰油部落念國中,青澀的臉龐,整日在學校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磨蹭,可以說是我們民族近代歷史的一大盛事,同時也是我們這個世代,出生於戰後的一九五〇年代的青少年開始認識新民族、新帝國、學習新殖民者的新語言、新文化,開始了我們夢的迷思的旅行。
我們六個部落說達悟語的口音各有差異,可是卻要學習共通說四音階的華語,以及英語,於是語音的差異發生了許多許多的笑話,譬如,A部落的同學朗讀華語:
「該洩了,該洩了,席校燜狗刮著過起,打價瀨了,同溪瀨了,老師一賴了……」正確的華語念法如下:
「開學了,開學了,學校門口掛著國旗,大家來了,同學來了,老師也來了……」
B部落的同學念:
「該薛辣,該薛辣,席校悶購寡之果器,打家ㄌㄞˇ辣,董希ㄌㄞˇ辣,ㄌㄠˋ師一來辣。」
又如:
「老是,搭說,搭又打勿嗎?」
「老師,她說,她有打我嗎?」
「米油補賴,搭燜朔的。」
「沒有不來,她們說的(她們說,她不要來)。」
諸如其他部落的同學,用達悟語音說華語引來許多的笑話,一到了晚上,宿舍裡的笑話就連篇連夜,連夜震動玻璃窗,夾著相互認識的好奇。達悟語、華語,兩種語言交叉的混音,這個過程最佳的模仿者是由最為頑皮的卡斯瓦勒所發動。
我們這一屆國中同學的出生年約是由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八,我們男同學的宿舍是工藝教室,每一個人一張三尺寬六尺長的合板為床,以桌子為衣櫥,為界線。
我的睡床左邊是齊格浪,右邊是卡斯瓦勒,頭對頭是吉吉米特。齊格浪是個安靜、寡言的同學,面容的皮膚都比我們白而嫩,然而每一個夜晚,我不曾聽過齊格浪跟我說過他未來的夢想,包括他的初戀情人,出社會後來成為情侶。我們國三時,他的大弟也過來念國中,從那時起安洛米恩開始來國中「要飯」與逃學,開始認識了我。他來國中,我們就會偷偷留白飯給他,安洛米恩於是對我有了好印象。
當我高中畢業,出社會的第二年,就是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在板橋染整廠工作,遇見三位在土城工業區工作的同學,其中之一,就是齊格浪。見到他,嚇我一跳,他變得很壯,很粗獷,不得志的眼神讓他變得非常喜歡抱怨,很怨天尤人。然而,外來「文明」入侵我們的島嶼之初始,我們這一代的達悟人,又有誰是得志的呢?
時光飛逝,一九八一年齊格浪回蘭嶼家,開始在《蘭嶼雙周刊》發表「小說」,當時蘭恩的創辦人跟我說這個事情,言下之意,我是當時的大學生,他也希望我寫「小說」。雖然我讀的是法文系,讀法國文學,然而,何謂「小說」,我一點概念也沒有,甭說寫「小說」。可惜同學寫的小說,我沒閱讀到。
當我大學畢業,在台北開計程車,搞原住民運動,有一天我接到南港山胞服務中心的電話:
「認不認識齊格浪與他的弟弟。」
「認識。」
原來齊格與他的大弟都住進了北市信義路底的精神病療養院,我當保證人把兄弟倆從醫院領出來。醫院交代我說:「他們不能喝酒。」那是一九八六年的七月,同年的九月,齊格浪跳樓自殺身亡。我當時跟朋友們募款,他的父母親與安洛米恩從蘭嶼來桃園,那一趟是安洛米恩第一次來台灣,他又遇見了我,同時開始跟我要菸抽。
一九八九年我回祖島定居以後,安洛米恩在蘭嶼機場常常遇見我,很自然地要菸抽,開始跟我說他的故事,當他進入他妄想的世界時,他說著達悟語,華語也非常流利,讓我佩服。當時我也開始寫散文,我於是慢慢記憶他的故事與遭遇。
我個人從小喜愛遠眺海平線逐夢,追夢。海,給我沒有疆界的無限想像……
國小,我們發現我們自己不是漢人、漢族,不會說華語,於是學校老師給我們稚幼心靈的謎題是:漢人文明,我們野蠻;漢人進步,我們落伍。
何謂文明?何謂進步?這是我個人一直在對抗的問題,也是整個星球人類的問題。筆者從開始說話起就一直生活在喜歡說海浪的故事,造船的故事,夜航獵魚的故事,男人吃的魚,女人吃的魚,燒墾伐木的生活,許多的數不清等等的,都市文明生活律動已遺忘的有機生活,獨占了我成長與求學的旅程。
原來我民族的島嶼生活被學校老師說成野蠻的生活,原來魚類分類的知識被說成是落伍的。時間飛逝,成長的學習是摸索,更是去對抗一元化的價值準繩,如今筆者方意識到,很自信地說,所謂的野蠻!所謂落伍!是我所擁有的,所追求的,是你所沒有的。
在深山裡與父親,叔父,堂叔的伐木經歷,讓我看見了純潔的野蠻美學,讓我身體髮膚深深體悟到原木到雛型到船身到海洋到魚類,那是我民族的環境信仰的核心,就是我們的詩歌文學;與家族裡的男人夜航捕飛魚,夜間潛水捉魚,潛水射魚,男人吃的魚,女人、孕婦吃的魚,海鮮貝類等分類的食的文明,讓我看見了體悟了分享的本質,就是我達悟人的海洋文學,所有的這些都必須經過傳統宗教的儀式。於是我身體髮膚深深體悟到儀式與分類知識是我達悟人的海洋文學,是我們珍愛島嶼環境,海洋生物的具體表現,這些都斧刻在我的身體,以及力行之,學習與環境、海洋相融,這些是你沒有的海洋文學。
筆者的寫實小說的真實人物安洛米恩、達卡安、洛馬比克、吉吉米特、卡斯瓦勒,夏本‧巫瑪藍姆、馬洛奴斯,以及筆者本人,都困在現代文明裡的迷題與迷思裡,從現實的島嶼生活來論,我們確實都藉著不同季節的「海洋」不斷地重複療傷,這兒沒有終極結論,只有愈來愈複雜的進行式。
身為書寫海洋律動的情緒的台灣籍的作家,迄今熱愛純文學創作的能量不減,也是我一生唯一的志業,純文學創作是多元而嚴肅的,也絕對是深遠的,你我他的文學作品,其更廣的意涵是,屬於台灣的華語文學,我稱你們是主流文學,我稱安洛米恩、達卡安、洛馬比克、吉吉米特、卡斯瓦勒、夏本‧巫瑪藍姆、巫瑪藍姆、馬洛奴斯等等是移動的「海流文學」。
當安洛米恩來不及把他航海家族的故事說給達卡安的時候,當他的大哥,我的同學齊格浪還來不及書寫的時候,我們的同學吉吉米特已經航海到了英屬法蘭克福群島,南、西太平洋。
這本書深深表達對他們的敬愛,還有我那些把我心魂帶到海上,我家族的海流前輩們,謝謝他們真實的故事。
願野蠻與落伍與我長在
夏曼‧藍波安完稿於新店七張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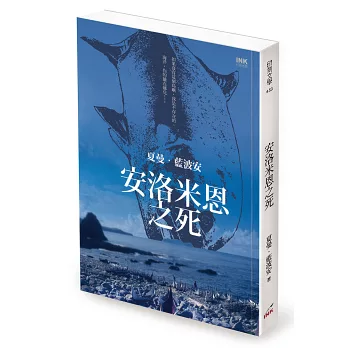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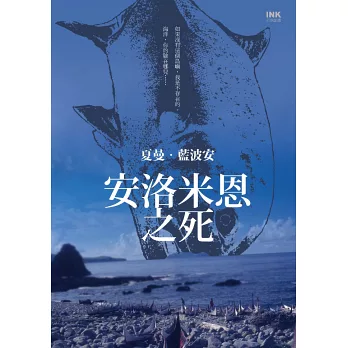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