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良知即為其心中之尺度
本書德文版原名《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一九一四至一九三三年回憶錄》。作者塞巴斯提安.哈夫納為二十世紀德國最著名、影響最深遠的政論家與歷史專論作家。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撰寫於一九三九年,過了六十一年以後才首度與世人見面,被書評界譽為「二○○○年度德國出版的最有價值書籍」。德國《時代報》並於二○○二年秋,將本書列入學生必讀的五十本書籍之林──其中包括歌德的《浮士德》與《少年維特的煩惱》、卡夫卡的《審判》及《短篇小說集》、馬丁路德翻譯的《馬太福音》、湯瑪斯.曼的《威尼斯之死》、施篤姆(Theodor Storm)的《白馬騎士》等世界文學名著。本書之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在此之前,《美國圖書館協會書目》(ALA Booklist)已將本書與《安妮日記》相提並論,稱之為「書中瑰寶」。美國《評論月刊》(Commentary)指出:「這本大師之作……娓娓道出希特勒帝國難解的重重謎團,幾乎令現代探討同一主題的長篇大論均瞠乎其後。」德國最著名的希特勒傳記作者費斯特(Joachim Fest)亦撰文表示:「這本小書足可取代一整個書架的報導文學作品。」
哈夫納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二日生、卒於柏林市,享年九十一歲。其生平充滿傳奇性,二十世紀德國史幾乎等同他個人的歷史。柏林市長狄普根(Eberhard Diepgen)即曾發表悼詞表示:「塞巴斯提安.哈夫納的一生,體現出許多德國人在本世紀的命運。」
他去世之前幾個月,「德國第二電視台」(ZDF)歷史節目的負責人古多.克諾普教授(Prof. Guido Knopp)已撰文表達輿論界對其高度的評價:「他的寫作能力,在德語地區幾乎無人可出其右:其語言強而有力、扣人心弦、優美雅致並富於獨創性。哈夫納是名副其實的全民作家,他在大戰結束以後,透過書籍、專欄及隨筆,獨自向德國讀者傳播歷史知識與歷史意識。這是旁人所無法企及的。有人因此對他心生不滿,其功成名就更招來了妒忌者。……哈夫納天賦異稟,有辦法將論點極度尖銳化,以石破天驚的方式,把眾人習以為常的事物改弦更張呈現出來,藉此發人深省。」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為哈夫納早年的作品,但已多方面顯露其日後的語言特質。全書始於一九一四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結束於一九三三年底,即哈夫納在「候補文官營區」通過「世界觀教育」之際。眾所周知,一九三三年就是「第三帝國」元年。
作者將二十年來的德國歷史與個人遭遇合而為一,稱之為「親身體驗歷史」。而一九一四至一九三三年之間,正是德國開始出現「大地震」的時代:
哈夫納入學不久,戰爭便結束了他的童年。他以「小沙文主義者」及「待在家中的戰士」等方式,興高采烈期待「最後勝利」到來。結果德意志帝國在他小學畢業前後戰敗並鬧出革命,變成了「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威瑪共和);德國必須割讓七分之一的領土、十分之一的人口,並且每年支付巨額賠款。當時街頭出現的「義勇軍」,被哈夫納視為日後納粹「突擊隊」的前身。
他上初中時幾度發生內亂、政變和內戰,德國瀕臨解體。他就讀高中以後,德國幣值於一九二三年不斷狂跌,馬克對美元匯率以四點二兆比一收場!也就在那一年,德國傳統的價值觀淪喪殆盡,凡事皆見怪不怪。各方妖魔鬼怪亦紛紛出籠,其中一人表現出「有如癲癇症發作一般的動作」。那個人便是希特勒,但希特勒正式登場的時刻尚未到來。德國經濟於同年底恢復穩定,進入「黃金的二○年代」,各路「救世主」被迫重返冬眠狀態。哈夫納本人則已蛻變為自由派的國際主義者。
哈夫納進入大學研讀法律前夕,威瑪共和首任總統艾伯特去世,由興登堡元帥接任──此人日後將任命希特勒出任總理。不過當時實際執政者為史特雷斯曼,以外長(副總理)的身分為德國帶來安定。柏林成為國際色彩十足的文化之都,哈夫納也自懂事以來首度經歷和平的日子。但是一般德國人並不曉得應如何享受「無聊的」自由生活,只想再度進行集體冒險行動。
史特雷斯曼於一九二九年猝逝以後,已無任何政黨可獲得過半數支持。興登堡乃架空國會的內閣同意權,逕自任免總理。他任命布呂寧接任總理時,全球正面臨經濟大恐慌,德國失業人口暴增至六百多萬,妖魔鬼怪再度躍躍欲試。布呂寧乃以「手術獲得成功,病患已經死亡」,或「陣地固守下來,人員全部損失」的模式,以反民主的措施維護威瑪共和,結果值得捍衛的事物所剩無幾。
哈夫納大學生涯的末期,亂局驀然重返。納粹在一九三○年國會大選中,從一個令人發噱的小黨躍升為第二大黨,從此希特勒的陰影不斷籠罩德國。布呂寧下台之後,相繼由投機取巧的巴本和性好權謀的施萊歇爾組成短命內閣。同時納粹於一九三二年兩次國會大選中成為最大黨。德國於是在哈夫納大學畢業前後變天,一九三三年一月底由希特勒上台組閣。
納粹上台還不到一個月,哈夫納就在化裝舞會上結識一位猶太少女(他日後的妻子)。結果那場舞會被白面金髮的「黑衫隊鯊魚面孔」強力驅散。兩天以後,國會大廈遭人縱火(可能為自導自演),興登堡立即在納粹催促下簽署《護民衛國行政命令》,限制德國人的言論、集會及新聞自由,德國自此處於戒嚴狀態。接著新國會通過臨時修憲案(《授權法》),將立法權拱手交予政府。此後希特勒即以「合法」方式肆意集權,幾個月之內已將各級政府及組織全面納粹化。
納粹接著在同年四月一日展開抵制猶太人的行動。哈夫納對猶太女友的愛意卻變得益發堅定,因為「沒有人可以強迫我去抵制她」。可是當他與女友前往野外踏青時,卻有一班又一班郊遊的學童興高采烈對著二人喊道:「猶大去死!」
哈夫納畢業以後在「柏林高等法院」實習期間,納粹「突擊隊」襲擊該院,將所有猶太裔法官及律師攆了出去,法院被迫關閉一個星期之久。接著有「黑衫隊員」取代猶太人出任高院法官,要求其他法官不得拘泥於法條,從此希特勒的旨意取代了法律,德國司法體系乃沈淪至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可是當時德國從左到右的政黨均喪失道德勇氣,以致束手就範或自動解散,德國變成了法定的「一黨國家」。作者的朋友或已投靠納粹而與之形同陌路,否則即已流亡海外。最後只剩下哈夫納暱稱為「查莉」的猶太女友,陪伴他度過苦難期。
哈夫納是「血統純正的雅利安人」、從未參加任何政黨及政治活動,除了女朋友是猶太人之外,全無「污點」可言。尤其納粹企圖建立「國家社會主義新法學」,他身為新生代法學家,正是新政權極力拉攏的對象。可是哈夫納既無意捨棄猶太女友,更不願於此環境下出任公職。在他眼中,納粹就是自己所珍惜之一切事物的敵人,於是不斷抗拒誘惑,並逐漸走上抵抗之路。然而能供他選擇的抵抗方式極為有限,只能「過著不泛政治化的生活」和「不與狼共嗥」。哈夫納一度在盛怒之下打算移居巴黎,但其父堅持他必須先通過國家考試及獲得博士學位,為學業畫下完美句點。作者聽從了父親的意見,可是為了取得參加考試的資格,被迫連續數週接受納粹的集體洗腦教育。
以上即為全書大致的故事背景。雖然哈夫納撰寫至此即已收筆,不過其原意是一直撰寫至一九三九年。我們不妨將有關本書的後續發展簡單過目一下:
哈夫納一通過國家文官考試,便於一九三四年初前往巴黎。他在該地停留半年並完成博士論文,接著返回德國成為自由作家。哈夫納前往巴黎之前,已開始為一些德國報紙撰稿,透過隱喻來表達對「第三帝國」的不滿。他投稿的主要對象,就是具有兩百年光輝歷史的《福斯日報》(Vossische Zeitung)。可是在他回國之前,《福斯日報》早就承受不住納粹政府的一再打壓(一年之內即有二千多位記者遭勒令退職),已經被迫停刊。這位日後的政論大師失去了自由創作的空間,只得在《珊瑚報》(Die Koralle)撰寫輕鬆小品,然後為《淑女》(Die Dame)流行服飾雜誌負責編輯工作。
禍不單行的是,納粹政府在一九三五年九月頒佈《紐倫堡法案》,禁止「雅利安人」與猶太人通婚,以「捍衛德國的血統與榮譽」。哈夫納與猶太女友埃莉卡.希爾胥無法締結良緣──那是非法行為!而埃莉卡的身分證件還被大大蓋上J這個字母,標明她是猶太人(Jude)。
埃莉卡在一九三八年初移民英國。哈夫納隨即於同年八月做出最後決定,選擇了猶太女友和流亡生涯,與埃莉卡先後在劍橋及倫敦過著貧困潦倒的生活。納粹時代的德國流亡者泰半為猶太人或曾經參加「不正確政黨」的人士。哈夫納與之不同,在納粹時代並未直接遭受迫害,純粹遵照自己的良心來做事。「只問是非,不看立場」即為哈夫納此後一生的寫照。無怪乎哈夫納去世以後,德國《明星雜誌》譽之為「德國的道德良知」。
作者在英國終於獲得自由發揮的天地,可以暢所欲言。他不想牽累留在德國的親人,於是不使用本名──萊蒙德.普雷策。他結合了作曲宗師賽巴斯提安.巴哈(Sebastian Bach)姓名的前一半,以及莫扎特《哈夫納交響曲》(Haffner-Symphonie)的標題名稱,做為自己的筆名,同時藉此展現自己對「另一個德國」的懷戀之情。此後他即以賽巴斯提安.哈夫納之名卓然於世。
哈夫納抵達英倫三島之後開始撰寫《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他才寫了一半,納粹德國就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入侵波蘭,英國乃對德宣戰。於是哈夫納把這本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著作永遠擱置下來,改弦更張以政治做為探討重點,寫出一本名為《論德國之雙重性格》的小冊子。英國在一九四○年與德國交火,哈夫納是敵國公民,於是兩度遭到拘留,險些被船運至加拿大集中監禁──依照當時德國潛艇活躍的程度,哈夫納不無永遠消失之虞!幸好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論德國之雙重性格》被邱吉爾規定為內閣人手一本的讀物,哈夫納不但從此躲過牢獄之災,進而在英國新聞界打響名號,並於一九四八年正式成為英國公民。如此一來,哈夫納當初寫下《一個德國人的故事》這本回憶錄,似乎就意謂著自己與德國的永遠告別。
可是在一九五四年的時候,西柏林出現了一位英國《觀察家報》駐德特派員。他很快就成為廣播、電視訪談節目的常客。德國大眾起初覺得奇怪,為什麼那位記者的德語聽不出外國口音?後來人們才逐漸曉得,原來他從前是德國人。那位「英國記者」當然就是哈夫納。
到了一九六一年,哈夫納重新投效德國新聞界,先後為《世界報》和《明星雜誌》撰寫專欄,並從一九七○年代開始著述歷史專論。過去他向英國人介紹德國,此後的職志改為向德國人解釋自己的國家,成為一位特立獨行、無法被歸類為「右派」或「左派」的媒體工作者。他寫出的政論,經常在德國政壇投下一顆炸彈;而他撰寫的歷史書籍,例如《希特勒》或《不含傳說的普魯士》,皆為經典名著。其中《希特勒》一書,更是國際間評價最高、銷路最廣的希特勒專論,曾經連續四十三週在德國暢銷書排行榜名列前茅,讓不少專業歷史學家覺得很不是滋味。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更是一本不同凡響的作品,集奇人、奇事、奇書於一身。德國《明鏡週刊》即曾表示:「我們彷彿聞到了一九三○年代初期柏林的空氣,當時哈夫納已經預見了希特勒上台後即將成形的災難。」「中部德國廣播電視台」(MDR)表示:「這本青年時代的回憶錄,以難得一見的方式,精確而深刻地描繪出納粹主義崛起的時代氛圍。」英國《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評論是:「哈夫納透過卓越的觀察力與想像力,以生動逼真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現出德國百姓的心理狀態……其深刻的見解說明了希特勒如何得以大權在握。」美國《密爾瓦基新聞衛報》(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稱讚道:「哈夫納就像是但丁的『地獄』嚮導,以詳盡細節描繪出德國逐漸落入納粹手中的經過……全書風格清新、立論直接,而且充滿奇妙的個人色彩,是一本引人入勝的著作。」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譽之為:「第一流的傑出回憶錄。」德國《世界報》則稱之為最偉大的「流亡文學」作品之一。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不久即已成為世紀經典名著。不過這種空前的盛況起先相當出人意料之外。哈夫納生前從未提及此書──其子奧利佛.普雷策於整理遺物時才意外發現早已泛黃的打字稿。尤其哈夫納自一九八七年以後即因年老體衰而無法繼續創作,逐漸自一般人的記憶中淡出。更何況全書撰寫於六十一年前,完成了一半就因為二戰爆發而束諸高閣,甚至部分文稿已經散失。無怪乎德國DVA出版社印刷三萬冊以後,即認為此數量應可綽綽有餘。
結果這本來自一甲子以前、中道而止的遺作,在二○○○年夏末付梓以後立即造成轟動,不但連續數月在德國銷暢書排行榜名列前茅,更成為聖誕節的熱門禮物。一年內僅僅在德國就售出了三十二萬冊。中譯本所採用的最新增訂版於二○○二年中面世時,《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已經再刷了十幾次!德國更出現迄今未衰的「哈夫納熱」,其一九三○、四○年代為德、英報刊撰寫的論述也紛紛被集結成冊發行。
國際間的反應也頗為類似。本書英文版發行人魏登菲德勳爵(Lord Weidenfeld)曾向「倫敦猶太文化中心」發表演說表示:「《挑戰希特勒》(Defying Hitler)是一本最出色和最富於想像力的書籍,是我們所出版過的最重要書籍之一。」(《挑戰希特勒》為本書英文版書名)。連遠在天涯海角的紐西蘭「旺阿努伊」(Wanganui)圖書館也傳來佳評:「哈夫納撰寫偉大歷史論述,並將讀者身歷其境地帶入當時日常生活的能力令人嘆為觀止。這是一本非凡的著作,值得一再咀嚼玩味,並將書中所述牢記在心。這是每個人都必須一讀的著作──不論是否曾經閱讀過有關納粹德國的書籍。」
二○○一年下半年,情況一度有所改變,德國報刊突然出現攻詰《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文字。哈夫納一生充滿爭議,為右派眼中的「左派」和左派眼中的「右派」,幾十年來得罪了不少人。其身後所獲得的熱烈讚揚,更令那些人由妒生恨,想利用他無法還手的機會,一舉將之徹底擊垮。率先發難者是一位退休的藝術史教授──保羅(J[u..]rgen Paul)。他在八月十日公開表示,《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只可能完成於二戰結束後,理由是書中出現一些此前沒有的用語,例如「最後勝利」(Endsieg)是二戰末期的用語,而柏林地鐵站在三○年代還沒有「電動手扶梯」……。他的說法很快即遭駁斥:一戰時德國已在談論「最後勝利」,柏林地鐵站於一九二七年即已使用電動手扶梯。
但「柏林自由大學」歷史系教授科勒(Henning K[o..]hler)六天後向保羅提出聲援,發洩鬱結已久的悶氣。他表示:許多事情是哈夫納當時根本不可能曉得的,所以文稿偽造於六○年代或更晚,然後放置於身後可被人「意外發現」之處,藉以展現自己的「過人才智」並「製造賣點」。「專家」言之鑿鑿如此表示之後,德國新聞界對本書的評價暫時變得比較保守,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哈夫納之子於是寫下出書的來龍去脈,將之收入二○○一年增訂版(〈後記〉的部分)。同時他主動將原稿交付「德國聯邦刑事局」鑑定。「聯邦刑事局」依據紙張的同質性(特殊英國規格:19.8 × 25.2公分)、紙張的水印及年代(一九三六年開始出現)、所使用的打字機(分別為德國一九二九及一九二八年的機型)……,在兩個月後提出鑑定結果:「原稿完成的時間絕不晚於一九三九年。」新聞界並發現,許多哈夫納「當時不可能出現的觀點」,在一九四○年出版的《論德國之雙重性格》早已白紙黑字表達出來。整場鬧劇自此落幕,哈夫納的聲譽更是如日中天。接著二○○二年三月又發現兩份遺稿,於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出現了最終的版本──最新增訂版。
攻訐哈夫納的理由雖然五花八門,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哈夫納打破了一個歷史神話。
希特勒雖然是被探討得最頻繁的二十世紀歷史人物,可是「希特勒現象」始終無法被完全解釋清楚。某些新聞界和史學界人士甚至在有意無意之間,將希特勒及納粹時代「淡化處理」,並把大多數德國人呈現為純粹的受害者。許多經歷了納粹時代的德國人,更可在後生晚輩質問的時候,堂而皇之表示:「當時的許多事情我們根本就不曉得。」哈夫納卻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裡面,從一九三○年代一個平凡德國人的角度,點出了即將成形的災難。這只能表示,當時凡是還沒有閉上雙眼或者視若無睹的人,都不可能看不見納粹的暴行和集中營,以及即將出現的戰爭與大浩劫。
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做出了預言,因為那些都是我們今天已經曉得的事情。其真正的意義就是,哈夫納入木三分地描繪出他那一代人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成長過程、心理狀態和社會變遷。同時他以最生活化、最直接的方式告訴我們,納粹的「世界觀」如何一步步滲入每個德國人的私人生活領域,最後演成千古悲劇。納粹在本書撰寫時仍為「現在進行式」,使人產生身歷其境的感覺,閱畢以後不覺驚呼:「難怪會變成那個樣子。」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的書評即表達出各國讀者的普遍反應:「想知道希特勒為什麼有辦法上台嗎?答案就在這裡!」本書也聯帶使人對二十一世紀的時局進行省思。除了德國以外,許多歐美國家的讀者均表示:「同樣的事情今天也可能在我國重新發生。」德國《明星雜誌》甚至在二○○年非常露骨地表示:「哈夫納的作品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當我們面對下一次考驗的時候,果真會有把握做出較佳的表現嗎?」
哈夫納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序幕指出,書中有一個「密而不宣的道德寓意」(啞謎)。哈夫納戰後的作為,似乎就為這個道德寓意做出了最佳的解說:納粹其實並沒有那麼可怕,真正可怕的就是當時德國人的集體軟弱和集體精神錯亂──他本人也不例外。如果不在事發當時立即提出異議,日後將不再有置喙的餘地;他在希特勒上台的時候也曾採取「置身事外」、「事不關己」的做法,最後只得期待外國用武力來拯救德國。當他流亡英國撰寫本書的時候,還想「打自己一記耳光」。因此哈夫納在德國新聞界重新起步以後,採取了類似「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做法,對當政者的不當措施立即嚴辭批判。他思慮周密、直言無諱,成為令任何政治人物頭痛的對手。
例如一九六八年一年之內,就發生了兩個著名事件,充分展現了哈夫納敢做敢當的行事風格。當時西德政府準備查禁極右派的「國家民主黨」(NPD),他立刻提出反對意見:「黨禁意謂議會民主因為畏懼死亡而進行的自殺!」(雖然他反對該黨)。西德政府稍後也對左派學生的「議會外反對運動」(APO)進行鐵腕鎮壓行動,他這個六十一歲的老頭子於是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
時人對他的評語是:「哈夫納從不向威權低頭屈服。他經常以絆腳石的姿態出現,有時更完全棄自己的前程於不顧。」他去世的第二天,《柏林晨間郵報》(Berliner Morgenpost)更發表了一篇名為〈良知即為其心中之尺度〉(Sein Gewissen war sein Maßstab)的專論:「隨著哈夫納的去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不但失去了最嚴厲的批判者,同時也失去了最聰明的捍衛者!」
周全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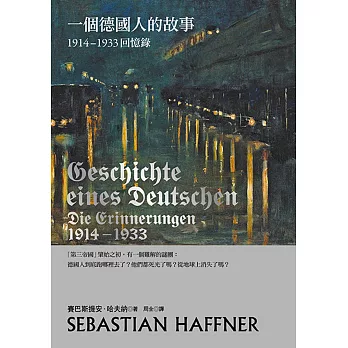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