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向梭羅致敬
交完譯稿後查看資料時才發現,到今年七月十二日,我們翻譯的這位奇人已誕生二百週年了。而我彷彿剛剛從他在華爾騰湖畔的小木屋歸來,豈止有一種時空穿越之感!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麻塞諸塞州康考特鎮,一八三七年畢業於名校哈佛大學,但按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的說法,他「在文學上是一個打破偶像崇拜的人,他難得感謝大學給他的益處,也很看不起大學」(愛默生《梭羅》)。畢業後梭羅在家鄉一所私立學校教書,並受到同住在康考特的愛默生的激發和影響,幾年後便完全轉向寫作。他為愛默生主編的評論季刊《日晷》撰稿,並協助編輯該刊。寫作之外,也到處演講,主張回歸自我和自然。一八四五年,梭羅為踐行他的生活觀念,在距康考特兩英里的華爾騰湖畔建造了一個小木屋,靠雙手勞動養活自己,體驗獨立、簡樸和接近自然的生活。他的散文集《湖濱散記》(一八五四年出版)詳細記載了他在那裡兩年零兩個月又兩天的生活。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梭羅因愛默生一家需要,離開華爾騰湖,重新回到康考特鎮。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因肺病醫治無效逝世,時年僅四十四歲。
在同時代人眼中,梭羅不過是一個愛默生的追隨者,一個偏執而怪異的人,直到十九世紀末期才被廣泛認識和推崇。梭羅一生創作了二十多種散文作品,尤其是他的《湖濱散記》,不僅被視為自然隨筆的經典,而且「變成了處於迷惘狀態的人們的生活指南」。其他有影響的作品首推政論《公民不服從》,面對政府、法律的強權和不義,為公民拒絕服從提出辯護。梭羅所主張的這種依靠個人力量的「非暴力抵抗」,後來對列夫‧托爾斯泰、聖雄甘地、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和美國民主主義、民權運動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有的《湖濱散記》版本中,最後也收有這篇《公民不服從》,它和《湖濱散記》其實也有直接聯繫:在華爾騰湖生活期間,梭羅因為拒交「人頭稅」而被捕,雖然他只在獄中蹲了一宿就被友人在未經他本人同意的情況下保釋出獄。為解釋他的抗命行為,後來他做出了這個著名的演講。
同我的許多同代人一樣,我在早年上大學期間讀的也是徐遲的譯本(現在據說已有數十種譯本了)。徐遲先生不僅首次將《湖濱散記》譯介到中國(1948年),其譯本在「文革」結束後重版,也吸引了廣大讀者,像葦岸、海子這樣的作家和詩人就深受其影響。徐遲先生舒展自如、優雅而富有韻味的譯文風格在那時也頗為人所稱道。
但是,如同歷史上的一些經典,《湖濱散記》也正是一部需要反復閱讀,需要不斷重新認識和發現的作品。
而對我來說,最好的閱讀方式就是翻譯。我自己的工作雖然主要在詩歌領域,但是,因為接受了作家榜的邀請,因為有這個機緣「以翻譯的方式」來重讀,我還是深深地激動了:一個眾說紛紜的梭羅更真切地出現在我的面前。我不僅透過翻譯真正抵達他的「在場」,而且對一個繁茂而深奧的文學世界、自然世界和靈魂世界有了更多,也更能給我帶來喜悅的發現。
比如說《湖濱散記》的第一章〈Economy〉,有的中譯本譯為「簡樸生活」,我認為這樣譯就有些問題,問題可能來自人們對梭羅的某種慣有的簡單化讀解,也來自對「詩意地棲居」這類當下願景的迎合。《湖濱散記》記載了梭羅在湖畔林間的獨居生活,梭羅的口頭禪也是「簡單,簡單,簡單」(Simplify, simplify, simplify),但梭羅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種避世隱士。與其說《華爾騰湖》是一曲田園牧歌,不如說它是英雄詩篇,是對那個時代和社會的挑戰,而這在愛默生看來也帶有一種「英雄」和「先知」的氣質:「這時候他是一個強壯健康的青年,剛從大學裡出來,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選擇他們的職業,……惟其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絕對自主,也要每一個人都絕對自主,所以他的處境只有更艱難。但是梭羅從來沒有躊躇。他是一位天生的倡異議者。……他的目標是一種更廣博的使命,一種藝術,能使我們好好地生活。」
愛默生的描述,真實地表露了梭羅的精神狀態和前往華爾騰湖畔居住的社會背景和心理動因。這種我行我素、不計代價對生活理想的踐行與通常的那種隱逸是有很大的差異的。實際上,梭羅渴望寧靜獨處,但同時又是一位很有責任感和參與精神的社會批評家,他寫有許多政論,一生支援廢奴運動,反對美國對墨西哥的戰爭,宣導公民權利和「公民的不服從」,必要時甚至甘願為此坐牢。即使在華爾騰湖畔期間,他也常常與人交往,並保持著對社會的關注。他只是不想循規蹈矩成為所謂「文明社會」的寄居客,而寧願「絕對自主」,去過那種更合乎本性的生活罷了。他在華爾騰湖的來去都合乎他性格的邏輯。他並沒有想到華爾騰湖畔日後會成為一個聖地。他也並不希望別人來追隨他,他只是痛感於人們在生活中的迷失,「還包括那些貌似富有卻於所有人中極為貧瘠的人,他們積攢了些無用的財產,卻不知如何使用或擺脫」,他要透過自己的實踐向世人證明何為自由和人生之價值,他寫下這部書,也「並非為自己,而是為人類;我身上的缺點和矛盾,並不影響我的陳述的真理性。……我下定決心,決不低聲下氣地做魔鬼的辯護人。我要努力為真理說話。」
觸動我的,就是梭羅的這種坦率和真實。他並不想充當一個聖人。他來到華爾騰湖畔探索生活的意義,但他絕不自欺,也不給他的鄉鄰和讀者提供任何廉價的、靠不住的承諾。他正是我所讚賞的那種「徹底的思想家」(radical thinkers)。如第十一章〈更高的法則〉的這個開頭,就使我深感驚異:
「當我提著一串魚,用魚竿探路穿過樹林回家的時候,天色已經相當昏暗了。那時,我突然瞥見路上有一隻土撥鼠悄然橫穿而過。一種野性的快感使我不自覺地戰慄,並使我強烈地想要捉住他,將他生吞活剝;並不是因為我那時餓了,只是為了他表現出來的那種野性。……我曾發現在我內心裡面,和大多數人一樣有一種追求更高的或者稱之為精神生活的本能,至今也還是如此。但同時,我又有另一種本能朝著原始的佇列和野性走去。我對這兩種本能都心存敬畏,對野性的狂熱也並不亞於善良。……我有時候喜歡粗劣地對待生活,更願意像動物一樣過日子。」
由此可見,梭羅來到華爾騰湖畔並拿他自己做「實驗品」,如用詩人雷內‧夏爾的一個說法,既是「對頂峰的尋找」,也是對「基礎」的重新勘探(夏爾的一部詩集即是「對頂峰和基礎的尋找」)。即使是「詩意地棲居」,首先也要把它建立在一個真實可信的基礎上。
正是基於這種「總體」上的瞭解,我們把第一章「Economy」按其本意譯為「經濟學」。這個看似不那麼「詩意」的開場白,卻更能還原梭羅生活和思想的出發點。當然,隨著閱讀的深入,我們會發現梭羅的「經濟學」,遠遠超出了一般層面,而具有了人生和倫理的意義。
《湖濱散記》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辯之聲,自辯,與鄰人和社會的對話和愛默生所說的「異議」。人首先是一種肉體的物質存在,是社會和經濟生活的一員,而且人人都得獨立謀生。爭辯就是從這種常識開始的。十九世紀中期,隨著工業革命對社會生產力的高速推進,傳統的生活方式受到衝擊,人們對物質文明的追求也相應遞增,人們不是忙於生計,就是在追逐所謂更奢華與舒適的生活方式,但是,對於「別給我金錢,別給我名譽,給我真理吧」的梭羅來說,這一切的意義和價值何在呢?他看到的是,在表面的光鮮和富有下,「芸芸眾生都過著一分平靜而絕望的生活」。他以自己的切身經驗向人們呼籲:
「據我自己的經驗,目前在我們國家,只需要一把刀、一柄斧頭、一把鐵鍬和一輛手推車等少數工具就足夠生活了,對於好學之人,還要再加上燈和文具,以及能讀上幾本書。這些東西僅次於必需品,花一點點錢就能得到。」
而為了發現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都有哪些,又該如何獲得,梭羅甚至在第一章中精細地列了一份份帳單,比如全部造房的材料費,豆地的花費與收入等。「總之,信仰和經驗使我確信,只要生活得簡單而智慧,維持一個人在世間的生命並不是一件苦差,而是一種消遣。」他甚至以他富有個性的方式說:「我寧願坐在一顆南瓜上,將它完全據為己有,也不願和眾人擁擠著坐在天鵝絨軟墊上。」
梭羅的這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在今天已為更多的人所認同和接受(比如在今天就有「必要的貧窮」「清潔精神」等說法),但在當時的那種社會習俗下,如按愛默生的評價,卻是「革命性」的。梭羅自己在《湖濱散記》中也講到這樣一個細節:「我要定做一件款式特別的衣服,女裁縫神情嚴肅地告訴我說:『他們現在可都不是這麼做的』……就好像她引用的是命運女神那樣一位非人間的權威。」「在給我量尺寸的時候,如果她不考量一下我的性格,而只是量我肩膀的寬度,就好像我是那掛衣服的釘子,那這種丈量又有什麼用呢?……我有時感到絕望,在這個世界上,要借助人們的力量完成一件哪怕十分簡單、樸實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他們必須先經過一次強有力壓榨機的擠壓,好把舊觀念擠壓出去,如此一來,他們一時之間也無法站穩腳跟……」
這就是梭羅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愛默生就曾這樣充滿欽佩地描述:「有幾個人幾乎崇拜他,向他坦白一切,將他奉為先知,知道他那性靈與偉大的心的深奧的價值。……他以這樣一種危險性的坦白態度處世,欽佩他的人稱他為『那可怕的梭羅』,彷彿他靜默的時候也在說話,走開之後也還在場。我想他的理想太嚴格了。」
但還有一點,梭羅對自己當然是嚴格的,在《湖濱散記》中他力求證明自己,說服別人,但他並不希望別人按他的方式生活。他自己的生活,在他看來不過是天賦良知的一種昭示:
「年輕人可以從事建築、種植或航海,只要能做他跟我提過的他喜歡做的事情,不妨礙他就好了。我們的智慧,就體現在透過計算而得到的那個精確的點,就好比水手或者逃跑的奴隸的眼睛總要盯著北極星;這種方法足以指導我們一生。或許我們不能在可預測的時間內到達預定的港口,但仍會保持正確的航向。」
可以說,梭羅的這種對世俗虛榮的拋棄,對物質文明和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抵制,在後來對重塑「美國精神」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美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嬉皮運動和「垮掉一代」那裡,我們就可以明顯聽到其迴響(縱然有些人學到的只是皮毛)。且不說「垮掉派詩人」,「新超現實主義」或「深度意象」詩人們也明顯和梭羅有一種血緣關係,如羅伯特·勃萊的「貧窮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詹姆斯‧賴特的「我突然感到/如果我能脫出自己的軀體,我就會/怒放如花」等。
在我喜愛和認識的詩人蓋瑞‧施耐德身上,也能看到梭羅的影子。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他透過翻譯寒山,創造的正是一個類似於「華爾騰湖」的新神話:「他是一名山中狂人,屬於古代中國衣衫襤褸的隱士中的一類。當他說『寒山』之時,不僅指他自己,也指他的住所和他的精神狀態。」
重要的是,同梭羅一樣,施耐德的人生也正是「知行合一」的一生。1955年從伯克利畢業後,他與森林公園簽約,成了一名山道維修隊的工人,整天在荒郊野嶺戶外工作。與他翻譯的寒山詩同時出版的,是他自己的成名詩集《砌石》(Riprap),他聲稱這是「為了紀念雙手的工作、對岩石的置放以及我開始將宇宙視為整體的那一刻……」「我猜這些詩歌之所以被欣賞,不僅僅是因為其中的藝術,還因為其中的汗水。」
的確,我熱愛這位詩人,他那些書寫大自然和戶外勞作、間或向中國古老大師致意、帶著汗水閃光和靴子的吱嘎聲的詩篇,不僅讓我深感親切,在我看來,還是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某種必要的「糾正」:「作為一個詩人,我依然把握著那最古老的價值觀,它們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土地的肥沃,動物的魅力,與世隔絕的孤寂中的想像力……我力圖將歷史與那大片荒蕪的土地容納到心裡,這樣,我的詩或許更可接近於事物的本色以對抗我們時代的失衡、紊亂及愚昧無知。」
多麼孤絕而又富有歷史洞見的詩人!正因為如此,在當今這個所謂後工業的時代,他卻在完成著一種「大地神話」的重構。在這方面,梭羅就堪稱一位先行者。梭羅在華爾騰湖畔黎明即起,到冰封的湖畔取水,他所迎來的,正是那片新大陸「大地之詩」的「第一道黎明的光線」。他也仍將為未來的人們提供啟示和範例。
以上主要介紹了梭羅回歸自然和本性的生活實驗,他所發現的人生真諦及其對後人的激勵和啟迪。《湖濱散記》引人入勝,也絕不單調,而是如大自然一樣豐饒。如同書中的梭羅是一個生活實踐者、修行者,也是一個詩人、哲人、預言家,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社會批評家,也是大自然的勘探者、博物學家、魯濱遜式的拓荒者、生態和環境保護主義先驅……在他這部作品中,蘊藏著巨大的複雜性、多樣性和啟示性。
梭羅的洞察力、感悟力和他的實踐能力一樣驚人,愛默生就這樣描述:「有一天,他與一個陌生人一同走著,那人問他在哪裡可以找到印第安箭鏃,他回答,『處處都有』,彎下腰去,就立刻從地下拾起一個。……他健旺的常識,再加上壯健的手,銳利的觀察力與堅強的意志,依舊不能解釋他簡單而祕密的生活中照耀著的優越性。我必須加上這重要的事實:他具有一種優秀的智慧,一種極少人數特有的智慧,……然而在他,這卻是一種永不休息的洞察力;……他永遠服從那神聖的啟示。」
或者說,在他的身體力行中,攜帶著他的生命哲學和光照。按照人們通常的說法,梭羅是一個「超驗主義者」,他相信人能憑直覺和本能認識真理,能憑心靈的力量提升生活,使生活變得崇高。華爾騰湖不僅是他在喧囂的世界中尋得的一個去處,也是他精神的家園,這個地方不僅給他提供了豆地,冬日的篝火,思考的空間,也給他提供了認識自然和自己的各種機遇。「古代詩歌和神話至少表明,農事曾是一項神聖的藝術」,不僅是農事,他在這裡感受到的一切都不能不讓人稱奇。他在這裡觀察、傾聽、思考,並且夢想,如他所稱,他含蘊、養育著他的珍珠,直到它完美之時,就將它奉獻於社會。
在《湖濱散記》中,有大量篇幅是關於動物、植物和自然環境的觀察記錄,這是全書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內容之一。梭羅在這裡花費了大量精力觀察湖水和樹木的變化,鳥類、動物的習性,有時還深入地質考古學的層面,這使《湖濱散記》的許多篇章初看上去像是有關自然的文獻。但是,梭羅展示自然的財富,是為了讓它成為人性的、精神的資源。他的這種貢獻,讓我不禁想起阿赫瑪托娃對帕斯捷爾納克的讚頌:「整個大地成為他的遺產/他要每個人與他一起分享。」
愛默生也非常看重梭羅對大自然的探索:「他決定研究自然史,純是出於天性。……他與動物接近,使人想起湯麥斯‧福勒關於養蜂家柏特勒的記錄,『不是他告訴蜜蜂許多話,就是蜜蜂告訴他許多話。』……很少有人像他這樣深知大自然的祕密與天才;這種知識的綜合,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廣大更嚴正。因為他毫不尊敬任何人任何團體的意見,而只向真理本身致敬。」的確,梭羅對自然的觀察、體驗和發現每每讓人驚歎。他不是簡單地記錄下事實與感受,他筆下的種種事物也不是靜態的,而是充滿了活力和啟示。他筆下的大自然不僅洋溢著一種原始的生命力,有一種粗獷蒼鬱之美,甚至還深具一種神祕性,有一種神話般的性質:
「啊,華爾騰湖的梭魚啊!當我看到他們躺在冰面上,或在漁夫所鑿的、有一個小孔來引入活水的冰井中時,總是會驚奇於他們那罕見的美,彷彿他們是傳說中的魚類,對我們的街道來說如此陌異……他們擁有一種相當炫目而超驗的美……他們不似松樹的青綠,不似石頭的灰褐,也不似天空的蔚藍;但是,在我眼裡,他們確有罕見的色彩,……他們,當然是全然無損的華爾騰;在動物王國中也是小小的華爾騰,華爾騰教派!我驚異於他們在此處被捕獲──這集金黃與祖母綠於一身的偉大魚類……隨著幾下痙攣般的游轉,很輕易地,他們就掙脫了自己在水中濡濕的幽靈,彷彿一個凡人在升入天堂那稀薄空氣前的時刻裡,掙脫了自己的肉身。」
這種對華爾騰湖梭魚的讚頌和神話般描述,不可能不對人們的感受力和後來的文學、詩歌產生影響。在伊莉莎白‧碧許的名詩《魚》的最後,我就感到了這位美國著名現代女詩人對梭羅的「致敬」:「……直到那船舷上緣/直到每一種東西/都成了虹彩,虹彩,虹彩!/我把魚放回了大海。」
梭羅是大自然的探索者和讚頌者,也是大自然的翻譯者,在翻譯中他認出宇宙的律動,也認出人與自然的「血親」關係。如第十七章中對冬去春來之時華爾騰湖的描述:「華爾騰湖在迅速融化……一塊巨大如野的冰從其主體中破裂出來。我聽見一隻北美歌雀在河岸的灌木叢中歌唱──謳利,謳利,謳利──叱,叱,叱,掣,吒,──掣,微嘶,微嘶,微嘶。」這是多麼動人啊。而在最後一章的結束語中,也即向他鍾愛的華爾騰湖告別之前,梭羅打通了人與自然的血肉關聯,向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獻上了這樣的頌歌:「我們體內的生命,就像河流中的水。它今年的水位,可能升高得為前人所無法想像,並漫上焦渴的高地。」然後他的筆觸竟轉向了一隻強壯、美麗的蟲蛾:
「誰聽了這個故事,不會強烈地感受到它對復活與不朽的信仰呢?又有誰會知道,何等美麗的、長著翅膀的生靈,它的卵已經埋葬在木頭的年輪中,進入生如死灰般的人類社會好多年了,先是封存在蒼翠鮮活的樹木中,後來這樹木漸漸變成了它枯塚的外殼──當一家人圍坐在節日的餐桌旁,它持續多年的啃噬聲,碰巧被這家中的人聽見──會出人意料地從這社會中最不起眼、隨手轉賣的家具中飛出來,終於享受到它完美的盛夏!」
最後,我簡單談一下梭羅的藝術風格、藝術成就和我們的翻譯。《湖濱散記》──多半內容草成於梭羅居住於華爾騰湖畔期間,後來經過了補充、修改和重寫。鑑於他的第一部書《康考特和梅里馬克河上的一週》的失敗,在寫作和修改《湖濱散記》時,梭羅格外慎重,他沒有倉促寫就和出版,而是靜下心來對經驗進行過濾和提煉,一次次地對文稿進行修改,使之達到完美。
《湖濱散記》早已是美國現代文學中散文作品的典範。它是生活和精神的傳記,但也是語言的藝術創作。如梭羅在日記中所說,他的寫作以真實經歷為依據,但「事實只是我的畫像的框架」「是我正在寫作中的神話中的材料」。《湖濱散記》的最後成書,讓我感到的,也正是一種「把大地轉化為神話」的卓越努力。這不僅在於他對《聖經》、古希臘、羅馬神話和典籍(如古羅馬加圖的《農業志》)、印度和中國古老智慧的大量參照和有機引用,更在於他對平凡事物的詩性轉化和神話重構,正如愛默生所指出的:「他性靈的知覺上有詩的泉源。……他也善於在散文中找出同樣的詩意的魅力。」這就是為什麼在《湖濱散記》中,會處處閃耀詩性的元素和神話的光輝。
《湖濱散記》的風格獨樹一幟,融自敘、觀察、思考、想像、批評為一體,像一部雄渾的交響樂。梭羅的文筆雄健有力,元氣充沛,富有思想性和鮮明的個性。他把敏銳的感受力、精準的觀察力和「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的想像力與概括力結合為一體。在行文風格上,有人已指出過他的特點:語句直截了當(straight forward)、簡約精煉(concise)、言說切題,往往一語中的(to the point),完全不像維多利亞中期散文那樣散漫、堆砌和矯情,也沒有那種朦朧和抽象的氣息。
在翻譯時,我們也時時感到了梭羅的語言天才,感到了他在語言上非凡的創造力。正如他自己聲稱,他要創造出「一個腐朽的時代所無法理解的語言」,他要拋開一切陳詞濫調,「回到語言最原始的類比和衍生意義上」。正因為如此,給翻譯帶來了極大挑戰。梭羅的語言,往往是敘述、觀察、哲思、雄辯和詩性隱喻的難以拆解的綜合,密度大,難度高。在翻譯時我們縱然耗盡了心力,但不敢說就完全達到了滿意的程度。此外,怎樣在今天重建梭羅的語調和文字風格,這也是我們面對的課題。在已有大量譯文的背景下,我們所做的,是儘量忠實於原文而又能在譯文語言上有所刷新和創造,重要的是,要讓人能聽出那活生生的語調。本書的翻譯除了我和李昕主譯外,李海鵬、唐小祥、方邦宇也參與了部分文字的初譯工作。我們從中學到了很多,感受到很多,它對我們的震動和啟示,也深深抵及到我們生命的深處。這一切,正如愛默生在《梭羅》一文中所引用的梭羅自己的詩句:
我本來只有耳朵,現在卻有了聽覺;
以前只有眼睛,現在卻有了視力;
我只活了若干年,而現在每一刹那都生活,
以前只知道學問,現在卻能辨別真理。
我們衷心希望,這不僅是我們,也是讀到這部偉大作品後更多的讀者所能獲得的珍貴感受。
王家新
二○一七年六月五日於北京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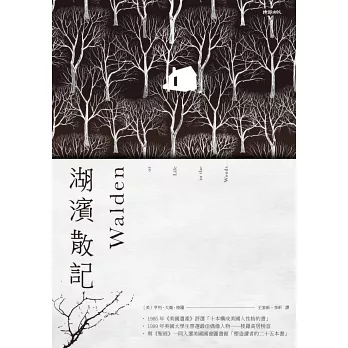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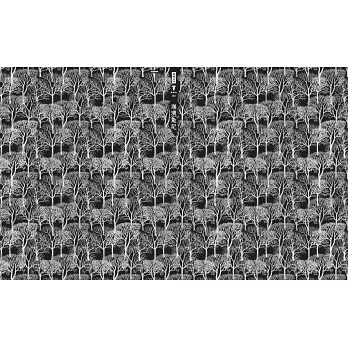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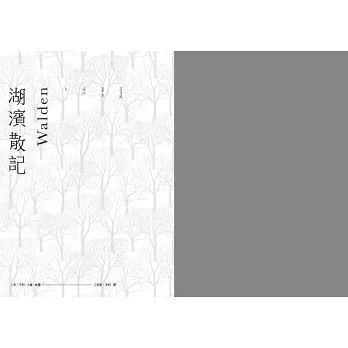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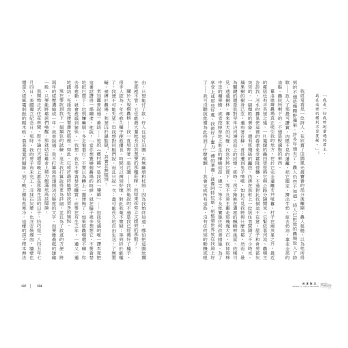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