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若你看得到,就仔細看
若你看得到,就仔細看
若你能仔細看,就好好觀察
這是薩拉馬戈在其小說《盲目》上的一段話。某天當他在改版上市的《切.格瓦拉:革命前的摩托車日記》(Diario de Rodaje)的封套上發現這段時,他說,「突然之間,對於迫切恢復視力,對抗盲目,我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洞穿的眼力。我之所以能如此,是不是因為我已經看見了那些書中未被實際寫下的字句?或者,是否因為今天的世界變得更加需要對抗陰暗?我不清楚。但是,若你能看得到,那就好好觀察吧。」
是的,今天的世界更加需要對抗陰暗,因為,這是一個「謊言的年代」。這本書,一個擅長用隱喻與寓言來探索世界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筆記,就是透過直接的批判,要人們張開眼睛去洞察世界,不再盲目。
薩拉馬戈的人生其實就是伴隨著葡萄牙顛簸的政治史,而且文學之外,他也始終以不同方式介入政治。
一九二六年,薩拉馬戈四歲時,葡萄牙出現軍事政變,成立了獨裁政權。一九三二年,薩拉查(Antonio Salazar)擔任總理,建立起法西斯性質的「新國家」政權。一九七四年四月,康乃馨革命爆發,葡萄牙開啟民主化的道路。
薩拉馬戈的前半生幾乎就是在法西斯主義下度過,他做過許多不同工作,如技師、基層公務員和報紙專欄作家,因此對體制有不同的認識。一九六九年,他加入共產黨,參與這個抵抗法西斯政權最主要的政治力量。
一九七四年康乃馨革命後,左翼軍事政權上台,工人佔領工廠、農民獲得土地,企業也被國有化,薩拉馬戈也被任命為國有報紙的主管。但在新政權的統治下,各種罷工和抗議不斷,內閣不斷更迭,左右派鬥爭激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又爆發一次不成功的政變後,溫和派取得政權,推動新憲法下的首次國會選舉,成立一個採取社會民主路線的新政府。但作為共產黨員的薩拉馬戈因此被報社開除,此時他五十多歲。
薩拉馬戈決定要做專業作家。而他上次出版小說,也是他第一次出版,是二十三歲。他說,「被開除是我生命中最幸運的事情。這個事件讓我停下來思考,開啟了我作為一個作家的新生命。」
然後是一本接一本小說,並且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二○○八年九月開始到二○○九年八月期間,在太太的鼓勵下,他開始寫部落格,內容是關於他的朋友,生活感受,以及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這些文章集結成為這本英文書名叫做「筆記」的書。在這一篇篇短小而犀利的篇幅中,我們看到一個強烈人道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如何嚴厲地批評小布希和義大利總理、批評以色列政府(「如果愚蠢會殺人,那麼不會有一個以色列的政客還會在世界上,也不會有任何一個以色列士兵還活著」);他也寫他在墨西哥聽馬科斯演講的激動,寫轉型正義、關達那摩監獄、這個世界對對女人的壓迫。他甚至批判動物園制度:
如果我能夠,我想關閉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動物園。如果我能夠,我想發布禁令,禁止馬戲團使用動物表演……,比起動物園來,還要更叫人沮喪的,是讓動物在各種荒謬項目中演出的馬戲團秀:穿著裙子的可憐小狗、海豹必須使用牠們的鰭狀肢,表演出鼓掌的動作、馬在韁繩上披著羽毛……。
薩拉馬戈的核心關懷是這個世界是被「組織性的謊言」編織而成的網所覆蓋。他們說我們作為選民是國家的主人,他們說我們做為消費者是市場的主人,但其實我們是被政客和企業所矇騙、操弄,支配。當然做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薩拉馬戈更激烈批評了宗教的謊言。
在他寫作的二○○八年,有一個人最能代表謊言的祭司:
如果一定要給小布希這個人的一生給予一項肯定的話,那就是有一項程式,在美國總統、機器人喬治.布希身上運作十分良好:說謊。他曉得他在說謊,他知道我們清楚他正在撒謊;不過,作為一個習慣性的騙徒,即使當最為赤裸裸的真相就擺在他的眼前,他還是會繼續說謊。……身為一位資深榮譽的騙徒,他是騙徒界的高等祭司。……小布希把真相實話從這個世界排除出去,在他的地盤上,現在建立起了屬於謊言的繁盛年代。今日的人類社會受到謊言的毒害,這是道德汙染當中,最惡質的一種,在這當中,小布希要負起主要的責任。
的確,還記得小布希說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毀滅武器所以要出兵攻擊嗎?是這個謊言和九一一共同拉開了二十一世紀的血腥之幕。
薩拉馬戈對當代民主的實踐也是充滿了懷疑:
我們錯誤地認知民主便只限定在所謂政黨、國會和政府這些計量的數字與機制的運作,絲毫不去注意它們的實質內涵,並且放任它們扭曲、濫用選票所賦予它們的位置以及責任。……讀者們不能將我上一段裡所談的,歸結成說,我反對政黨的存在:我本人是它們當中的一份子。讀者們不該認為我憎惡國會,或者它們的成員……我只是拒絕接受,現行的民主模式,會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裡,唯一一種可行的道路……我們明明就在餵養著這些禍害,卻表現得像是發明了一種萬物通用的萬靈藥方,能夠治癒在這星球上六十億居民的身體與靈魂:服用我們這款民主靈藥,一次十滴,一天三次,你就能永遠歡樂下去。而真相是,真正而且唯一致命的罪孽,就是偽善。
這個對民主的偽善與謊言的批判是左翼思想的根本傳統。薩拉馬戈說的對,我們不能以為政治民主可以脫離經濟與文化的民主而存在,也不能以為現行的民主是唯一的可能。然而,我們也不能像某些左派徹底否定「資產階級民主」而淪為左翼威權統治的辯護者(當前最明顯的就是中國的新左派學者,以批評西方民主來將現行中國的政治模式合理化)。關鍵不是要揚棄現在的自由主義民主(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對政治權力的制衡等),而是要不斷深化,因為民主意味著公民能更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更好地控制掌權者,而這都是現行民主模式還需要大幅改革的。
當然,資本主義體制中民主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真正影響公共事務的不是 人們選出的政府,而是沒有人民賦與正當性的市場。薩拉馬戈寫下這段非常精采的話:
人民並未選擇能管控市場機制的政府,相反的,是市場在各個層面上,透過政府,把人民交到市場機制的操弄之下。而我如此的談論市場機制,唯一的理由就是在今日,它是特出、統合而唯一的權力,是全球經濟和金融的強權,這種強權並非民主,因為它從未經由人民選舉;這種強權不是民主,因為它從未交由人民統治;而最後,這種強權不屬民主,因為它並未以人民福祉為其目標。
尤其,這些文章的寫作時間正好是金融危機爆發,而這個危機讓過去二十年縱橫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徹底破產。薩拉馬戈毫不留情地批評金融資本家們所犯下的罪惡:「在每一個角度來說,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都是種違反人道的犯罪……我並沒有誇大其詞。種族滅絕、民族文化滅絕、死亡集中營、酷刑、蓄謀刺殺、蓄意引發的飢荒、大規模的汙染、以及透過羞辱來壓迫受害者的認同,違反人道的犯罪並不僅限於此。違反人道的犯罪,也是現下那些金融和經濟霸權,加上美國和它們那些實際上默許犯罪的政府一同共謀,業已冷血地加害於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們。 」
二○○八年下旬,他更和幾位來自不同國家、抱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們,簽署了一份共同聲明,宣稱:「「紓困」就意謂著「利益私有化,損失國家化。」這是一個特殊的機會,以有利於社會正義的觀點,來重新規範定義全球經濟體系……,現在紓困的對象,應該是我們,我們公民!而我們應該以速度和勇氣,來支持將一場經濟戰爭轉變為全球發展的經濟……。新資本主義?不!……改變集體與個人之間經濟關係的時刻已經到來了。正義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
「馬克思從來沒像今天這樣正確過。」他說。
然而,即使他從左翼的觀點嚴厲批評了資本主義與現行的民主,他對當代的左派評價也很低:「左派對於他們所居住的這個世界,一點操他媽的理念想法都沒有。」「左派還是繼續他們那懦夫般的態度,不思考,不行動,不冒風險往前踏出步伐。」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說,「我曾經無數次的自問:到底左派將往何處去?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左派與他們的天然支持者--窮苦大眾與懷抱夢想的人們--之間,產生了如此根深蒂固的隔閡與鴻溝?他們本身的信條,又還有多少迄今仍留存下來?」
簡言之,這不僅是個謊言的年代,還是個失去抵抗的想像力的年代,是我們自己從戰場上撤退了:「我們已經喪失了分析這個世界上正發生事情的批判能力。我們看來是被鎖藏在柏拉圖的洞穴裡,業已拋棄我們思考和行動的責任。我們已經讓自己成了無法憤怒的呆惰生物,無法拒絕隨波逐流,失去了向我們最近的過去,那些崢嶸的人與事,發出異議的能力。我們已經來到了文明的終點,而我並不歡迎那象徵終結的最後號角聲。」
許多人認為薩拉馬戈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在紐約時報雜誌的長篇訪問中他說:「這個世界對千百萬人的人是地獄一般的悲慘。這世上雖然有不少人試圖尋找出路,但是你無法改變人類的命運。我們生活在一個黑暗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我們的自由正在消逝,我們沒有批評的空間,而極權主義--多國企業的極權、市場的極權--甚至不需要一個意識型態,並且宗教的不寬容力量正在上升。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就在這裡。」
在本書中,他自己也說:「我通常被說成是一個悲觀的人……,我通常強調對於我們人類在道德上任何有效且實在的進步與改進之可能性,感到懷疑。」
但是,他接下來說,「實際上,我寧可選擇樂觀看待,即使是只剩下一個希望,也就是那直到今天,日日都升上來的太陽,明天也依然會升起。太陽明天依然會升起,但是總有不再日出的一天。文章開頭的這些反應,是受到家庭暴力這個議題激發引出的思量。」
的確,當面對實際問題時,他仍然對戰鬥保持樂觀,比如當時面對歐巴馬的上台,他是帶著期待的:「在歐巴馬的演說裡,他告訴我們一些理由(這些「必要」的理由),讓我們不受上面這些聲音的欺瞞蒙騙。比起當前我們所詛咒的模樣,這個世界可以更好。基本上,歐巴馬在演講裡告訴我們的,就是「世界是可以有所不同的」。我們當中有許多人,長期以來一直在倡議這個想法。或許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嘗試去作以及決定世界將如何不同的大好機會。這將會是個起點。」
更重要的是,他終究認為「如果有朝一日,這個世界能夠很成功的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我知道這只能是透過我們的行動,才能夠達到的結果。」
那麼文學可以改變世界嗎?在紐約時報的訪問中,他表示悲觀:「一個倫理的小說可以暫時影響一個讀者,但只有如此。我會盡量地寫,但是當我的讀者說你的小說改變我的生命時,我不相信。也許這就像新年願望:你只有在第一週會希望記得這個願望,然後就忘了。」
但是,即使小說的力量有限,他還是必須要寫,因為:
如果一個作家屬於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倘若他沒有受到過去的鎖鏈綑綁,他就必須知道他生而為人的這個時代當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那麼,當今之世的問題是什麼呢?……最根本、最要緊的是,當世界需要批判觀點的時候,文學就不應該遺世而孤立。
是的,這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的樂觀。縱使我們生活在當前民主與市場體制下的謊言的年代中,但薩拉馬戈還是不斷地用他的小說,用這本「筆記」,提醒我們不要繼續麻木∕盲目,而是要仔細去看,要好好觀察,然後,起而改變。
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張鐵志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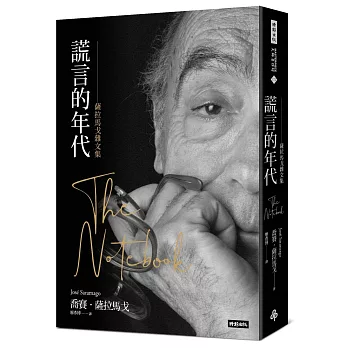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