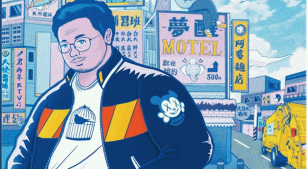推薦序
導演庶民詩劇場的日子—許赫《早晨,有垃圾車經過》序
白靈
許赫是個活得有點不耐煩的人,參加「合作社」玩玩詩也就罷了,沒想到越玩越起勁越大膽,自己不想也勸別人不要再當柏拉圖的「洞穴人」,要「告別好詩」來一起玩詩。末了乾脆拉著《早晨,有垃圾車經過》的標語到處收集這社會的垃圾,最後還把它們倒在「詩劇場」的舞台上,一件件展示他收集到的「寶貝」,並邀請原本還困在洞穴裡看不清真相的庶民百姓走出來看劇,許赫站在台上對社會宣告,說:看呀,你們,不,我們,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他這本詩集很適合編成荒謬劇,幽默與刺痛並存,笑聲與眼淚交織。他不試圖拯救什麼,但他記錄一切正在崩壞的事物,不說大道理,而是把苦悶難熬的日子寫進詩裡,讓你苦笑著點頭說對對對。
在他的詩裡,早晨是幽微而漫長的傷口,垃圾車的聲響劃破城市慣常的寧靜,也劃破我們對生活的「假性接受」。他的詩像一台沿街出沒的垃圾車—每天出現,不起眼,卻默默清運我們生活中的廢物與不滿。他的語言日常到不行,卻又彷彿從生活最灰濛的角落中蒸餾出來,帶著油煙味、發霉的光線與冰冷塑膠的質地,然而正是在這些不起眼的事物中,我們才真正看見了這個時代、這個社會、這些人—與我們自身。
比如〈漫長的等待〉是一首在靜默與無力之中怒吼的詩:
生命是漫長的
這一天到那一天
這個痛苦到
各種痛苦
等待是漫長的
這個盼望到那個盼望
這個人到
沒有任何人
漫長的生命
那是一條終於會
走完的隧道
地板是人工的
冷是人工的
無聊是人工的
光
是人工的
等待
從很久很久以前
蔓延到現在
被等待寄生的人
都喝塑膠瓶裝米酒
全詩節奏緩慢,幾乎無聲,但那種疲倦中攪動的痛苦卻極為震耳。這是一首反制度的詩,是一首從鋼筋水泥與螢光燈管下長出來的存在主義詩作。等待,在詩中不再是希望的另一面,而是一種「被迫」的生存狀態。從「這個痛苦到/各種痛苦」、「這個人到/沒有任何人」,詩人將等待寫成一種延伸性侵蝕,像藤蔓一樣從時間的裂縫裡長出,纏繞著那些還沒死、活不好但仍得活著的人們。詩以極簡、重複與冷峻的語言,描繪了一種存在的荒涼與絕望,「生命」與「等待」視為彼此糾纏的無盡長廊。特別是末兩句:「被等待寄生的人/都喝塑膠瓶裝米酒」,前一句暗喻那些無法主動掌控命運、只能靜候某種改變或救贖的人,不是人在等待,而是等待活在他們身上,如同一種寄生蟲,吸走意志與尊嚴。而「塑膠瓶裝米酒」則是一種極具台灣社會底層象徵的物件—廉價、冷冽、無詩意卻深具現實痛感的慰藉。極其具象、粗糙卻誠實的畫面使等待讓人沉淪、失落,最終只剩一瓶米酒陪著度日。許赫用極其克制的語言與冷硬意象,將生命的荒謬感與社會的冷漠揭示得令人心寒。
德勒玆(Deleuze,1925~1995)說所有人皆是社會性動物,都活在被規範好的「條紋空間」中(馬路、電線、規則、條約、年月日),秩序井然、可測量、具再現性,這與「平滑空間」(海、沙漠、天空、森林)的流動性和無結構性形成鮮明對比,而人都有「由此而彼」想「逃逸」或「游牧」出去的衝動。許赫的詩作其實即其「告別好詩」主張的實踐,是「棄條紋」而「就平滑」的大弧度跳躍,因此由此詩集輯一的「類童詩」寫法,即其「一起來玩詩」的行動示範,要主動將生活中的瑣碎事物和不完美,詩化成有意義或只是「好玩」(比如詩)的東西,因只有這樣才過得下去。
垃圾車的路線每天都固定,是「條紋式」的,但其裝載和將棄置或焚化的垃圾卻是髒亂雜沓以致成「平滑式」,是毫無規則可言的堆疊。如此,我們日常的語言也都按某種規則被說出,詩則不然,它是不按規則的重組,堆出疊出「非條紋的平滑」,這即是借語言以「逃逸」或「游牧」的一種方式。因此許赫寫的都不是崇高理想或宏大歷史,而是庶民生活裡的「小痛苦、小荒謬、小信仰」。他的詩中充滿這些場景:洗澡盆像鱷魚、肥皂像儒艮,孩子托夢說要買皮帶給死去的爸爸,學生在教室裡因為畫「五顆星星」被質疑,一張洗爛的名片還好是自己的才鬆了一口氣,而傷心的爸爸是因「生意不順利/同事不和睦/政府黑白來/候選人好瞎」,這些看似微不足道卻又遍及每一家庭每一人的日常細節,透過他精準又「貼地氣」的觀察與轉譯,都成為詩意的來源。他的詩是一種庶民的記錄術,也是一種輕巧的抵抗。
許赫的語言極簡、白話、冷調,非常靠近說話口氣,但不落於單調平淡,反而藉由重複、斷裂、跳接,製造出詩的節奏與語感。他善於在簡單語句中埋入強烈情感張力:「天空沒有足夠的傷心/只是就這樣/屎臉一整天」、「好險/是一個/被洗壞了也沒關係的人」,這些語句看似玩笑,卻有著深層的存在疲憊與身份焦慮。
又比如〈美好的早晨〉這首組詩,形式是多聲部合唱。由五段構成,每段皆以「⋯⋯一樣/美好的早晨」作為敘述骨架,從模仿長輩圖上的早安問候(長輩圖一樣/美好的早晨/所有的星星/一起解散)開始,逐步瓦解這份「美好」的假象。「美好早晨」連寫五回,其虛假慣性,遂成了反諷基調:這不是美好,而是被灌輸成美好的。
第一段「長輩圖」到二段「稀飯」、三段「行道樹落葉」,到底下四五兩段,詩人一層層拆解我們對早晨的浪漫投射:
4.
電視機雜訊一樣
美好的早晨
沙沙沙沙
沙沙
沙沙沙沙
是夢境裡
聽到的海潮聲
5.
摩托車冒的
黑煙一樣
美好的早晨
翻過一座山頭
再一座山頭就到了
那箱兩人書信
落海的地方
原本電視機應該是雜訊與故障,卻被許赫轉譯為浪漫的自然之聲。詩人揭露了一種「幻象機制」的必要性,如此生活中的不完美才有機會幻化成有意義的東西,否則日子會過不下去。而「摩托車黑煙」是早晨生活中非常「醜陋」的畫面,也被形容為「美好的」,且由「翻過山頭」「再一座山頭」的敘事性開展,從寫實跳進記憶與詩意。最後一句「那箱兩人書信落海的地方」是整首詩最浪漫的一筆,失去象徵著人與人聯繫的「那箱書信」,指出遺忘、或情感崩解乃人生必然,再多努力與奔波,重要的也終將沉沒。「條紋公路」終將落入「平滑海洋」是必然之道。
許赫讓我們看見:我們之所以都是「洞穴人」,看不到許多「美好」都是「假象」,皆因「我們都是可以被格式化的」,而我們可能正活在那些格式裡。如此,「瓦解條紋」以「游入平滑」,看清世界真相,卻又能出以日常語言的詩形式,這即是許赫「告別好詩」、提倡「人人可玩詩」、寫「壞詩」一樣有樂趣、以符應「庶民日子」,卻又能導演出一幕幕輕鬆的「許赫詩劇場」的初衷吧。
導讀
這本詩集傳遞的不是宏大敘事,也不是標榜激烈情感的抒發,而是一種在日常的生活裡找尋自己位置的能力。
垃圾車的聲音是每個城市幾乎都會聽見的東西,它意味著重複、機械、生活的背景音,但在詩人許赫筆下,卻是提醒人「你還活著」、「你還有明天要處理的事情」的訊號。
詩人許赫並不急著給你答案。他寫一隻貓、寫人與人之間小小的誤會、寫下班回家的鞋、寫朋友的訊息未回——這些看似瑣碎的元素,在詩中形成一種溫柔但真實的對照:
我們所說的「生活」,其實就是這些小事堆疊起來的認真與荒謬。
在許赫詩的世界,不需要你具備詩學知識,也不需要你對文學懷有崇高敬意。你只需要願意對自己稍微誠實一點,對世界稍微敏感一點。
當你讀他的詩,你會發現:
• 原來自己也曾在垃圾車的聲音中想起某個失聯的朋友。
• 原來「買一杯手搖飲」也能成為一首詩的主題。
• 原來孤單不是要哭,而是靜靜坐在沙發上等手機亮起來。
你會慢慢發現,許赫寫的不是他自己的生活,而是「如果你夠誠實,你也會寫出來的那種生活」。
他讓你知道:
詩不是要讓你逃離生活,而是讓你看清生活的細節,然後繼續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