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移去國際了解的魔障
許倬雲
最近讀到德國學者尤根.歐斯特哈默的《亞洲去魔化:歐洲與十八世紀的亞洲帝國》,引發了長期困擾心思的問題,亦即所謂東方與西方之間,究竟該如何相對?學歷史的人本來就逃不開這一問題的糾纏,只是近幾年來西方霸權的專橫,表現於中東的衝突,而「東方」繼日本及東亞四小龍之後,中國與印度的急劇發展,無時不迫人思索:那些恩恩怨怨如何方能解開!
不同文化認知有蔽有偏
歐氏顯然也是從他研究漢學的經驗,不得不在此時再度思考歐洲人士對於東方的認知,及其演變歷程。他將歐洲與「亞洲」做為對立的雙方,其主要論述是在於歐洲建構「自己」時,實係以所謂「亞洲」為其對比的「他者」。於是,歐洲是一個囫圇的觀念,亞洲也是一個囫圇的觀念。歐氏此書討論的時段是十九世紀。不過他特別說明,他所關注的時代,是一六八○─一八三○年間,那首尾均有延伸的十八世紀。在那一百多年內,歐亞內部均有重大的變化,而歐洲人對於東方的理解,也前恭後倨,從近於盲目的崇拜,逐步發展為「彼可輕易取之」的蔑視。果然,接下去,即是歐洲人對於東方世界的步步進逼,巧取豪奪,終於實質上奴役東方,至今又已是一個世紀了。
歐氏此書,是今日後現代的解析,尋找歐洲人不同世代對於東方世界不同的認識,指陳歷史上歐洲人收集的東方知識,其性質各有特色,而這些特色往往又根源於當時歐洲人自己的獨特視角。其實,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認知,無時無刻不是由「自己」看「他者」,都有所蔽,有所偏。歐氏書名是有關亞洲的去魔化,實則,今天是二十一世紀了,歐美文化系統的人士,對於世界人類的其他部分,又何嘗不是還在此時自設的迷霧之中?解迷去魔,談何容易?歐氏陳述十九世紀歐洲對於亞洲的解迷,又何嘗不可解讀為我們這一時代,依舊還須不斷解迷破魅?若不是還在迷惘之中,小布希也就不會陷入中東泥淖,而還不悔悟了。
中國早期也受魔障附身
歐美文化系統人士,對於「東方」最大的迷障,即是以「亞洲」為「東方」,籠統的當作自己的「他者」,而建構了一個自己為中心的虛幻世界,這一心障與智障,在中國自己的歷史上,又何嘗不存在?
中國文化在史前時期,多元共存,到了春秋還是南北東西,各有異同。秦滅六國,政治上統一,漢重儒家,思想也定於一尊。自此以後,中國文化在東亞的龍頭地位,四鄰不能挑戰,也因此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文化,不免自負;用今日的名詞,中國人的文化沙文主義,遂成為附身的魔咒,歷久不能自拔!二千年來中國難得以平等觀念處理涉外事務,不是自大,即是屈服。由於這一重魔障,中國在大洋航運開拓以後,即使民間力量已經參與國際海上活動,文化精英及政府官僚卻懵然不知世界已經開始的巨變。自此以後,西潮東來,而中國呢?先則有乾隆對於英國使團的自大,繼而有鴉片戰爭的昏聵慌亂,終於則是義和團代表的愚昧荒唐。最後,中國又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彎,由自大而自卑,「重洋媚外」之風,從清末延續至今。
西方開始正視東西差異
不僅中國,日本又何嘗沒有附身的魔障?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是西方文化的優等生,從裡到外一切模仿歐美,以致比西方帝國主義更為帝國主義,成為東方世界的禍害。
回頭看看,日本的維新,中國的洋務,甚至五四運動,東方對於西方文化,只是照單全收,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終究只是未落實際的口號。明治與五四人物,似乎都未認真省視西方文化演變的線索,於是在輸入西方文化時,也很少推敲其中必然與偶然的因素,以致始終欠缺了深度闡釋與由此而進行的鎔鑄。
現在,正如歐斯特哈默諸人所做,西方人士已在省察自己的文化與「他者」之間的互動了,新近故世的薩依德曾提出「東方主義」一詞,陳述「東方」實由「西方」的立場界定,自薩氏以來,從地中海東岸到太平洋濱,這廣大的「東方」地區,學術界與文化界還是很沈默,至今未見從省察自己與省察「他者」往返映照,庶幾真切的認識自己,也認識別人。
消弭誤解化解東西衝突
畢竟,全球性的經濟正在成形,在二十一世紀「西方」與「東方」必然會合,吉柏林「東是東,西是西,兩者永遠不會交集」的詩句,終將證明為錯誤的自負。我們不願看到目前兩河流域與波斯灣─紅海地區的災難擴及於世界別處。基督教與回教之間長期的誤解及由此發生的衝突,再加上石油能源惹起的貪念,都導致今日全世界恐怖活動與暴力侵略的災難。我們若不早做努力從根本消弭「西方」與東亞∕太平洋地區之間彼此的誤解,則杭廷頓文化大衝突的預言,也將會不幸而言中。
這一深刻省察自己與「他者」之間認知差異的工作,當是全世界知識分子的共同志業。西方已有人著手了,我們呢?我們是不是也該開始想想了!
推薦序
新世界與老亞洲
楊照
十五、十六世紀在西方興起的大航海浪潮,是歷史上的關鍵轉捩點。大航海的冒險探索,才讓原本各自獨立發展,僅有零星、偶然交會的文明,彼此認識、彼此衝擊,才誕生了一個以全地球為領域的「世界」新概念。
大航海時代真正驚人處,不在其冒險探索所發現的,毋寧在遠赴全洋冒險這個意念衝動上。人的肉體存在,從來不是為海洋生活所設計的。航海技術上的突破,不足以改變一項事實:長程遠航,極其折磨,而且時時處處佈滿了死亡陷阱。
離開熟悉、溫暖的土地家園,擠進髒臭狹窄的航艙,朝根本不知什麼何處航去,有道理嗎?奇怪的,十五、十六世紀,歐洲許多人竟然視之為生命最大的意義所在!
大航海時代之所以可能,依賴當時歐洲人對陌生事物的好奇。從未到過的地方,從未看過的景色,從未想像過的動植物,比安穩的土地,對他們產生了更大的吸引力,才使得他們前仆後繼願意為未知賭上一切。
可以這樣說:大航海必須以歐洲自身知識系統的動搖,為其前提。在穩定的知識系統中,人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生活所需的一切答案,當然就不會對陌生事物好奇,甚至不會假想假設陌生事物的存在。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出發航向完全未明的水域?
中國就是長期籠罩在穩定的知識系統中,因而不可能與海洋、海洋的另一端,發生什麼關係。中國自給自足的知識關懷中,容不下「彼岸」的想像。看不見的東西不屬於這個知識系統,也就不需、不能思考,當然也就不可能好奇、想望。
從十六世紀起,大航海陸續帶回來的海洋「彼岸」訊息,進一步動搖、乃至改造了西方知識。原本出於冒險、傳教與財物掠奪動機的航行,很快就多增加了一條理由──為了知識的擴張。
於是航行除了原本牽涉的商業資本家、水手和傳教士之外,多加了一種必要角色──博物學家。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遠洋船隻隨船帶著博物學家,幾成慣例。
博物學家帶回來令人看得瞠目結舌的奇特動植礦物標本。他們同時也帶回來令人聽得目瞪口呆的遠方故事,關於那些無法任由他們捕捉、風乾帶回家的,人與社會的故事。
那是一個驚訝發現異種、異俗、異語、異文明的熱鬧時代。較為科學的客觀描述、理解方法,還來不及建立起來之前,一個豐富而有趣的「輕信」時代。
翻看那個時代航海博物家帶回的異文明紀錄,最凸出的特色,必然是其光怪陸離。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戲仿航海家紀錄,寫了《格列佛遊記》,裡面有小人國、大人國,還有以馬為人的國度。史威夫特固然誇大了海外存在國度的奇貌,不過讓我們別忘了,本來航海誌裡就充滿了各種常識上不可能,航海者卻堅稱自己親見親歷的怪事怪物。
為什麼航海者帶回來的故事,都那麼怪?今天透過異文明歷史的比對,我們有把握明確地說:那些光怪陸離,不管是航海者看到的印加帝國、日本或大溪地,幾乎都不是事實。他們不見得是刻意捏造,而是一股要在海洋彼端看到「異物」的預期,扭曲了他們的經驗,使他們成為不忠實、不可信的觀察者、感受者。
航海博物家先入為主要找到「異物」,也就意謂著他們帶著清楚的歐洲標準,來搜尋海洋彼端的印象。「異」者,異於歐洲既有的事物。尋找「異物」的人,敏銳地看到的、不自覺誇大的,一定是和歐洲「一般」、「平常」不同的現象。
所以,那些光怪陸離的異物記載,與其說是關於印加帝國、日本或大溪地,還不如當做是歐洲人流浪心靈中,以彼岸經驗刺激出的華麗想像,與歐洲既有知識經驗主流,不斷辨證對話的結果。
原本就是出於知識系統的不安,才有大航海創舉,進而大航海帶回來的「異物」訊息,又不停地搖晃著歐洲一般人賴以生存的世界觀。
那兩三百年,歐洲經歷了知識系統的大破大立大重建,而這知識系統上進行的變化,正就是分隔開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最鮮明的分水嶺。
有趣的知識系統變動,發生在十八世紀。對待大航海時代中找到的「彼端」,十八世紀開始試圖不只是記錄其怪模怪樣傳奇,而是去進行理解。十八世紀也開始收拾原來不同船隻不同航程不同人搜羅到的片段,試圖建立起系統來。更重要的,十八世紀歐洲人看見海洋「彼端」的企圖動機,慢慢從主觀中走出來,試圖找出一套客觀方法論來。
主客異變之間,而有了極其豐富的內容。與前面的時代相比,十八世紀歐洲的異文化知識,不再那麼狂野放任,充滿了自我中心的想像,轉而浮現了一點秩序,尤其是浮現了一點想要參與貢獻這個領域裡的人,不得不遵守的規範。不過和後來的十九世紀相比,十八世紀卻又還沒有明確的社會制度管轄這套異文化知識的產製、流傳與評價,也就是說,異文化知識尚未「專業化」、「體制化」,尤其尚未與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合為一體,而有著較大的個人、學派特色空間。
在歐洲人的異文化想像到異文化理解中,亞洲當然佔有重要地位。早在大航海開拓前,歐洲已有對亞洲的模糊傳說,而且已經認知亞洲有著和歐洲一樣高度發展的文明,和非洲或美洲,情況大不相同。
歐洲人或誇張對亞洲文明成就的「驚艷」,或誇張對亞洲「原來不過如此」的失望幻滅,在這兩種極端態度間的取捨,往往不是決定於亞洲是什麼,而在歐洲本身需要什麼。
亞洲比其他地區,更關鍵地扮演了這段時期歐洲建構自我形象的對照角色。當歐洲需要新的文明標準以砥礪自己奮起時,他們便抬高亞洲的成就;反過來當他們需要鼓舞具侵略性的自信心時,他們便不客氣地貶抑亞洲。亞洲知識亞洲印象,被不斷拋擲、搓捏,進行無窮變形。
「亞洲去魔化」整理的,就是十八世紀知識系統大變動中,歐洲人如何與亞洲知識、亞洲印象糾?的過程。這裡面固然有逐漸累積增加的亞洲經驗,同時卻有更多歐洲本身快速變動的矛盾衝突。透過歐洲人的眼光,我們可以部份復原十八世紀亞洲的相貌,不過,看得最真確的,畢竟還是歐洲眼珠光影中幻映出來他們自我的形影吧!
「亞洲去魔化」給了我們豐富的資料,深入十八世紀歐洲知識世界裡。我們不必也不能將當時歐洲的知識,視為亞洲寫真。不過倒是可以回頭藉此對亞洲自我歷史認知與歐洲的想像建構,對這段西方逐步凌駕東方的過程,有更深入更細膩的掌握。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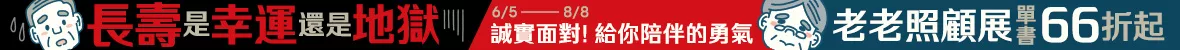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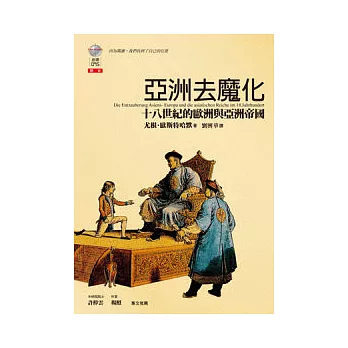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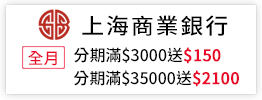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