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重現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間那座天橋
此卷寫作於十多年前。當時是企圖開解縈繞心中的一些困惑。我在《中國抒情傳統》一書的序言中曾說:中國抒情傳統不僅是中國文學的道統,而且是一種超越抒情詩文類的、持續而廣泛的文化現象。我這一觀點的根據,是概述前輩學者高友工教授的學術思想,包括其本人以下一段文字:
這個觀念(抒情傳統)不只是專指某一詩體,文體,也不限於某一種主題、題素。廣義的定義涵蓋了整個文化史中某一些人(可能同屬一背景、階層、社會、時代)的「意識形態」,包括他們的「價值」、「理想」,以及他們具體表現這種「意識」的方式。
雖然在這一段文字以下,高友工指出:理論上抒情傳統是源於一種哲學觀點,即肯定生命價值之在於個人具體的「心境」。但高氏並未對他所說的「理想」「意識形態」作出解釋。或許多數學者都會首肯高先生的觀點,但此觀點本身卻是未經證明的。縱然二十世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已證明了許多重要詩人如杜甫、李白和王維的創作確受傳統儒道釋思想沾溉,而古代文論研究,如對曹丕的研究、對劉勰的研究、對司空圖的研究,更進一步證明了中國思想中的元氣說、儒學、玄學和佛教諸觀念實參融於中國詩學,但這一切尚不足以證實:中國抒情傳統作為中國文化的主脈之一,乃一對應傳統「意識形態」、「理想」和「價值體系」的大傳統。因為上述詩人和論詩者本人均並非哲學思想家。而哲學思想家如孔子、朱熹雖然偶或也會談到詩,卻究竟未對整個詩歌傳統作過理論追問。近年來出版的一些對中國文學藝術作全景式考察的學術著作,如韓林德的《境生象外:華夏審美與藝術特徵考察》、朱良志的《中國藝術的生命精神》 等等,都是將中國詩學、文藝學和潛美學放置在中國思想的框架中加以審視和把握,其中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筆者決無意否定。然而,由於這些著作是在跨時代、跨文類、甚或跨越領域的視野之下展開,而這種種跨越之間的聯繫又是出自今人思維的構建,在最終的追問裡,也許都免不了用「思辯」作為結論的依據,雖然這種思辯的結論可能不誤。但 「思辯」(speculation)在學術傳統中本非褒義。在上述將中國詩學放置在傳統思想框架中加以透察的著作中,不應忘記一部英文著作——美國當代這方面最具影響的學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傳統中國詩歌與詩學:世界之徵兆》(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此書在討論對仗和中國詩歌的結構法則等問題時,即從中國文化「非創造的宇宙」諸觀念著眼。在該書的兩篇序言中,作者皆坦言:跨越不同文明、及文學歷史時間之間的障礙去重建失去的閱讀規則,以推論(inference)和猜測(guess)進行的思辯方式是必要的條件,因為他本來就被置身於能作確切斷言者的疆域之外。作者在序言最後以如下一個比喻對讀者說:
我在一間沒有窗戶的,愈見幽暗的房間裡。你從一個隱藏的麥克風諦聽。有人在鄰近的房間通過牆壁上的小孔對我講話。在聲音之外,我無從證實他的存在。我不斷地督促他回應,但那聲音只當它願意時,只在無從期待的間隔中才傳過來。我能設想我聽到的可能只是個人幻覺,然而當聲音傳來時,憑借其個性及所談論的事情,我認識到那聲音屬於他人。因為我不會談論這些事情。我說過我能設想我或被欺蒙,但你作為偷聽者,卻不會被欺蒙。
宇文氏在此表達了在被時間和不同文明的牆壁分隔而作理論判斷時的困難。這應該包括連結中國思想和中國詩學的那些聲音,它也「只當願意時,只在無從期待的間隔中才傳過來」,而且更其微弱,更使人難以判斷:那究竟是否只是我們「個人的幻覺」?作為本文化的研究者,我們其實只比宇文氏幸運一點點,畢竟也被時間和文學史的牆壁與古人隔絕了。正如宇文氏所說,我們也無法再期求古人對我們解說,而只能被動地聽上一兩句。這對重建中國詩學和思想哲學之間的聯繫來說,也恰如暗室拾音,盲人摸象。除非我們能找到一位古人,他站在另一間房間裡,卻在談論與我們相似的主題。真能如此,經分析他的話,我們就能使上述關於抒情傳統和傳統「意識形態」、「理想」和「價值體系」之間的討論超越思辯和推測,成為嚴格邏輯意義上的證明。
而在中國文化史上,恰恰有這樣一位大哲。其學遠祧孔孟,近宗張橫渠,於儒家經典皆有發明,且廣涉佛老莊學。於詩,亦縱攬古今,自詩經、楚辭、漢魏六朝三唐兩宋詩以至明人歌詠,各體之作皆有評騭。以視域之開闊,品藝之精微,論風之痛快淩厲而言,在中國文論史上,亦屬罕見。此人就是生活於明清鼎革之際的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船山。在中國文化史上,他或許是集大哲學家與大文論家於一身的孤例。對於其詩學和哲學思想關係之究詰,當可使今人關於中國抒情傳統的探討進入哲學層次之時,庶可免去純粹的「思辯」和「揣測」。
然而,反觀多年以來今人關於船山詩學的研究,包括本人八十年代初發表的這一方面的論文,卻普遍存在著將其詩學與其經學、子學割裂的現象。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二端:首先是在中國文論史上,如亞歷士多德、叔本華和尼采那樣能一身而兼為大文論家和大哲學家的人物,船山是絕無僅有者,研究者容易忽略其特殊性。其次,船山在上述兩個領域的著述都堪稱卷帙浩繁,綜合研究的難度較大。然而,這種割裂式的研究不僅使對於其詩學許多範疇的界定,失去了參指依據,更犧牲了上述船山詩學對探索中國抒情傳統的獨一無二的的價值。本書的寫作,首先是為補償過去的過失。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曾就船山詩學發表過一些論文,雖然是由中國大陸最權威的學術刊物刊出,然而,囿於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本人學養、視野,這些文字今天是令作者赧汗的。從學界而言,這無疑說明了近二十年間的進步,然對個人而言,卻在心中成為難以揮去的愧怍。由於這些文字中的失誤,我亦成為學界若干謬論的始作俑者,實有糾正之責任。所以讀者在本書各篇中都能讀到作者對過去的反省。這種反省,有時又超越個人,成為對作者身歷其中、且有無窮瓜葛的學界若干普遍觀念的反省。具體地說,討論「現量」一篇對時下以文藝心理學為框架解釋「情景交融」作了反省。論船山詩學與天人之學關聯兩篇提出在理學性命哲學和生機說易學背景下「情景交融」說的「語義」和「語法」的問題。論「勢」一篇質疑了「意境」是否中國抒情詩歌中心審美範疇的觀點。論「興觀群怨」一篇指出了以伽德瑪詮釋觀念比附船山觀念之不當,並提出船山對抒情傳統本體意識的修正問題。論詩樂關係一篇與論「勢」一篇呼應,從宏觀詩學史的立場重新檢視明代以樂論詩的意義,以及中國抒情詩的時間藝術的本質。論內聖與船山詩學理想一篇正視了船山對宋明理學的承緒,並質疑了因尚「和」遂以「優美」一類西方美學範疇界定中國傳統詩學之謬論。上述反省和批判涉及的均為有關中國詩學最重要的理論問題。僅此已說明了船山學對理解中國抒情傳統何等重要。必須說明的是:雖然就哲學思想和詩學的直接聯繫的全景而言,船山學幾乎是惟一的標本;然而從中國詩學的縱向發展而言,它又主要代表了思想史中宋明理學和詩學的關聯。故而,從歷時性而言,它又不是全景的,而是局部的。玄學和佛學映照下的傳統同樣不可忽略。但船山在易學背景之下論詩強調「勢」和以樂為詩之極詣,卻給了筆者這樣的啟示:抒情傳統在佛教散播之際,料必在形態上和觀念上有過一番嬗變。全面地描述中國抒情傳統,則必須重建佛學佛學的誤解)與抒情傳統之間的關係,雖然不再可能找到類似船山學這樣一個思想與詩學之間全面而直接的標本了。但船山學的研究卻給筆者指出了以後的工作方向。所以在此後,我又完成了現此書中第二卷的《佛法與詩境》。而後者的寫作,又令我感到有必要於魏晉玄學和詩學的互涉中發現抒情傳統一些早期觀念的淵源,這又推動了現本書第一卷《玄智與詩興》的寫作。所以,本卷的寫作其實是一個歷時十餘年學術艱苦探索的起點。
從一種意義上,本卷的寫作又是為了完成一個提出了卻未能充分證明的論題。我在二零零一年由美國密執根大學出版的有關《紅樓夢》的著作(The Chines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曾以這部名著討論中國抒情傳統於古代社會晚期的式微,其中提出:抒情傳統乃以審美理想重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終極信念。但對這樣一個重要命題的全面論證,卻不可能在那本書中展開,而必須在解答了中國詩學和思想之間的種種聯繫之後方能完成。換言之,研究船山思想這一理論標本或許提供了一個論證此論題的直捷方式。我在本卷的最後一篇的後面部分點明了這一點,那一段話可視為這一論證的結穴:
[船山詩學] 處處體現了中國文化「有機」(organistic)宇宙觀念﹕即宇宙秩序呈人類藝術的「音樂的」形式,承載著人類價值,善與美;而人類藝術則在節奏上「重義地」體認出宇宙生命。筆者堅持認為﹕這才是不為宗教意識統攝的中國文化中超越儒家政治理想的終極信念,亦是此文化光輝標誌抒情傳統之審美理想。作為藝術理論,船山詩學或許是上述信念的最完整、最透徹的表達。它處處欲詩人「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如筆者在本系列其他文章中指出,船山以樂論詩,不僅標舉「樂與天地同德」,且更欲彰顯心「因天機之固有而時出以與物相應」;船山詩學 中「勢」這一概念,則旨在彰顯詩與宇宙事物之間通感(synaesthetic)意義上的共同節律或「宇宙和弦」,而任何時間上第二義的、形貌上的「再造」 或「摹仿」, 將使詩人永難擺脫 「迎隨之非道」的困惑;船山詩學中情景在 「語法」意義上之與乾坤、 陰陽這些符號範疇對應,則潛在地肯認了人所參贊之天地化育與道體所開展之世界必歸攝於一;而船山以「現量」界定詩人的審美體驗,其真正的理據是李約瑟所說的天人之間的「象徵的互應系統」。即使船山討論作者-文本-讀者關係的概念的「興觀群怨」理論,在至少三位英文作者看來,亦不無體現宇宙動態生命的意味。
由這段話看,本卷的寫作是圍繞一個大的論題而進行的。的確有這樣一個初衷。作者開始這個研究時,曾大致列出了七、八個論題,對其中的關聯也有過某些考慮。但我所工作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很難有較長的時間寫作大部頭的著作。為完成這種需恢宏視野的論題,只得取先分割包圍再最後決勝之策略。所以,各篇實際上是在兩年多時間裡分別陸續完成的。最後又斟酌各方意見,以兩、三個月時間作出修改和統稿。並增加或修改了原篇章的副標題以凸顯船山詩學揭示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關聯的特殊意義。最費周章的是由各篇順序體現的全書結構。按寫作的先後順序排列的想法先被否決,因為無從體現船山詩學本身的架構。而任何基於現代理論概念的「結構」都與本書的宗旨不符。最後的決定是基於船山詩學的內在思路去建構。我在研究時發現:船山論詩的最重要著作《夕堂永日緒論內編》由序言至前五條的次序並不苟然,乃取逐漸壓縮命題規模的邏輯。現在本書作為其詩學之詮解,乃根據閱讀循創作逆過程的原理,由船山邏輯展衍的終端反溯回其啟端,即取逐漸擴張命題的邏輯。根據這一想法,各篇的內容依次為:有關取景之現量──體現詩人創作瞬間際遇的情景交融──詩意在文體中開顯的勢──關乎世界、詩人、文本和讀者關係的興觀群怨──關乎詩的終極義的詩樂關係論。而在各章之前,我又增加一篇從宋明儒學發展的縱向角度去總結的篇章,以增強全卷可能被淡化的歷史意識,以與本書第一、二卷連接。此又兼為論證抒情傳統重述中國傳統文化之終極信念這一論題的完成。但願這樣一種安排能令讀者透過雲林森緲、重睹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間那座天橋。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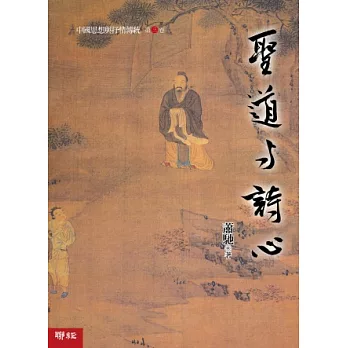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