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命該遇到這個時代。──莎士比亞《辛白林》
作者前言
我從不這樣看重自己,覺得非要向別人述說自己的經歷不可。在我鼓起勇氣寫這本以自己為主角──或者更確切地說,以自己為中心的書之前,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災難和考驗,都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我個人根本沒有資格站在舞台上,我只是扮演幻燈報告的解說員,時代給出畫面,我只是為它們做注解。而且,我?述的並非只是我個人的命運,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運──我們這代人遭遇了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磨難。我們中間的每個人,包括最年幼和最無足輕重的人,在內心深處都被歐洲大陸上連續不斷如火山爆發般的動盪所震撼。在無以數計的人群當中,我知道自己最有發言權,因為我是奧地利人、猶太人、作家、人道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而且,我恰恰站在地震的中心。那些震盪三次毀滅我的家園和生活,使我變得一無所有,它們用戲劇性的動盪將我拋入一種我已經太熟悉的虛空之中──「我不知該何去何從」。但是,我毫無怨言,正是因為無家可歸,我獲得了一種新的意義上的自由,正是因為一無所有,我便無所羈絆了。因此,我希望自己至少能具備如實描繪歷史的兩個基本條件:公正和不抱偏見。
我脫離了所有的根源,甚至脫離了滋養這些根源的土地──我確實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例子。1881年,我誕生在一個強大的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在地圖上,人們已經找不到它了,它的蹤影已經被抹的乾乾淨淨。我在維也納長大,這是個具有兩千年歷史的國際大都市。後來,我被迫像罪犯一樣離開了它,它隨之也被降格為德意志的一個省城。我的書曾和成千上萬的讀者為伴,而同樣在這個國家,我用母語寫就的文學作品在那裡已付之一炬。因此,我不屬於任何地方了,在世界各地我只是一個陌生人,頂多也只是過客罷了。歐洲──我心所屬的真正故鄉,自從它第二次同室操戈,開始自相殘殺時,我便也失去了它。我無奈地見證了有史以來理智所遭遇的最慘痛的失敗和野蠻獲得的最瘋狂的勝利。從未有人像我們這一代人從精神的高處墜落,而道德如此倒退──指出這點時,我毫無得意之情,卻深感羞恥。當我從乳臭未乾的少年變成兩鬢斑白的老人時,短短半個世紀內發生的變遷遠遠超過十代人所經歷的,我們都感覺到,變化太多,太大了!我的今日與昨日是那麼的不同,我的得意與失意相差是那麼大,有時我覺得自己不僅僅在過一種生活,而是過了許多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當我無心說出「我的生活」這個詞的時候,常常會不自覺地問自己:「你指的是哪個生活?」是指一戰前的?二戰前的?還是今天的?同樣,當我說出「我的家」時,卻不知道自己指的是哪個家,是巴斯的那個家?薩爾茨堡的那個家?還是維也納的老家?當我說「在我們國家」時,會吃驚地想起自己早就不見容於家鄉了,就像個英國人或美國人一樣,我已經不是那裡的一員。我與故土已無任何基本的聯繫,而在此地,又從未真正融入。我在其中成長的世界和如今身處的世界,以及兩者之間的世界,它們在我的心目中越來越不一樣,最後終於成了截然不同的世界。每當與年輕朋友談及一戰以前的時光,總是從他們驚訝的問話中發現,有多少事對我而言,依舊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但對他們而言,卻已成歷史,或是不可思議了。在我內心有種秘密的直覺告訴自己,他們是對的。聯繫我和他們的今天、昨天與前天的橋樑已經全都斷了。連我自己也不得不感到驚異,當年我們竟然把那樣繁多豐富的內容壓縮在一代人短促的生活之中──當然,這是一種無比艱難和遭逢傷害的生活。當我拿它和祖先的生活相比較時,這種感觸就更深了。我的父親、祖父,他們都經歷了什麼呢?他們的生活都只有一種形式。自始至終,他們只過了一種生活,沒有大起大落,沒有震盪和危險,只有輕微的激動、毫不起眼的變化,節奏平穩寧靜,時間的波浪將他們從搖籃帶進墳墓。他們一生住在一個國家、一座城市,甚至一棟屋子裡,外面世界所發生的一切,說實在的,只存在於報紙,並不會碰觸到他們的家門。在他們那時候,可能在什麼地方也有過什麼戰爭,但用今天的標準來看,那只是小陣仗,只在遙遠的邊境上進行。人們聽不見大炮轟鳴,半年之後,也就風平浪靜,被人們遺忘了,然後成為一頁枯萎的歷史,原先一成不變的生活仍在繼續。而我們所過的生活根本不會重複,已逝去的一切再不復返,這一代人充分地經歷了過往歷史有分寸地落在一個國家、一個世紀的一切。以往,這代人經歷革命,下代人經歷暴亂,第三代經歷戰爭,第四代經歷饑荒,第五代經歷國家經濟的崩潰──而有些幸運的國家和時代甚至不會有任何以上的遭遇。可是我們,今日已六十多歲的這代人,還有幾天可活的這代人,我們什麼沒見識過,什麼罪沒受過,什麼沒經歷過?所有可以想到的災難,我們都一一飽嘗(而且沒有盡頭)。我自己就經歷了人類兩次最大的戰爭,而且,兩次還是不同的戰線,第一次是在德國前線,第二次卻是在反德國的前線。戰前我曾目睹個人自由的最高形式,接著又看到百年來它遭遇的最差狀態。我曾受到稱頌,又遭到貶低,我曾自由和喪失自由,我曾富有,然後貧窮。「世界末日」那幅畫中,代表革命、饑荒、貨幣貶值、恐怖、瘟疫、流亡的蒼白馬匹全都闖入並橫掃了我的生活。我親眼目睹群眾思潮的產生和蔓延,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及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尤其是那瘟疫般的國家社會主義,毒害了我們歐洲的文化之花。我成了手無寸鐵的見證人,面對人類不可想像的倒退卻無能為力。人類以反人道的教條有意識有計劃地退回到早已被遺忘的野蠻狀態。這使我們在幾百年後又見到了不宣而戰的戰爭、集中營、嚴刑、搶劫和對無抵抗力城市的轟炸。這一切都是我們以前五十代的人未曾見識過的,也但願我們的後人再也不會容忍這些。在這個時代,我目睹了世界的道德倒退了千年,矛盾的是,同樣也就是這個時代,這些人,在科技和智力上獲得未曾預料的進步,猛地超越了以往幾百萬年的所有成就:人類用飛機征服了太空,人類的語言一秒鐘就能傳遍整個地球,人類因此征服了空間距離,原子的裂變戰勝了最兇險的疾病,人類幾乎每天都在實現昨日還不可能實現的事。在此之前,作為整體的人類,還從未露出如此猙獰的面目,也從未做出如此令人驚歎的偉業。
我覺得,見證這種充滿戲劇性與令人驚愕的生活,是我的義務。因為,──我再重複一遍──每個人都是這種巨大轉變的見證人,每個人都迫不得已成了見證人。對於我們這一代人而言,沒有任何逃避的可能,我們無法像前人那樣置身事外。由於這個時代的同步性,使得我們始終被時代拖著走。如果上海的房屋遭到轟炸,在受傷的人被抬出房屋之前,歐洲的我們在自己的房間裡就已得知了。發生在幾千海里以外的事,很快就會印成圖片生動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沒有什麼可以躲避和抵擋這種不斷的溝通和介入,人們無處逃遁,也買不到任何安寧,命運之手每時每刻、隨時隨地將我們攫獲,把我們拽回到它永不饜足的戲弄中去。
人們必須不斷服從國家的意志,甘願充當最愚蠢的政治犧牲品,適應最離奇的變化,個人的命運永遠與人類整體的命運相連,儘管他極力反抗,共同的命運那還是把他拉扯進去,不容抗拒。一個徹底經歷了這個時代的人,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被驅趕追逐的人──我們沒有什麼喘息的機會──比他任何一位祖先都有更多的閱歷。即使今日,我們依然處在一個轉捩點上,處在一個結束與新起點之上。因此,我有意用一個固定的日期讓自己的生平回顧暫時告一段落,1939年9月的一天,造就了六十幾歲的這代人的時代結束了。假如我們的見證能讓下一代的人對那個分崩離析的時代哪怕有一星半點的認識,也算沒有虛度年華了。
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寫下這些回憶的情境,雖然極端艱難,卻也最能代表我們這個時代。我流落異鄉,手邊沒有任何有助回憶的參考,在戰爭中,我寫下了這些文字。旅館客房裡,我沒有自己的任何著作,筆記,和友人的信件。我與世隔絕,全世界的郵遞全部中斷,或因為檢查而遭到阻礙。我們每個人都像幾百年前沒有輪船、火車、飛機和郵電那樣孤絕地生活著。關於從前的一切,我都只是依憑著腦子裡的回憶。其餘一切,在這時對我而言都遙不可及,或者都已經失去了。不過,我們這代人已經徹底學會不去緬懷業已失去的東西,也許,文獻和細節的缺漏正是我這本書的可貴之處呢。因為,我不認為記憶只是偶然地記住此事,偶然地忘卻彼事,記憶實則是一種用理性整理和刪除的能力。在一個人的生活中被忘卻的一切,實際早已被他的內在直覺判定,它們必須被忘卻。只有自己想保留的一切,才要求為他人保留下來。因此,你們替我說吧,替我選擇吧,我的記憶!在我的生命遁入黑暗之前,至少將它映亮一回!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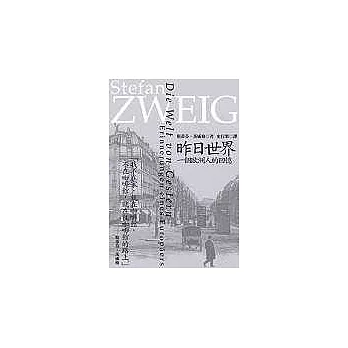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