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看哪,星星在說話 胡晴舫
「我呼吸過遠洋的風,我在唇梢嚐過大海的味道。只要品嚐過那個滋味,就永遠不可能把它忘記。我熱愛的不是危險。我知道我熱愛什麼:我熱愛生命。」──《風沙星辰》
如果你曾經幸運,有機會在一艘飄蕩在外海的船上過夜,周圍看不見一丁點陸地的影子,月光替代了太陽,整片海洋閃亮光滑宛如白銀打造的地板,躺在甲板上仰望浩瀚夜空,繁星密密麻麻,比任何城市街道燈光更叫人眼花繚亂;或是登高山岳往下鳥瞰,下頭沒有山谷也沒有河流,只有望不見盡頭的原野,平時遭房屋、森木、山脈遮蔽了原貌的大地罕見地顯露了她的漂亮圓弧線,像嬰兒後腦勺,曝曬在夏日豔陽下,遠方吹來的微風聞上去有股萬年雪的冰涼;也或者,你只是在一架黑夜中趕路的商用飛機上,跟著其他兩百名旅客飛越極地上空,當其他旅客或沉睡於夢鄉、或沉浸於機上娛樂節目,坐在窗口的你往外眺望,天空與大地同等漆黑,雪白冰原卻不知從哪兒找來的光源,在一片看似深不見底的虛無中,兀自閃耀純潔的光芒。
也或者,你只是拖著疲憊身軀,如一隻微小螞蟻走在回家路上,抬頭看了一眼當夜的月亮,一瞬間,你便進入了安東尼・聖修伯里的世界。「他記得一種屬於遠洋的氣息,人類一旦感受過它,就永遠不可能忘懷。」(《風沙星辰》)
聖修伯里是一名飛行員。當飛機航行,他飄浮在空中,萬事萬物都離他有段距離,地面、房屋、樹木、高山、花園、海洋,他身在萬事萬物之中,卻無法隨手觸摸他們,而除了起降,他也要努力與萬事萬物保持距離,以免撞毀他手上正在操縱的飛行器。同時,為了不撞及萬事萬物,他事先偵測他們的存在,瞭解每條河流、每座山巒、每處農場以及牧羊人的移動範圍,遼闊大地蘊藏了各種豐富的細節,像一張充滿密碼的飛行圖,等待飛行員的探索。
而萬事萬物皆朝他發光,飛機跑道、港口燈塔、路燈、窗簾裡透出來的燭光、河面上的月光、星星、沙漠升起的篝火,每一道朝他投射過來的光,都是訊號,都是一顆星球,代表一個獨立完整的世界,皆在對他說話。他們對他表明身分,所以他會知道那是一座湖泊、城鎮、農場,一條河流還是一條披滿鱗片的細蛇,一顆遙遠的星辰,一隊沉默中穿越大漠的駱駝商旅,也或許是一艘孤零零等待天明的漁船。點點光亮,從宇宙深處,來自四面八方向他發出訊號:最近的,起碼要兩千呎,最遠的,必須旅行幾萬光年,才抵達他的瞳孔。最微弱的並不表示最不明亮,最明亮的也不代表最強大。飛行員將星光、月光、燈光、螢光、陽光各種光點盡收眼裡,飛行員不只觀賞,他在思索這些光的訊息,背後密碼的真正意義。
當蒼穹變幻多端,地貌廣闊無邊,各方光點都在眨眼,他是自由的,他哪裡都可以去,但是,自由的真諦究竟何在?當飛行員總在離開,奔往無羈的天空,那麼,那股他形容為比愛情更偉大、並不斷使他降落的地心引力又是什麼?
聖修伯里創作《小王子》時,人在紐約。之前他來過美國五次,在紐約,他已是家喻戶曉的法國傳奇人物,因為《風沙星辰》美國版的成功,因為他與機師友人基佑美(Guillaumet)共同駕駛當時世上最大的水上飛機,飛抵紐約長島,得到英雄式的盛大歡迎,雖然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他甚至住過曼哈頓一陣子。一九四〇年底,法國潰敗於德軍,維琪政府成立,聖修伯里經過長考,決定出走,與法國導演尚.雷諾瓦結伴而行,第六次來紐約,他的身分是流亡的異鄉人。
他的妻子康蘇艾蘿隔年也來紐約與他團聚,他們先搬進中央公園南大街,公寓太吵太熱,沒法工作,而後,康蘇艾蘿在長島找了一處僻靜宅院,聖修伯里看了房子驚訝地說:「我只是想要一間小屋,這是凡爾賽宮。」他在這間美侖美奐的「凡爾賽宮」開始創作《小王子》。二〇一四年初,美國紐約摩根圖書館展出他們收藏的《小王子》手稿時,也揭露了一點私密細節,聖修伯里時常逃出他的「凡爾賽宮」,午後去到他的紅粉知己希兒薇雅(Sylvia Hamilton)家裡,塗寫他的小王子。根據希兒薇雅的說法,《小王子》的狐狸角色便以她為雛形,她送給聖修伯里的拳師犬則是《小王子》故事中的老虎。
而故事中那朵令小王子牽掛的玫瑰,無疑地,是聖修伯里的妻子康蘇艾蘿。他們之間,愛得激烈,折磨得痛苦,根本沒法在一起,卻又難分難捨,而她依然是他生命中最重要也是獨一無二的玫瑰,「因為一個人一旦做出選擇,就會滿足於自己生活中的偶然,就會去愛自己的選擇,就會受制於偶然,一如愛情。」(夜間飛行)
關於小王子的原型,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他朋友的兒子,有人說是他在火車上看見的一張熟睡孩童臉孔,他寫在《風沙星辰》裡,「在微弱的夜燈下,我看到他的臉龐。啊,多可愛的一張臉!那對夫妻孕育出一顆鮮嫩欲滴的金色果實。從一群粗鄙不堪的人物之間,誕生了一個魅力與優雅的化身。我傾身凝視那滑嫩的額頭,那雙微微嘟起的嘴唇,我不禁心想,這是個小莫札特,這是個生命的美好承諾。」而像我一樣有機會閱讀《風沙星辰》、《夜間飛行》以及《小王子》等這三本書的讀者們,可能會得出與我相仿的結論,小王子就是聖修伯里本人的化身。
《小王子》故事簡單,文體純淨,作者親手繪製了美麗的插圖,長久以來,包括聖修伯里的美國出版商以及紐約友人都相信自己說服了聖修伯里寫了一本童書。然而,正如聖修伯里所說的,「所有大人都曾經是小朋友。(可是只有很少大人會記得這一點)」,我個人堅信這本書是寫給世上所有看出一頂平凡無奇的棕色帽子其實是蟒蛇正在消化一頭大象的人。
跟自認正經的大人解釋,《小王子》不是一本簡單漂亮的童書,很累。就像書中所講的,大人只相信數字。只要跟他們說,《小王子》是全世界翻譯最多語文排名第三的作品,共兩百五十種語言,而且票選公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第一名,他們才會接受這本薄薄小書的重量。
文學讀者將《風沙星辰》、《夜間飛行》與《小王子》三本一起讀,會讀出《小王子》故事看似簡易實則深刻的文學涵義,也看見了作者的生命歷程如何淬煉了他的寫作,他的思想如何像一塊外太空飛來的隕石,原本有棱有角,經過日月磨練,吸收天地精華,風吹雨淋,逐漸磨成一塊渾圓無瑕的玉石。「真正的完美不在於無需加入任何其他元素,而在於不再需要消除任何細節。」小王子一誕生,就完美無缺,只能解釋成來自別的星球,但,來到地球之前,小王子已經遊歷了無數星球。他的純真,不是因為他是「小」王子,有頭可愛金髮,風吹來時會如麥田波浪起伏,而是在閱歷了世界之後,依然願意謙卑地面對生命。
從動筆《南方郵航》(Courrier Sud)開始,一直到最後作品《小王子》,聖修伯里的作品幾乎都在法國境外完成。他的飛行帶他離開他的星球,他在其他星球眺望滿天星斗,尋找那顆屬於他的星星,上面有他的火山和玫瑰。他只有三座與他膝蓋同高的矮火山,但他天天疏通他們,打掃得乾乾淨淨。他只有一株玫瑰,但他細心灌溉她,每晚替她蓋上花罩,保護她不受風寒,除掉她身上的毛毛蟲,「傾聽她的自憐自艾、自吹自擂,有時甚至還靜靜聽著她的沉默無語。」他只有一顆比他自身大不了多少的星球,他仔細梳理,按時拔掉猴麵包樹的樹苗,避免猴麵包樹的樹根鑽透整座星球。有一天,他離開了,可是他每晚都仰望燦爛星空,思念他的玫瑰,擔心她只有四根刺,無法抵擋外界的侵略。
《小王子》一開始以作者在撒哈拉沙漠飛機失事經驗開始,《風沙星辰》對此次生死遭遇有第一手的詳細描述,而《夜間飛行》又以第三人稱敘述了他與其他飛行員的價值觀與人生信念。三本書描繪了一幅聖修伯里身處的世界的圖像,那不僅是一個由風沙星辰構成的自然世界,也是一個道德混亂、文明衝突的複雜時代。當他年輕時以郵航飛行員身分,穿越陌生山脈、沙漠,駐紮在對法國敵意很深的土地上,歐洲殖民帝國正在各地瓦解,歐洲本土即將陷入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而他的飛機卻帶他飛越所謂文明的邊界,看見一般人沒法看見的瑰麗山河以及奇風異俗。沙漠、星空、大海,人類一旦離開他熟悉的城市,就會明白他們的存在有多麼渺小。拜飛機之賜,聖修伯里學會了「從宇宙的規格衡量人類」,很快領悟到了「神秘的核心」,明白人類的文明「不過是脆弱的金箔,只消一片火山、一片新生的海洋,一陣沙塵風暴,即可加以泯滅。」(《風沙星辰》)
生活在沙漠中的日子,讓他懂得什麼叫真正的孤獨。「人並非因為青春在只有礦物質堆疊的風景裡消蝕而恐懼,而是感覺到離自己很遠的地方,整個世界正在老去。歲月的腳步不斷前進,而人卻在他鄉身不由己……大地的財富宛如沙丘的細沙,就這樣在指間流去。」(《風沙星辰》)
一九三五年他駕駛的飛機迷路,墜機於埃及沙漠外,他與他的機械師兩人只有半公升咖啡、四分之一升白葡萄酒,一點葡萄和幾顆柳橙,一些巧克力和一把餅乾,相當於一人一天份的液體。他們很快出現幻覺,看見海市蜃樓,直到身上一滴汗都流不出,第四天才讓一個恰巧路過的貝都因人用遊牧民族土法救了他們兩人。
一九三九年出版的《風沙星辰》,與同伴沙漠歷劫歸來的聖修伯里這麼寫著:「愛絕不是互相凝視,而是一起往相同方向凝視」,因為當一個人「飛越安地斯山時,他內心的人類誕生了──那是屬於他的真理」,「對人類而言,真理就是使他成為人的東西」。然而,對聖修伯里而言,真理並不是越辯越明,因為只是單純用邏輯推論,任何觀點皆可以自我成立,卻也容易自我耽溺,只會造成無可化解的絕望對立,無法帶來救贖。對他來說,「任何事物都必須用一種卑微簡單的語言向我們訴說,我們才能感受到它們。」(《風沙星辰》)真理應能簡化世界,讓事物直接露出純淨本質,直接對我們說話。
在這個真相替代真理、而真理千變萬化的網路虛擬時代,重讀《小王子》,尤具深意。聖修伯里相信實體世界,他是一個堅持出發親身感受的旅人,他的工作便是接觸風、接觸沙、接觸水,接觸星星,從天地萬物去找出自己的標位。另一方面,他又堅信眼前的景物並不是一切,就像狐狸說的,「最重要的東西,眼睛是看不見的。」只能用心去看,去想,去瞭解。當他徒步走在沙漠中,太陽灼烈燃燒著他的嘴唇,面對無垠的沙漠,他找不到一點可供參考的地標,尋不著方位,他一心一意只想要找到一口井,他幻想在那平滑無紋的沙地,有一口口井,宛如秘密寶藏。沙漠因為這些看不見的寶藏而閃閃發亮。小王子說:「沙漠之所以這麼美,是因為在某個角落裡,藏著一口井」,就像仰望浩瀚星空,知道幾百萬顆星星中有一顆星星長了一朵自己愛上了的玫瑰,整個宇宙的意義便會截然不同,此時的孤獨只是一種思念的形式。
飛行越多地方,碰見越多臉孔,橫跨越多國界,航過越多海洋,聖修伯里越相信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對他來說,「世上只有一種真正的奢侈,那就是人與人的關係。」飛行員是永恆的旅人,他總在離開與抵達之間,他什麼也帶不走,唯一隨時隨地帶著飛走的隨身行李只有他與世界的連接,一條無形的線,肉眼看不見,卻牢牢牽住他,不斷將他拉回來。
然而,全宇宙那麼多星球,陸地上那麼多城市,城市裡那麼多花園,花園裡那麼多玫瑰,為什麼我跟他有無形的線,而不是跟你,人與人之間那條無形的線究竟怎麼來的,那並不僅是隨機的緣分,聖修伯里認為情感是一種時間與精力的投資。在《小王子》裡,狐狸告訴小王子,「如果你馴服了我,我們就會互相需要。對我來說,你將會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對你來說,我也會將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馴服是建立連接,彼此必須發展出一套相處的儀式,容納對方進入自己的生活裡,容許自己依賴對方也讓對方依賴自己,因為「你花在你玫瑰身上的時間,才讓你的玫瑰變得這麼重要。」人類社會的基本原理不過如此。
當現代人習慣了速度,以廉價消費與臨時友情打發了寂寞,聖修伯里的小王子寓言或許顯得幼稚天真,有點保守,因為他相信照顧玫瑰的責任,相信日復一日的重複儀式,他唯一能認同的對象是點燈人,因為「他關照的是別的事,而不是他自己」。就某方面來說,聖修伯里是一位懷有責任感的老派浪漫英雄,內在質地很像他筆下《夜間飛行》的李維耶,模模糊糊感覺「好像有某樣東西的價值是超出人命的」。
不相信意識形態、不信任戰爭、不崇拜金錢權勢的聖修伯里最終選擇為他的玫瑰去死。僑居紐約多年,一九四三年四月他毅然決然回去加入盟軍的北非戰場。他的紐約友人說,他在紐約生活時非常思念法國。他將《小王子》獻給他留在法國的猶太好友雷翁.維爾特。在他替雷翁.維爾特書稿《三十三日》所作的序文,他宣稱法國是他的血肉,他全部情感的基礎,他需要那些與他有關的人活得比他長,因為「為了知道我的方位,我需要他們存在」。「大人都忘了這條真理,」狐狸說,「可是你不該忘記。你現在永遠都得對你馴服過的一切負責。你要對你的玫瑰負責……」
聖修伯里沒來得及目睹《小王子》在美國出版後的轟動盛況,一九四三年七月底從科西嘉島起飛,從此沒有回來。三個禮拜後大戰正式終結。聖修伯里離開地球的方式跟小王子一樣。他只是消失了。無人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一九八八年,一名漁夫在法國馬賽港外海捕魚,收回來的漁網裡有聖修伯里飛行員的手鍊,上頭刻了他的名字以及他紐約出版商的地址。我們才知道小王子去了哪裡。
法國一直等到戰後才有機會出版《小王子》。小王子愛看日落,紐約初版內容原是小王子有一天看了四十三次日落,小王子補充:「你知道……當一個人覺得非常悲傷時,他總是喜歡看日落。」聖修伯里離開地球時四十四歲,法國版因此改為小王子一天看了四十四次日落。我始終覺得,對所有鍾愛《小王子》的讀者來說,這是最溫柔的慰藉。
胡晴舫 二○一五年九月九日 於美國紐約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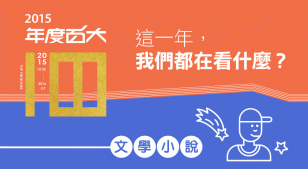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