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珍.奧斯汀生前不曾在文壇享有盛譽。她在世時,總共出版了四部小說,都沒有署名,印數也有限。在她的時代,英國的文壇活躍著幾位女作家,如安.拉德克利夫、伊麗莎白.英奇巴爾德、范妮.伯尼,但珍.奧斯汀不屬於其列。無論是她的作品,抑或她本人,知名度均不能與她們比肩。她終生過著默默無聞的居家生活,相熟者,不外乎家人、親戚和鄰里。一八一七年,她在四十二歲時去世,當時前往溫徹斯特大教堂出席葬禮的,只有她的家人。
說起拉德克利夫等作家的作品,奧斯汀本人也十分熟悉。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伯特倫家和克勞福德家的年輕人沒有演成的那齣戲,就是英奇巴爾德的《海誓山盟》。在《諾桑覺寺》第五章,奧斯汀曾特別寫了一段話,談論當時閱讀小說的風氣,提到了范妮.伯尼的《西西莉亞》和《卡蜜拉》。不過,時至今日,中文讀者多半只能在奧斯汀的小說裡,才能一睹這幾位曾紅極一時的女作家的芳名。在自己的時代,奧斯汀沒有走紅,但她越過當時的知名作家,憑著六部長篇小說,獲得了後世的無數讀者,直到今天依然廣受喜愛。二十世紀美國著名的文藝評論家艾德蒙.威爾遜在談及英國文學的趣味流變時曾說:「文學口味的翻新影響了幾乎所有作家的聲望,唯獨莎士比亞和珍.奧斯汀經久不衰。」
珍.奧斯汀的生平與創作
今人談及奧斯汀的寫作,常有一個印象,即在她的人生中,寫小說是「副業」,是她在從事一位淑女的日常活計之餘,小心進行的一種祕密活動。她的侄子詹姆斯.奧斯汀—利在為姑姑撰寫的《珍.奧斯汀傳》中回憶了這樣的細節:
她很小心地不讓僕人、訪客或家人以外的人察覺她在寫作。她寫在小紙片上,這些小紙片好收納,還方便用吸墨紙蓋住。在雜役間和前門之間有一扇轉門,開門時就會吱呀作響,但她一直不讓人修理這個小毛病,因為門一響,她就知道有人來了。
這段描寫,為我們勾勒了一幅羞怯的,甚至有些偷偷摸摸的畫面,似乎奧斯汀是一個天生的小說家,僅僅利用茶餘飯後的碎片時間,就信筆寫就了六部傑作。事實上,如果對她的寫作生涯詳加考究,便能發現,她的絕大多數主要作品,都經歷了曠日持久的醞釀和改寫。
以《傲慢與偏見》為例。據奧斯汀的姊姊卡珊德拉.奧斯汀回憶,《傲慢與偏見》的第一稿寫作於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之間,題為《第一印象》,是一本書信體小說。到一八一○年,奧斯汀開始著手重寫該書,一八一二年完稿,定名為《傲慢與偏見》,即後來出版的版本。《理性與感性》的初稿《埃莉諾和瑪麗安》完成於一七九五年,比《傲慢與偏見》早些,起先也是以書信體寫作的。這本書後來經歷了兩度修改,之間間隔將近十年,最終形成一八一一年發表的版本。其他如《曼斯菲爾德莊園》、《諾桑覺寺》、《艾瑪》,都是幾易其稿、最後付梓的故事,與她最初寫作的版本相比,從標題、情節到結構,都有巨大的變動。
可見,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奧斯汀其實在不停地思考和修改她的幾個故事。從初步構思,到最終定稿,她的作品往往要歷經十數年的反覆改寫。文學批評家Q.D.里維斯提出,奧斯汀「有些很奇特的寫作習慣」,並非「直接憑靈感下筆」:
一個習慣是接連搭起幾副龍骨,然後依次逐個充實內外,船臺上始終有不下三艘的船隻在施工,但是任何一艘總要建造好幾年才下水,並且至少要留出整整一年來把每艘最後翻修一遍。再一個習慣,是在長篇動筆之先,她已經醞釀很久了,比大多數小說家,也許比其他任何一個小說家都久得多。
奧斯汀生前沒有成名,瞭解她的只有家人。在她身後,家人對她的形象極盡保護,形成一致的對外口徑。在她的哥哥亨利.奧斯汀的〈奧斯汀小姐傳略〉中、在她的侄子詹姆斯.奧斯汀—利的《珍.奧斯汀傳》中,她都是一個善良、靈巧、樂觀、溫順、虔誠的淑女。她的姊姊卡珊德拉.奧斯汀甚至不惜毀掉一部分妹妹的書信,以保證作家的隱私在後世不被探知。由於奧斯汀這聰明伶俐的淑女形象太具壓倒性,世人很容易忽略她的另一面——一名嚴肅的小說家,常年腳踏實地、嘔心瀝血地寫作。
奧斯汀從十一二歲就開始寫作,早期作品帶有戲仿意味,主要寫來供家庭成員消遣。她出生於一個愛好文學的家庭。父親喬治.奧斯汀是漢普郡史蒂文頓地方的教區長,年輕時受過良好的教育,畢業於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母親卡珊德拉.利出身富裕的鄉紳家庭,其伯父西奧菲勒斯.利曾長期擔任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院長。在父母的教導之下,奧斯汀家的孩子都具有高雅的文學鑒賞力。珍的哥哥詹姆斯和亨利均博覽群書,曾和父親一道引導妹妹的閱讀。珍在友愛而富於書卷氣的家庭氛圍中長大,經常用逗樂的詩歌、短劇、書信體作品去取悅家人,幾乎每一篇都題獻給某位家庭成員,文中充滿著只有親近的人之間才瞭解的玩笑。後來,她從這些少年時期的作品中挑出一部分,抄錄編纂成三卷。
奧斯汀的長篇小說創作始於一七九五年,當時她也只有二十歲。到二十一歲的時候,她便寫出了《第一印象》。看起來她似乎是個早慧的作家,但正如前文提及的,《傲慢與偏見》直到一八一二年,即她三十七歲時才完稿,其間歷時十六年之久。當然,在這十六年中,她還陸續修改了《理性與感性》,寫作了《蘇珊》(即後來的《諾桑覺寺》)和未完成的《沃森一家》。我們很難界定,從哪一時期開始,作家不再僅僅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遊戲和消遣,轉而以更嚴肅的態度對待它們。目前可知的是,一七九七年,《第一印象》完稿之後,她父親曾私下寫信給倫敦的出版商湯瑪斯.卡德爾詢問他是否會考慮出版一本小說,「共有三卷,長度相當於伯尼小姐(即范妮.伯尼)的《埃維莉娜》」。對方表示不感興趣。對父親的這番嘗試,奧斯汀本人可能並不清楚。一八○三年,她將《蘇珊》手稿以十英鎊的價格賣給出版商班傑明.考斯比,但考斯比一直沒有出版該書。直到一八一一年,《理性與感性》出版上市,她才終於獲得了除家人以外的讀者。
誠然,在作品發表的道路上,奧斯汀走得並不一帆風順,寫作也沒有改變她的生活。她終身未嫁,沒有財產。早年,她和家人一起住在史蒂文頓的牧師住宅。一八○一年,她的父親退休,全家遷往巴斯。等到父親去世,她便始終和母親、姊姊住在一起,經濟上由幾位兄長供應。《傲慢與偏見》中班內特太太所擔憂的命運,正落在奧斯汀母女的頭上。好在她們還有體貼的兄長照顧。她們先在南安普敦,與法蘭西斯.奧斯汀同住。三年後遷往查頓,住在愛德華.奧斯汀提供的一幢宅子裡。珍.奧斯汀在這裡住了八年,得以潛心寫作。這也是她人生中最後一處住所。
經濟情況決定了奧斯汀的生活狀態。一七八五—一七八六年,她曾跟卡珊德拉一起就讀寄宿學校,但家裡無法負擔兩個女兒的學費,因此短短一年後,兩人就回到家中。此後,她始終在小家庭的圈子裡活動。直到生命的最後十年間,她才因為小說的出版,而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不過,那本賣給出版商卻遲遲未出版的《蘇珊》的版權,最後仍是由她最親密的哥哥亨利.奧斯汀出錢贖回的。寫作沒有讓她進入文學界,也沒有擴大她的交際圈。她終身筆耕不輟,但從不曾以「專業作家」自居,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她還得做不少必要的家事,例如管理僕人、照顧家人——均為她這個社會地位和年齡的女性須負責的工作。比起寫作才華來,她談論自己的縫紉手藝也許更多些。她和姊姊不但要根據潮流去製作、修改自己的衣物,還要為兄弟做襯衫。
因此,在身分認定上,珍.奧斯汀無疑是謙遜的。在談論自己的創作時,她也一向保持謙遜。她把自己的小說比做「小小的(約兩吋寬的)象牙微雕」——這個比喻在後世一再被人引用,以說明她那種局限在「描繪一個村鎮上的三、四家人」的選材和筆觸。用中文說,這就是「雕蟲小技」。她的謙虛之詞,會讓人以為她對自己的寫作評價不高,或不那麼看重寫作。但讀到這裡,你應該已經明白,事實並非如此。
謙遜的態度不會影響奧斯汀寫作時的判斷力。有一件事可以證明,對於寫什麼、不寫什麼,奧斯汀有她主動的選擇。當時的攝政王(即後來的喬治四世)很欣賞《理性與感性》和《傲慢與偏見》, 但並不知道小說的作者是誰。一八一五年,奧斯汀到倫敦照顧病中的哥哥亨利,給他診治的醫生恰好也是攝政王的醫生之一,因此機緣湊巧,這位地位顯赫的讀者獲知了奧斯汀的真實身分,便邀請她前往其在倫敦的居所卡爾頓宮參觀。接待她的,是卡爾頓宮的圖書管理員詹姆斯.克拉克。此後,奧斯汀與克拉克先生有幾輪通信,詢問將作品題獻給攝政王的事宜。在回信中,克拉克先生曾兩度熱心地對她的寫作提出建議。第一次,他指出她「沒有刻畫好英國牧師這個形象,至少沒有刻畫過當代牧師」;第二次,他提議說,「描繪科堡家族的歷史傳奇應該會很有意思」。奧斯汀謙遜而鄭重地拒絕了這兩個想法。她表示:「我向您保證我真的沒有這個能力。」「除非是為了救自己的性命,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其他理由能讓我正襟危坐去寫一部嚴肅的歷史傳奇。」「不,我必須保持自己的風格,只能走自己的路。」
與之同時代的大作家華特.史考特以寫作歷史傳奇見稱,奧斯汀也喜歡讀他的作品。這位想像力豐富、筆觸雄健的小說家,曾在一八一五年寫過一篇未具名的評論,對《艾瑪》大加讚賞。他把奧斯汀的小說與感傷和傳奇小說對比,稱「其特色有如麥田、農舍和牧場比之一所名勝邸宅中加意修葺過的園林,或一派茫茫山色中坎坷不平的奇峰」。他尤其指出奧斯汀所選的題材與現實生活的關聯:
……《艾瑪》的作者在完全依靠平凡事件和普通階層人物的同時,創作出了如此充滿生氣和獨特氣質的素描,使我們一點也不覺得欠缺了那種只有藉由描寫大大超乎我們自己之上的思想、習俗和情感所產生的異常事件才能得到的興奮感……她的全部小說的故事都是由一般人就能觀察到的普通事件所構成的。讀者會發現,她的登場人物的起心動念也正是他們自己和他們身旁大多數人的起心動念。
這段話,正好從一個擅長「大題材」的作家的角度,闡釋了奧斯汀本人「小小的(約兩吋寬的)象牙微雕」這一說法。不過,「麥田、農舍」與「名勝、奇峰」的比較,以當今的眼光來看,似有居高臨下之感。
其實,回過頭去看奧斯汀的三卷少年作品,會發現裡頭淨是些誇張、荒誕的故事。這是因為他們全家人經常在一起閱讀小說,對市面上流行的諸如范妮.伯尼、亨利.麥肯齊等作家的感傷小說,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奧斯汀的寫作,便以對這類小說的戲仿開始。她用誇張的筆墨,去諷刺感傷小說那矯揉造作的章法和文風,引起家人的共鳴。卷二「一束信」的第五封,寫到一個青年為了催促他愛的姑娘下定決心,揚言要為她而死:「我死了以後,叫人把我抬去放在她腳下,也許她還不至於驕傲得不肯在我微賤的遺骨上灑一滴憐憫的眼淚吧。」像這樣的情節和措辭,在她的成熟作品中是絕對看不到的。起初可能僅僅出於孩子的遊戲動機而開啟的寫作,在經年累月的實踐當中,慢慢剔除了不屬於作家本人的成分,荒誕的調調不見了,文雅而幽默的筆觸則發展起來,最終形成了獨屬於珍.奧斯汀的寫作風格。
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文壇,推崇的是像史考特、勃朗特、薩克雷的作品那樣大開大闔的風格。奧斯汀卻能不受干擾,開拓出自己的寫作道路。這份力量,不該被她的謙遜作風所掩蓋。
(未完)
許佳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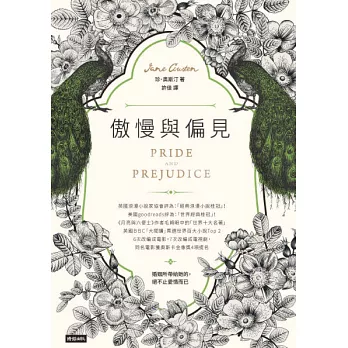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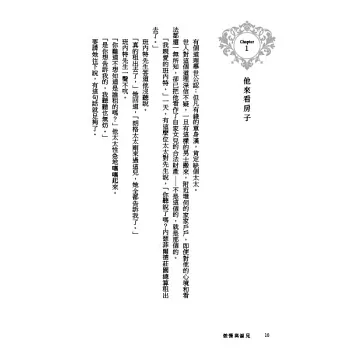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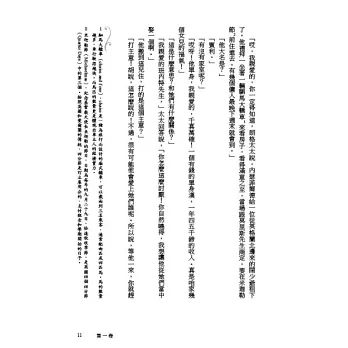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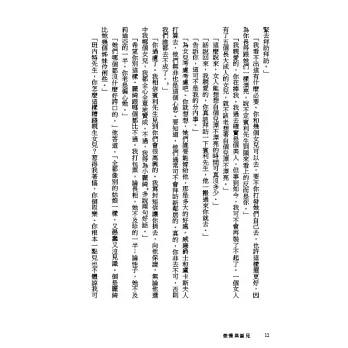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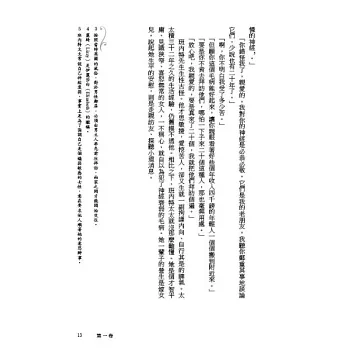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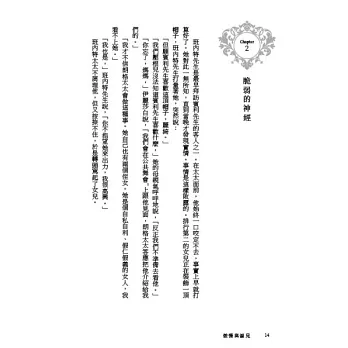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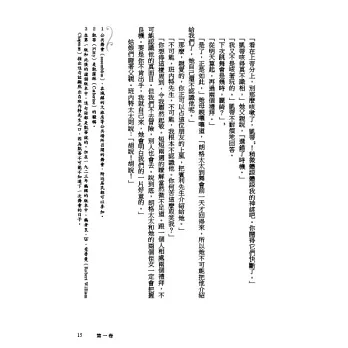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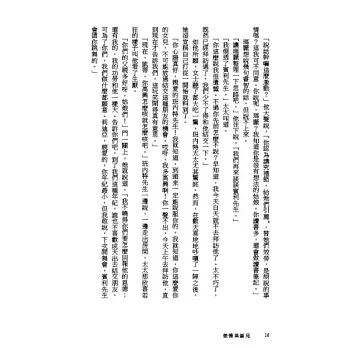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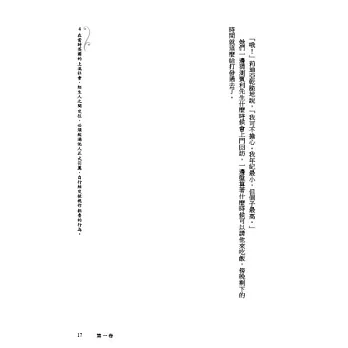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