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楊德昌做為導演的人何其多,
舒國治做為朋友,淺淺憶寫之。
極個人的憶友私情,集大時代的一頁縮影!
一九八一年,舒國治經由余為彥介紹,認識了甫自美國回台的楊德昌。那時楊德昌拋開前半生一切,投入拍攝電影,十年內極其風格地完成了《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份子》;一九九〇年底,舒國治自美漫旅返台,近距離參觀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拍攝過程。兩人交誼愈發深刻。
轉眼之間,楊德昌已去世十六年。不到三十歲就認識楊德昌的舒國治,在七十歲時寫下《憶楊德昌》,將楊德昌的性格、創作習慣、藝術涵融……等,以及這四十年的台灣電影、台北藝文風情,順手將一些幾乎可稱「當代藝文史」的瑣事也記上一筆,寫成了這本極有意思的書。既是極個人的憶友私情,也成為大時代的一頁縮影;實乃一位台北風華人物敍寫另一位遠行矣之風華人物的精神執索。
「我們人生的探索與選擇,再怎麼矢意自由、矢意創作,
會不會仍然擺脫不了近代史的軌跡?
啊,我能跟他聊的,屬於我和他的年代以及更早,應該極多極多,
唉呀,如今不可能了!」——舒國治
【本書收錄】
● 舒國治提供,與楊德昌、友人們相聚留影,及前進東京影展之隨行珍貴相片。
● 被舒國治譽為「九〇、九一年台灣最出色的攝影人之一」王耿瑜,鏡頭下記錄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拍攝現場。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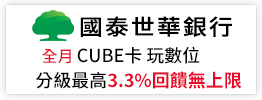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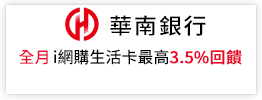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