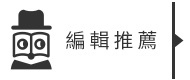推薦序
不願散場的人——閱讀李時雍《永久散步》
孫梓評(作家)
香港朋友來台短居一季,約我去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許多次我路過它卻未能停下。看完各種押房,在小小的苔綠的放封區,想像當年許多秀異青年,莫名成為良心犯,抱持怎樣的心情在此?日落前我們走向余余劇場《百合.ゆり》,地點就在園區內禮堂。時雍替舞劇做了精采的導聆,舞蹈以家族故事為軸線,舞台上許多箱子,重複被舞者搬運堆疊撞落,箱子是很有效的道具,那麼具體,卻又抽象。
《永久散步》也讓我想到那些箱子。箱子本身表情匱乏,但能收納各種情緒。就像這些讀起來質地均勻的字,揭開之後可能藏有「燙手的心」。
輯一「燈塔街」是時雍哈佛一年的薩默維爾住處,望文生義我喜歡那街道是暗,卻有燈塔矗立指引。寫在四十歲之前的這些字,像手札,日記,或寄給親密朋友的一束信,要求敘事的人大概會迷路,然而其中一閃一閃的星芒,帶有哲學思索,是一名青年藝術家真誠的說話。我特別喜歡此輯撥亂時間線性:抵達早於出發,停留同時返回。時間在此是個地層,我們跟隨記憶,沿途拜訪左營的水兵,民雄的大學生,飛到美國度過暑假的少年……寫作者的年輪,若析磨其中成分,是美術,音樂,電影,舞蹈,還有文學,或說許多許多的愛——那些燃燒了全部的自己,提前離席的,已成灰燼的,往往是時雍最在意的「暗中之暗」。能於暗中辨別另一種暗,必然因為,那暗,閃爍著氣質相近的毫光。
書中引阿巴斯說,「我察覺人未能細看眼前景物,除非它存在框架內。」這些低溫的文字,也是時雍炭筆勾勒的景框(或者箱子)。許多話語連同事件的線條被裁切,但總有各式的人:朋友,同學,戀人,親人,甚至工作與生活中萍水相逢的誰,走進相紙,成為構圖。地球上持續的移動,形成程度不一的眷戀,就像他離開前隨手拍下一幀異國或異地的房間(那也是一個箱子)。
如同時雍,我亦篤篤寞寞察覺生命來到中途埡口,想像過可能的燦爛墜為「沒有的生活」,面對日子,惟低頭耕耘視線所及。同時明白,人生確實一趟無窮盡補課,比如,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後來便在陳列《殘骸書》得到更為立體的理解。相較於前輯較內向性的私人斷代,「紀念碑」作為輯二,彷彿由內推擴向外,置身文明與野蠻之間,當然可以與其從文學審視、梳理現代台灣四次原住民關鍵事件的論文《復魅》對讀。
「紀念碑」從學者回到作者,以均衡的抒情,寫新城,白水湖,鶯歌,和平島,蘭嶼,霧社,廬山;讀陳映真,巴代,夏曼.藍波安,鍾肇政,舞鶴,李昂,這些島國行腳,是對遺忘的喚醒(打開箱子),也是對詮釋的拮抗(衝撞箱子)。
時雍曾借小說《餘生》的句子說,思考是一場「無所為的永久散步」——不知怎的我想起一個十七歲夜晚,和同樣著迷寫作的朋友們捧著剛領到的人生第一座獎盃,在南方深夜城街,沒有盡頭往前走著,渾然不覺剛剛轉彎處是湯德章被槍決之地,再往前,來到二十年後將重新開張的林百貨。心底的柴薪熊熊燃燒,因為曾被燈塔的光拂過,散步不是為了目的,而只是讓自己在路上,持續移動著,當夜浸潤更深,哪怕置身暗中,「就讓我成為那樣一個不願散場的人吧。」
後記
未曾清晰的路
讀書時,曾念到這樣一句話:清晰的不確定。
寫作外,近年我同時的研究書寫,沿著文化人類學者詹姆斯.克里弗德對當代的旅行、移置,影響所及生命的「根源」與「路徑」等思考;他曾引用高更著名的畫作名,代為自我的問句:《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回想最後卻回覆道,只有不確定性,lucid uncertainty。
高更那幅橫長的、彷彿總結人類一生的最大規模畫作,就收藏在波士頓美術館。離開多年,我仍時常印象起那個展間,想起粗礪畫布上鋪展開的新生、成年的中途,或晦暗憂傷;而金橙色的人身,總像籠罩於豔陽的光芒。出生巴黎的藝術家餘生遠赴南太平洋的小島大溪地,愈往深處,僅為找尋一種嶄新的光色,新的顏料、繪畫主題,聽尋一種,內在愈清晰的不確定。終致在臨界著虛無面前,以一瞬揭示生命永久的勃發。
我未曾想像過會有這樣一部散文集。就像我未曾想像有這一段路。《永久散步》的文字,主要寫自二○一八至二○一九年,與二○二一到二○二三年間,並曾有各別的系列名。寫作當下,未曾浮現任何書的念頭。直到今年初,在研究室彙編另一部論著時,莫名地,想起這幾年生活過的文字,一個下午重新閱讀,竟有了它彷彿清晰的輪廓,一幕幕鋪展的影像似有回聲,我是誰?我從何處來?
此刻,我仍然懷抱著「我向何處去」的疑問?一如留在零點的薩默維爾,房間裡,暖氣時而漫起薄薄的霧,我的窗外,可見一架微鏽的舊單車斜靠欄杆。後院的樹、草坪,在雪後泛白,在春天覆蓋上金色的光。前側是家門前那條以燈塔為名的長街,如果沿著一直走,會途經古老的校園,徹夜敞亮的圖書館,地鐵站,與廣場,如果一直走,是否將又走回到清晰的查爾斯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