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民主在「歷史的終點」仍然屹立不搖
二十五年前,我為一份名為《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小型雜誌寫了〈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那是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對於我們這些曾陷入冷戰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大辯論的人來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時刻。那篇文章發表於柏林圍牆倒塌前幾個月,正值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民主抗議活動,東歐、拉丁美洲、亞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當時也正處於民主轉型的浪潮之中。
我當時認為,歷史(在宏大哲學意義上的大寫歷史)的結果與左派思想家的想像相去甚遠。經濟與政治的現代化進程並不像馬克思主義者所斷言、蘇聯所宣稱的那樣,通向共產主義;而是走向某種形式的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我當時寫道,這大寫的歷史似乎在自由中達到了頂點:選舉產生的政府、個人權利、經濟體系內的資本與勞動力也在國家相對溫和的監管下流通。
如今再回頭看那篇文章,讓我們先說一件顯而易見的事:二○一四年的感覺跟一九八九年非常不同。
靠著油元的挹注,俄羅斯現在是一個具威脅性的選舉專制政權,它霸凌鄰國,並試圖奪回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時所失去的領土。中國仍然是專制國家,但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在南海與東海展現自己的領土野心。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家華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近期所述,舊式的地緣政治已經大範圍捲土重來,歐亞大陸的兩端正威脅著全球的穩定。
當今世界的問題不僅僅是專制勢力正快速挺進,許多現有的民主國家狀況也不樂觀。以泰國為例,其脆弱的政治結構上個月被一場軍事政變所取代;或者以孟加拉為例,其制度仍然被兩部腐敗的政治機器牢牢掌控。許多看似已經民主轉型成功的國家(像是土耳其、斯里蘭卡、尼加拉瓜)卻一直往專制體制開倒車。其他國家,包含最近加入歐盟的國家,如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貪腐的問題仍然嚴重。
然後還有已開發的民主國家。過去十年,美國和歐盟都經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意味著經濟低迷與高失業率,對年輕人來說尤其如此。雖然美國經濟現在已經重新開始擴張,但利益並沒有被平均分享,而該國兩極化與黨派化的政治制度似乎也難以成為其他民主國家的好榜樣。
所以,我的歷史終結假說是不是已被證明為誤,或者即使沒有錯,也需要大幅修正?我相信,根本的理念大致上仍然正確,不過如今我對政治發展的本質有了更多的了解,而這些是我在一九八九年那激動人心的日子裡看不太清楚的。
首先讓我們考慮一下,在過去兩個世代裡,經濟與政治體系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在經濟方面,世界經濟產出大幅提升,從一九七○年代初期到二○○七至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期間,大約成長了四倍。雖然這場危機是一個巨大的頓挫,但全世界各大洲的繁榮程度已大幅提高。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世界已經在一個自由的貿易與投資體系中結為一體了。即使在中國與越南這類共產主義國家,市場規則與市場競爭仍占主導地位。
政治領域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根據史丹佛大學民主研究專家賴瑞.戴蒙(Larry Diamond)的說法,在一九七四年,世界上只有大約三十五個選舉民主國家,占世界國家總數不到百分之三十。但到了二○一三年,這個數字已經擴大到一百二十個左右,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一九八九年所標誌的是一個廣泛趨勢的突然加速,即已故哈佛大學政治學家薩繆爾.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稱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這股浪潮大約從十五年前的南歐與拉丁美洲的民主轉型開始,接著又延伸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亞洲。
以市場為基礎的全球經濟秩序的興起,與民主的普及,兩者間顯然有所聯繫。民主總是建立在廣泛的中產階級基礎上,而在過去一個世代,擁有資產的富裕公民群體到處都擴大了起來。較富裕、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往往對政府的要求也高得多──因為他們納稅,所以他們認為有權利要求政府官員負責。世界上許多專制主義最頑強的堡壘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像是俄羅斯、委內瑞拉或者波斯灣各國;在這些地方,所謂的「資源詛咒」給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收入來源,而非人民自己。
自二○○五年以來,我們也目睹了戴蒙博士所說的全球「民主衰退」,石油資源豐富的獨裁者甚至有能力抗拒改變。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發布的政治與公民自由指數,民主制度的數量與品質(包含選舉的公平性、新聞自由等)過去連續八年都呈現下降趨勢。
讓我們把這種民主衰退放在恰當的脈絡背景裡來看。雖然我們可能會擔心俄羅斯、泰國或尼加拉瓜的專制趨勢,但這些國家在一九七○年代都是不折不扣的獨裁體制。儘管二○一一年在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發生了驚心動魄的革命,但「阿拉伯之春」除了在發源地突尼西亞,不太可能在其他地方產生真正的民主。不過長遠來說,這很可能意味著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將會更回應民意。期望真正的民主會迅速發生是極其不現實的。我們忘記了,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歐洲的「人民之春」)之後,民主又花了七十年的時間來站穩腳跟。
此外在思想領域,自由民主仍然沒有任何真正的競爭對手。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的俄羅斯以及阿亞圖拉(編註:「ayatollah」,伊朗伊斯蘭什葉派領袖的稱號。)的伊朗即使在踐踏民主的實際作為中,也仍會向民主的理想致敬。不然普丁為什麼還費力在烏克蘭東部舉行虛假的「自決」公投?中東一些激進分子也許夢想著恢復伊斯蘭的哈里發國,然而這並不是穆斯林國家絕大多數人的選擇。看起來唯一還算有機會與自由民主制互相競爭的制度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它將專制政府、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高度的技術官僚以及技術能力混合在一起。
然而如果讓我打賭,五十年後,是美國與歐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國,還是中國會更像歐美,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很多理由顯示,中國模式不可能延續。體制的合法性與共產黨的長期執政都仰賴持續的高度成長,但在中國努力從中等收入國家轉型為高收入國家的過程中,這種成長率根本不會發生。
中國透過毒害土壤與空氣累積了巨大的隱藏負債;雖然政府仍然比大多數專制體制更能快速應變,但中國的中產階級日益壯大,當情況變壞時,他們很可能不會接受當前腐敗的家長式統治。中國不再像毛澤東革命時期那樣,將普世主義的理想投射到自己的國界之外。隨著不平等程度的不斷升高,以及擁有政治關係的人所享有的巨大利益,「中國夢」代表的不過是一群相對少數的人快速致富的途徑而已。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放心滿足於民主在過去幾十年的表現。我的歷史終結假說從來無意指向決定論,也並非單純地預測自由民主在全世界必然勝利。民主國家之所以能夠生存和成功,只因為人民願意為法治、人權和政治可問責性而奮鬥。這樣的社會依靠的是領導力、組織力,以及純然的好運氣。
──二○一四年刊於《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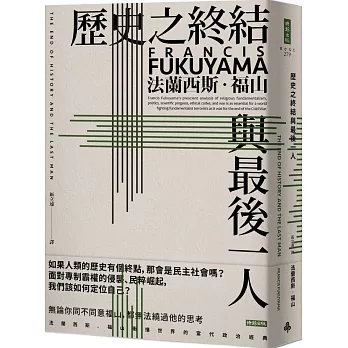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