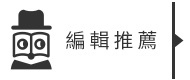推薦序
灰塵與光
張惠菁(作家)
在曹馭博的小說即將出版的前幾天,台灣熱烈討論的事情之一,是有一位高中老師批評顧炎武的〈廉恥〉在許多新版課本中不再收錄。這位老師認為,少了這篇文章,她便少了引導學生思考「士大夫夫之無恥,是為國恥」的依據。對此,她呈現出一種深深的、憤怒的被剝奪感,令許多人不解而亦回應以憤怒。自然雙方是無法相互說服的。因為在那些論理的背後,語言說的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在每個人不同的心智地圖中,事物的勾連狀態。對這位老師而言,一篇文章的在與不在,勾連了許多事物,特別是朝向一個對她而言不理想的時代,當中或許有她個人的挫折與無法對準。在另一些人眼裡,這些勾連毫無根據,只有她個人在這時代裡的無法對準是成立的,除此之外,她的話或許也勾連起他們小時候被強迫背誦、灌輸某些價值觀的不愉快記憶。
讀曹馭博的小說,我想起這件事。書中的七個故事,從一種集體的失能說起。父親們出門工作,依循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則,賺錢,存錢,買房,買車。「直到雷曼兄弟搞砸了一切,把曲線圖往下撥弄,萬物也跟著下墜——首先是房價,然後才是人類。」作為開頭的〈煞車〉這一篇,展開了一個原有信仰緩慢崩塌,或所依循之規則被抽走的世界。一位失業,同時也失去了妻子與兒子之尊敬的父親,考慮輕生。他孤獨地面對著人生中到此為止,種種超出他控制的發展:自己從就業到失業,兒子從神童長成了普通卻傲慢的孩子,附近學區裡的孩子也壞透了、成了會設局害人的惡童,在學校的後門(而不是正門,正門保持著讓家長接送孩子的功能),進行著霸凌勒索的遊戲。
雖然如此,曹馭博對許多人類以外事物的描述,卻令我感到,這不盡然是一個醜惡的世界。「小雨中太陽的光暈像新生兒的拳頭緩緩鬆開」,「在雨落傾盆的終結一瞬間,浮光擴散到看不見路面」,「鳥群在河口掠過橘黃色的雲彩,牠們受大風所迫而停懸,瘋狂地抓著天空」。世界金光燦燦。城市也是。然而獨行於其中的人類卻孤獨,無法互相理解。對周遭景物的描寫,好似正對比著角色的渺小無力。「一切事物都待我如陌生人」,〈橋〉的第一人稱主角這樣對自己說。〈你可能會比死更慘〉裡,男主角投胎轉世變成了蟲,然後從地上、從壁角看著曾經的一家人,就如卡夫卡〈變形記〉的台式家庭加上東方轉世信仰版。
這是誰之過呢?還是我們不應該在詩人寫的小說中追究簡單截然的是非對錯?曹馭博在扉頁上引用了瑪莉蓮.羅賓遜的《遺愛基列》的句子。那是一位老人,暮年得子,小說家羅賓遜讓他回顧著自己的一生,表達著自己對孩子所感受到的、那無條件的愛,「只因你活在世上,我就鍾愛著你」,與這愛並存之下,世界萬物彷彿籠上一層新的光亮。這樣的句子出現在扉頁,而翻開進入曹馭博所寫的七個故事,卻是個和「只因你活在世上,我就鍾愛著你」有段距離的世界:被時間消磨了的父子之愛,受虐的孩童,被歧異而扭曲地對待著的上班族,變成蟲的人,記憶著沙漠與核爆、分不清誰是誰的幻想的母子和情人,還有被餵以許多文本、開始生育敘事的AI......。
但就此便說,曹馭博寫的一個跟瑪莉蓮.羅賓遜相反的世界;說他是在說,在一個沒有愛之光照耀的世界裡,一切都不可能對、人只能是孤獨,我覺得也不盡然。或許有時,愛就如同〈你可能會比死更慘〉裡,陳盡妹分不清楚是埋怨還是思念,轉世的阿哲分不清是擁抱還是囚禁,這樣的描述是不是令人想起,某種我們常聽說(或親身體驗的)台式家庭,講話難聽卻執著到死也不放——難道這才是愛的本質?有的愛,不是純淨的光,而是摻雜著各種雜質,有著灰塵在其中飛舞,明明暗暗,閃閃爍爍,似子宮似牢籠。
七個故事來到尾聲,有一個不同的母親,是AI的餵養者(〈盜賊的母親〉)。「逼近生命的秘訣,就是在虛構裡頭,操作他人的生命,在他們的大腦裡,放一根無中生有的釘子」,雖然原本是無中生有而來,但一旦那根釘子被拿走,人卻會要死要活地尋覓,想要找回它來。讀到這裡,我會聯想到佛法。想到人窮盡一生追逐的釘子,還有那釘子勾連而來的一切,夢幻泡影,牢固難破。
在這泡影牢固的世界裡,詩人曹馭博的第一本小說集,對我們起著詩的作用:搖晃我們,疏離我們,籠罩我們,將我們轉向,插入釘子,拔掉釘子,拆掉鷹架,築起鷹架。這個世界與我們的心智,恐怕不是一篇文章就必定能開啟什麼地,那樣對仗完美。有光照不到的角落,有灰塵能漂浮著抵達的地方。無論到或不到,詩搖晃著我們,讓我們放下傲慢,感受那些灰塵與光,也感受那歪斜、對不準、混沌的一切。